我叫陈芳,今年 38 岁,在国企做了十五年会计。每月 8000 块的工资雷打不动,就像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出现在厨房熬小米粥的身影一样,连高压锅上汽的声音都带着一成不变的调子。老公周明比我大两岁,在汽车 4S 店做销售经理,每月能拿 15000,不过他的工资条总带着汽油味和酒气,就像他回家时永远沾着应酬的烟味。

我们结婚十三年了,儿子浩浩今年初二,正是能把人气到高血压的年纪。去年秋天我妈摔断了腿,出院后就搬来和我们住,每天要吃三种降压药,药盒在餐桌上摆成小方阵。我每天像个陀螺,早上送孩子上学,顺路去菜市场挑最新鲜的鲫鱼给我妈熬汤,白天对着电脑算厂里的进项销项,下午四点半准时溜去接我妈做康复理疗,晚上回来盯着浩浩背英语单词,等周明醉醺醺回家时,往往已经过了十一点。
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周明第一次提出分房睡是在元旦后的第三天。那天我给我妈换完纸尿裤,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他凑过来想抱我,身上还带着健身房的汗味。我条件反射地躲开了:"别碰我,明天还要早起带浩浩去补习班。" 黑暗里他翻了个身,床垫发出弹簧不堪重负的吱呀声,再后来,他就抱着枕头去了客房。


起初我没觉得有什么,毕竟结婚这么多年,激情早就磨成了亲情。直到三月份,周明突然开始频繁提起 "舞蹈"。他说 4S 店新来了个年轻销售,整天炫耀自己在肚皮舞工作室练出的马甲线,他跟着去试了节课,发现跳完浑身轻松。我擦着我妈床头柜上的药渍,头也不抬:"你一个大男人跳什么肚皮舞,不怕别人笑话?" 他梗着脖子说:"现在男人跳爵士舞很正常,教练还是个单亲妈妈呢,人家自己开工作室,厉害得很。"
从那以后,周明每周三周五都要去 "练舞"。有天晚上我帮他洗外套,闻到衣领上有股淡淡的茉莉香,不是我用的蓝月亮洗衣液味道。他的手机开始设密码,洗澡时总把手机带进浴室,有次我路过客房,听见他压低声音说:"今天这个动作我回去再练,你视频指导我好不好?"

真正让我警觉的是清明节前的周末。我提前从娘家回来,刚打开家门就听见客房传来视频通话的声音。周明的声音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温柔:"朵朵今天有没有想叔叔呀?等你妈妈带你去动物园,叔叔给你买棉花糖好不好?" 朵朵?我知道那是女教练的女儿,他居然连人家孩子的名字都记住了。
我推门进去时,周明正对着手机屏幕笑,屏幕里那个穿露脐装的女人也在笑,卷发垂在肩头像黑色的瀑布。看见我,周明手忙脚乱地关掉视频,手机壳上还贴着张卡通贴纸,是个跳芭蕾的小女孩 —— 显然不是我们儿子喜欢的奥特曼。
"她多大了?" 我盯着他发红的耳尖。
"28,离婚三年了,自己带孩子..." 他突然意识到说错话,慌忙改口,"就普通朋友,人家教舞很专业的。"
我没再说话,转身走进主卧,打开衣柜最下层的抽屉,翻出我们的结婚照。照片里周明穿着笔挺的西装,我梳着齐耳短发,笑得像两只偷喝了蜂蜜的小熊。现在的他,微信头像换成了在舞蹈室自拍的半身照,手臂上的肌肉线条比结婚时明显多了,而我的眼角,已经爬满了细纹。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特意请了假,说要带浩浩去科技馆。其实我把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躲在 "舞之灵工作室" 对面的奶茶店里。下午三点,周明准时出现,穿了件新买的黑色紧身 T 恤,衬托得腰板格外挺直。工作室的玻璃门推开时,一股热风混着香水味涌出来,那个叫林小羽的女教练迎上来,直接伸手搭在周明肩上,指尖在他锁骨处轻轻点了点。
我看着他们在落地窗前练舞。林小羽的手从周明的腰侧滑到后背,又顺着脊椎骨慢慢往上,最后停在他后颈处轻轻揉捏。周明的耳朵红得要滴血,却乖乖地跟着她的节奏摆动身体。阳光穿过玻璃窗,在他们身上镀了层金边,像极了当年我们在婚纱照里的模样,只是现在,女主角换成了别人。
我猛地站起来,奶茶杯捏出刺耳的响声。穿过马路时我听见自己心跳如鼓,推开工作室门的瞬间,林小羽正踮脚帮周明调整领口,两人的距离近得能看见彼此睫毛投下的阴影。

"你就是周明的老婆吧?" 林小羽先开了口,语气里没有半点慌乱,"他总说你工作忙,没想到这么年轻漂亮。" 她穿着露脐装,肚脐眼里还戴着枚银色的脐钉,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像把小刀子。
周明猛地往后退了半步,撞翻了旁边的音响,《玫瑰少年》的前奏戛然而止。我盯着他胸前的汗水,突然发现他锁骨下方有块淡红色的印记,像是被人咬出来的。
"回家。"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芳姐,周哥最近进步特别大," 林小羽突然凑过来,身上的茉莉香几乎要把我淹没,"他说你们分房睡半年了,夫妻间还是要多沟通..."
她的话没说完,我已经抬手给了她一巴掌。声音清脆得像玻璃杯摔在地上,她的脸颊立刻肿起五道指痕。周明冲过来推我,我踉跄着撞在把杆上,后腰传来火辣辣的疼。
"你疯了?" 他眼里全是怒火,"小羽离婚后一个人带孩子有多难你知道吗?她只是教我跳舞,我们什么都没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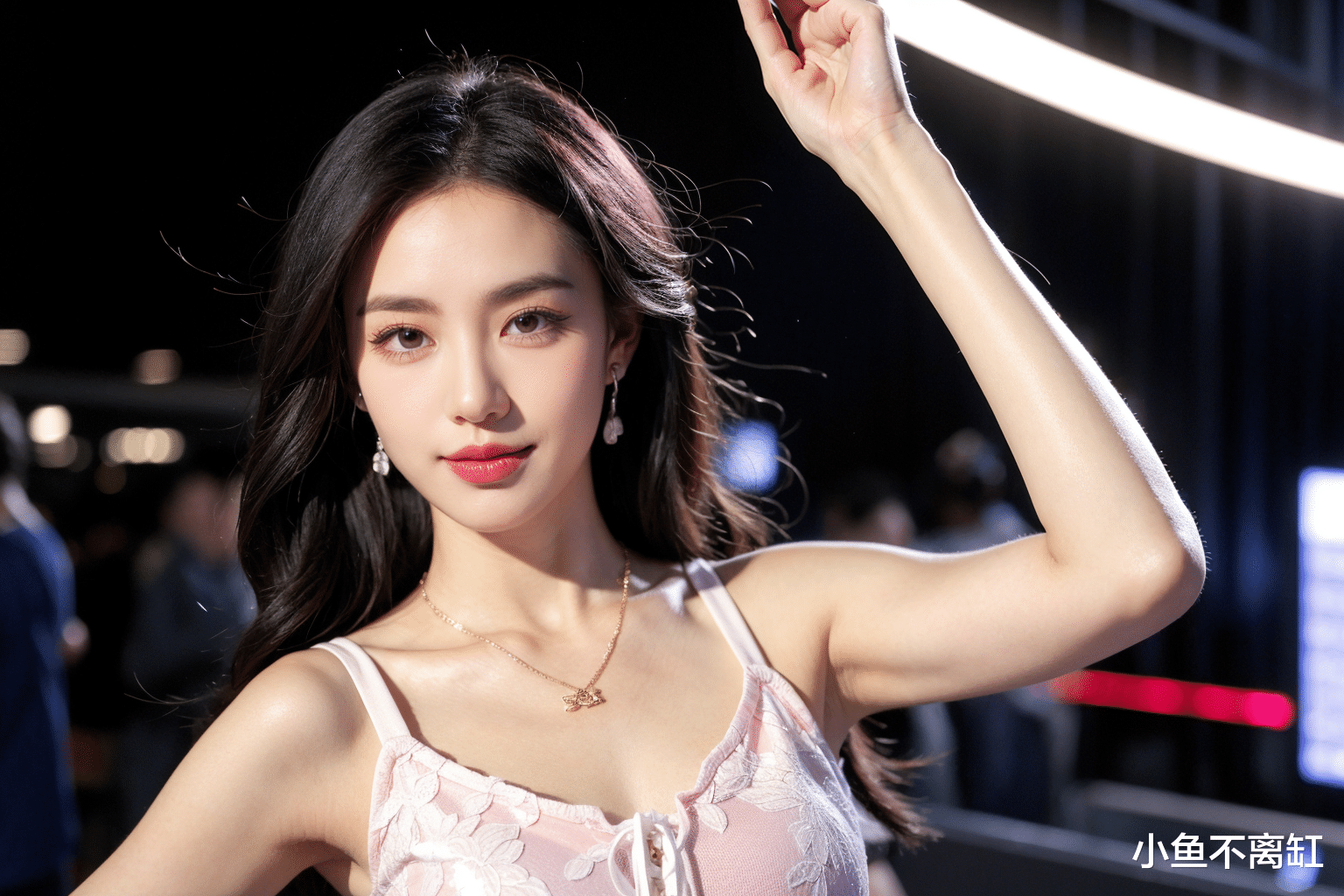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陌生。这个曾经在产房外守了我十八个小时的男人,现在正护着另一个女人,用我从未见过的凶狠眼神瞪着我。林小羽蹲在地上捡散落的舞鞋,抬头时嘴角还挂着笑:"周明,你先送芳姐回家吧,朵朵还在幼儿园等我呢。"
那天晚上,我们在客厅坐了一夜。周明说林小羽让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说她会认真听他讲销售压力,会在他跳错动作时轻轻敲他的手背,说她的女儿朵朵喊他 "周叔叔" 时,他好像又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
"你呢?" 他最后问我,"你多久没正眼看过我了?每次我想和你说句话,你不是在给你妈擦身子,就是在骂浩浩不写作业。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像个妻子,简直像个保姆!"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抗抑郁药瓶,没告诉他自从我妈住院后,我每晚都要靠吃药才能睡着。也没告诉他,上周家长会老师说浩浩成绩下滑,是因为听见我和他在客房吵架。更没告诉他,刚才在工作室摔倒时,我感觉下面流了血 —— 那个被我忽略了半年的月经,终于在今天造访,带着迟到的疼痛。

凌晨五点,我妈在房间里喊我,说想喝水。我站起来时腿麻得差点摔倒,周明伸手想扶我,我躲开了。走进老人房,床头灯昏黄的光里,我看见我妈鬓角的白发比上个月又多了,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她也是这样在我病床前守了整夜,用温毛巾一遍遍给我擦手心。
"小羽说她不要名分," 周明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只要我们不离婚,她愿意一直这样... 她说婚姻不一定要靠性维持,重要的是彼此理解..."
我转身看着他,这个我熟悉又陌生的男人,突然笑了。原来在他眼里,婚姻是可以分成两半的,一半给家庭责任,一半给激情梦想。而我,不过是他精心搭建的城堡里一块不起眼的砖,稳固却乏味,直到出现另一块更漂亮的玻璃,让他宁愿打碎城堡也要去追逐。
"周明," 我听见自己说,"明天去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吧。"

他愣住了,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我没再理他,转身给我妈倒水,水温正好,就像我这么多年来熬的每一碗粥,温度精确到让人生厌。窗外传来第一声鸟鸣,不知道是不是楼下那棵玉兰树上的斑鸠,去年春天它还在我们家空调外机上筑过巢,后来被周明嫌吵赶走了。
现在想想,有些东西一旦飞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像周明衣领上的茉莉香,就像我们床笫间消失的温度,就像那个在婚姻里慢慢枯萎的自己。或许林小羽说得对,婚姻不一定要靠性维持,但她不知道的是,当爱情连最基本的欲望都消失时,剩下的不过是两座孤岛,在生活的海洋里各自漂浮。
天亮了,我要给我妈煎药,要送浩浩上学,要去单位报销理疗费。只是从今以后,这些事都将变成 "我" 而不是 "我们"。周明坐在沙发上抽烟,烟灰落在我们的结婚照上,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笑得那么甜的样子。现在,照片上的玻璃已经有了裂痕,就像我们的婚姻,看似完整,实则千疮百孔。
或许有人会说我傻,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计较男人那点破事。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当一个女人在婚姻里连拒绝亲密的权利都要被指责时,当男人把逃避责任美其名曰 "寻找自我" 时,这样的婚姻,不要也罢。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茶几上我没喝完的奶茶杯上,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一颗颗滑落,像极了昨晚没掉的眼泪。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疼痛,也带着未知的可能。而我,终于在人到中年时,第一次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 它说,哪怕前路坎坷,也好过在无爱的婚姻里,慢慢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