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成书过程,长达一千多年,早在三国期间,有关三国纷争的遗闻逸事就有流传。而历代文人在诗词中吟咏三国故事,亦不胜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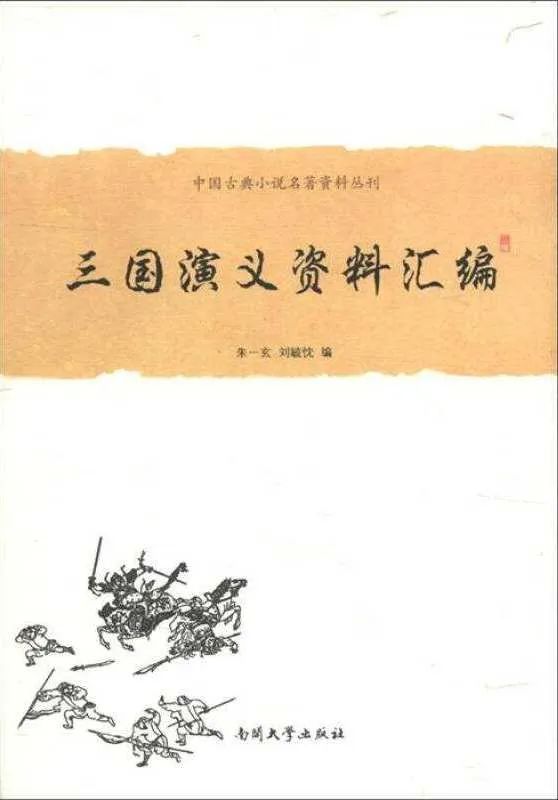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本事编”收录历代文人创作的有关三国题材诗歌词曲,自六朝至宋元,为数甚多,其中即有陆游《诸葛书台》诗一篇。笔者近日翻阅陆游词作,发现其中亦有涉及三国故事者,凡有6篇。
陆游一生勤于创作,尤以诗歌为多,流传至今者有近万首,而见存词作130 馀篇,虽仅为其诗歌的百分之一强,但数量也并不在少数。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陆游曾长时期生活在吴越间,并在剑南有过多年的戎幕生涯,但是,无论是在诗歌,抑或在词作中,吟咏三国事者,却是寥若晨星。因此,其涉及三国事之词作6篇,还是值得注意的。

放翁词中涉及三国事者凡有6篇,为:[水调歌头]《多景楼》、[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大圣乐]《电转雷惊》、[鹧鸪天]《送叶梦锡》、[恋绣衾]《不惜貂裘换钓篷》、[好事近]《平旦出寝关》。
但是,在这6 篇词作中,只有[水调歌头]《多景楼》一篇,尚可认为是以三国事为题材的,其馀5篇,仅是在作品中提及三国事,或用事与三国事有关而已。[水调歌头]《多景楼》一篇,本文将专节讨论,这里,先对其他5篇词作逐一考索。
[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约作于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秋季①。陆游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五月除左通直郎通判镇江府,明年,离开镇江,饯行于镇江府西之浮玉亭。因此,这是一篇吟咏别离之作。
词上片写绿树、长亭、秋色,情绪颇见怅恨;下片亦是写离别销魂,但末三句为:“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从字面上看,这也纯为抒写离情别绪而已,且《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此词调下即有题作《别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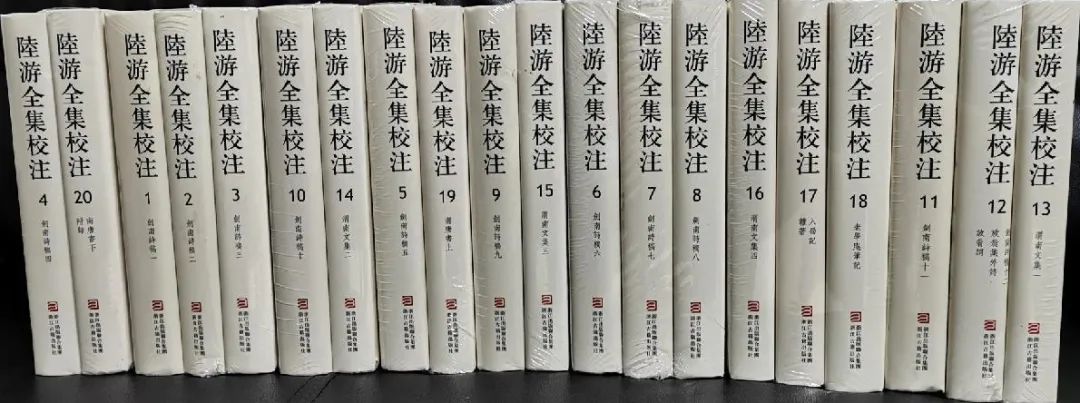
《陆游全集校注》
只是其中“横铁锁”事,乃典出《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1]1209
丹杨,即丹阳,今属江苏省镇江市。此是王濬于灭蜀之后,继而起兵伐吴之事。吴人凭借长江天险,并横置铁锁、铁锥,抗拒北军,然晋师除锥熔锁,终无阻碍,顺流鼓棹,直捣三山。孙皓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率百官投降晋师,东吴遂亡。
唐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有“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句,于东吴之亡国,颇为感慨。陆游用此典,当亦是想起当年江边鏖战之事,因此,词虽写离别愁绪,但不能排除其亦有思古之幽情。
[大圣乐]《电转雷惊》,或作与乾道二年(1166)。此时陆游家居镜湖,年已42 岁,功名无成,心灰意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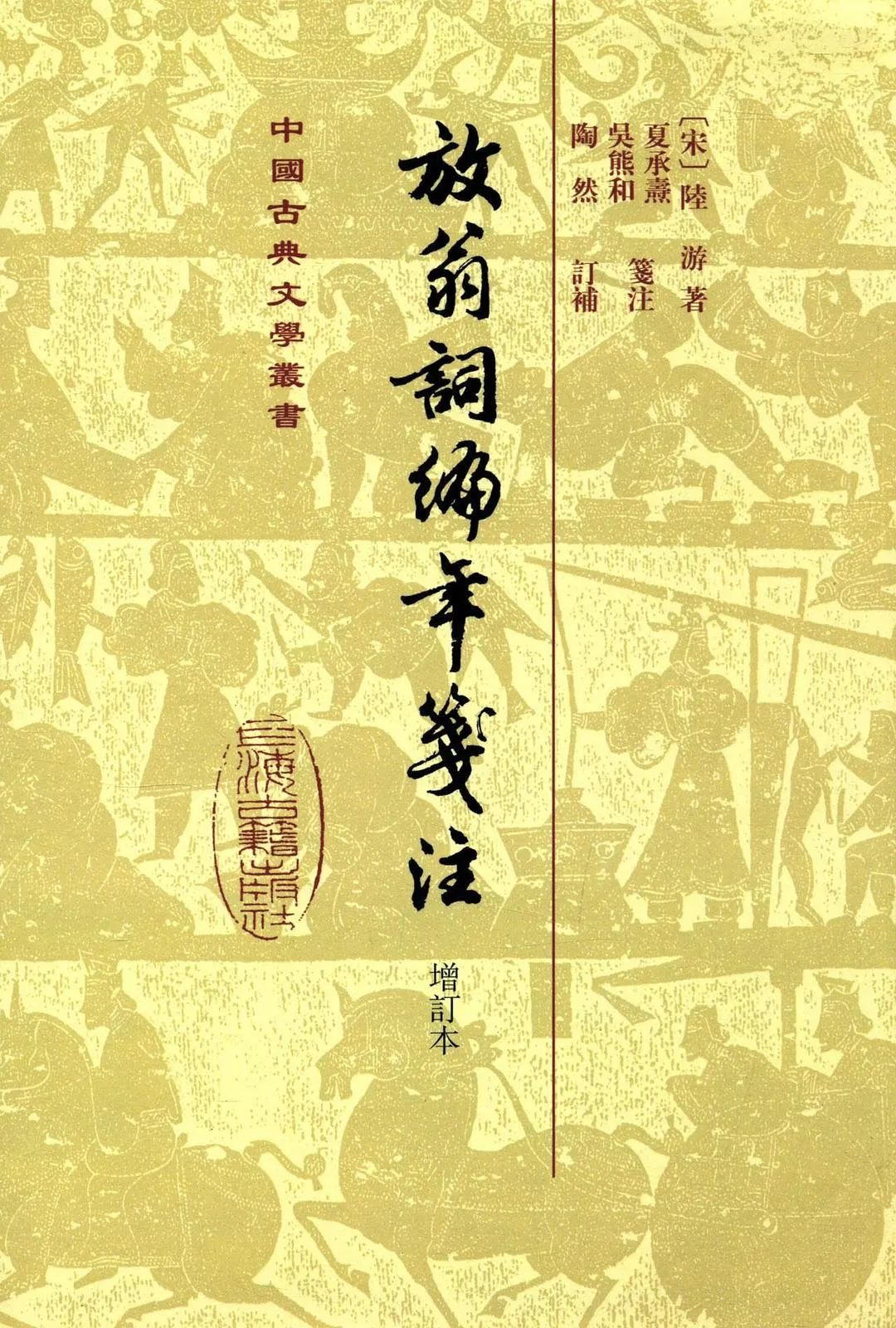
《放翁词编年笺注》
词之下片写道:“须臾便是华颠,好收拾形骸归自然。又何须著意,求田问舍,生须宦达,死要名传。寿夭穷通,是非荣辱,此事由来都在天。从今去,任东西南北,作个飞仙。”潦倒之中,尚见安命乐天之意。
此中“求田问舍”是个熟典,在宋人词中并不乏见,如稍晚于陆游的辛弃疾,在其[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即有“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句。
《三国志· 魏书》卷七《陈登传》记刘备与许汜议及陈登:“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2]2229-2230
陈登,三国时下邳(今属江苏省睢宁县)人,字元龙,举孝廉,有名于世。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曰:“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年二十五,举孝廉,除东阳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2]230
[鹧鸪天]《送叶梦锡》,或作于乾道九年(1173)。叶梦锡,即叶衡,梦锡其字,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尝知成都,于乾道九年召赴临安。
陆游此词,当是在成都为叶衡送行之作。词中所写无非亦是人生易老,两鬓成霜而一事无成,于是在青楼酒肆,虚掷光阴。
词之上片有“十千沽酒青楼上”句,典出三国时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文选》注云:“平乐,观名。”诗写贵族少年斗鸡走马、狩猎宴游之事。此亦为熟典,唐李白《将进酒》:“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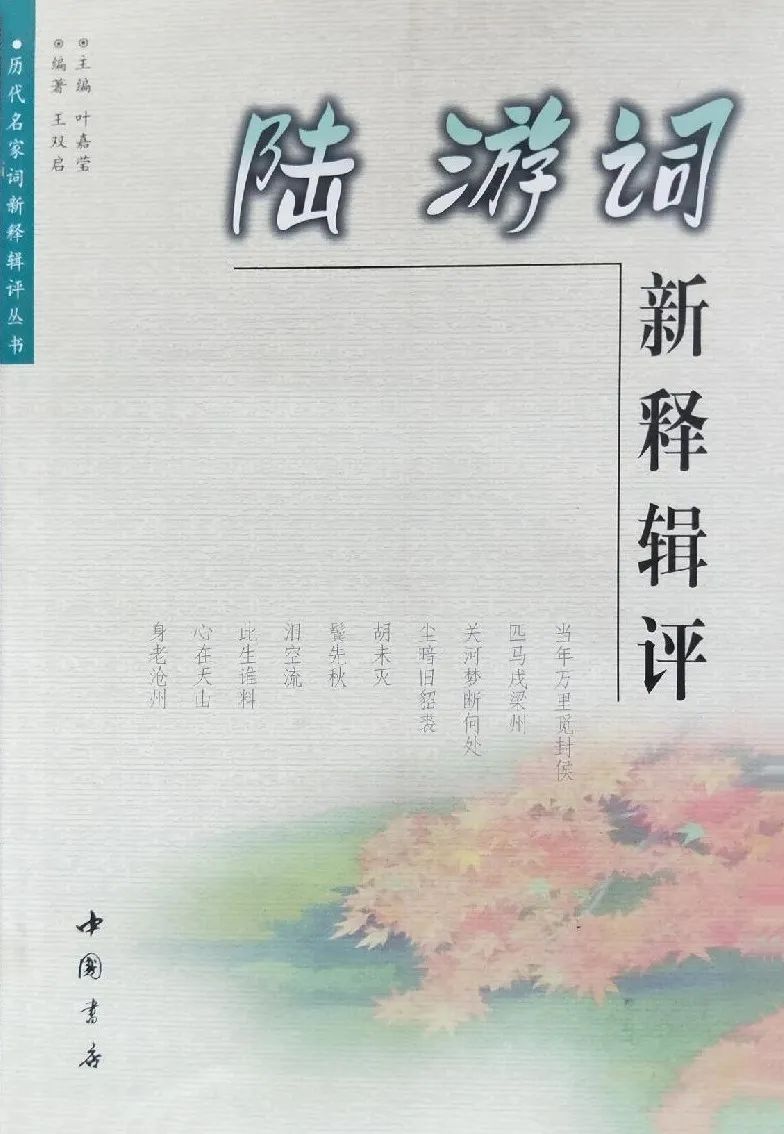
《陆游词新释辑评》
[恋绣衾]《不惜貂裘换钓篷》,具体创作年份不详,然观其词意,当作于自蜀中归来,闲居家乡山阴时。此时陆游已是步入晚年,一生志向,皆成空想,赋闲乡村,生活亦较困窘。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颇为达观。
词之下片写道:“幽栖莫笑蜗居小,有云山、烟水万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画中。”
其中“蜗居”一典,乃指三国时有名隐士焦先,事见《三国志· 魏书》卷十一《管宁传》裴松之《注》:
“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其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值。又出于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藏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不肯妄言。”
“《高士传》曰:或问皇甫谧曰:‘焦先何人?’曰:‘……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如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结绳已来,未及其至也,岂群言之所能仿佛,常心之所得测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能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污其耳目,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之处,延年历百,寿越期颐,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2]363-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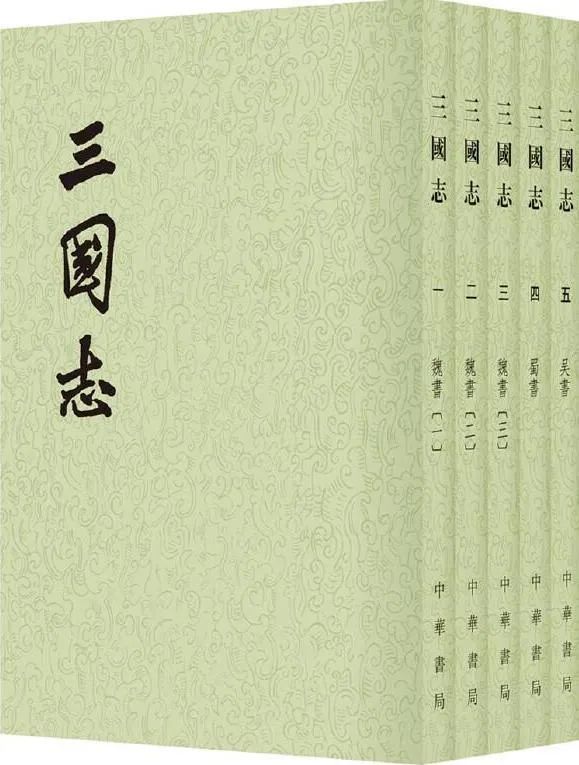
《三国志》
瓜牛庐,即蜗牛庐。裴松之《注》云:“案《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室,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庐。《庄子》曰:‘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谓此物也。”[2]366
陆游一生力主抗战,垂暮之年在梦中还想着为国戍守轮台,在诗词中抒写隐逸情怀,亦属违心之语。而且此处用事,舍陶令结庐人境仅避车马喧闹,而独取焦先蜗居以远离战火,隐约之间,亦可见其对朝廷之深深失望。
[好事近]《平旦出寝关》,具体创作年份亦不详。此篇写到“秦关”、“伊水”等,皆在今河南省。词之下片为:“汉家宫殿劫灰中,春草几回绿。君看变迁如许,况纷纷荣辱。”显然,这是一篇借古吊今之作。
所谓“汉家宫殿劫灰中”,典出曹植《送应氏三首》之一:“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劫灰”乃佛家语,喻天地大劫,焚烧殆尽之馀灰。中州乃汉末三国时主要战场,狼烟连天,生灵涂炭,正如曹操《蒿里行》所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陆游有感于此,,油然慨叹,亦是情理中事。
上述陆游词作,实际上,除却[水调歌头]《多景楼》,唯有[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尚可见思古之情,其馀均只是用事而已,与三国事并无多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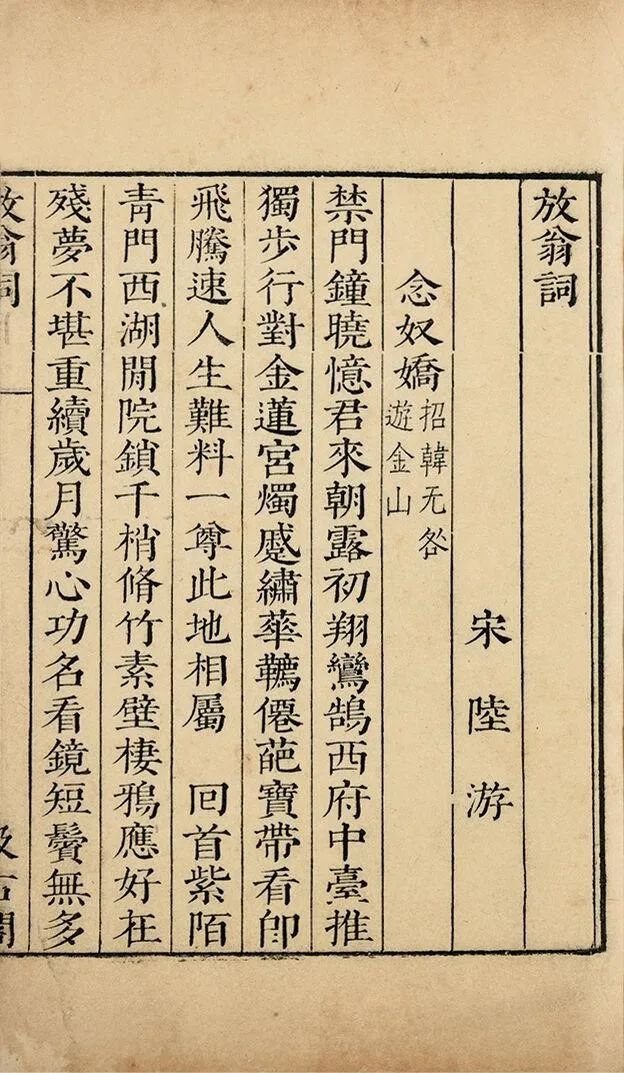
《放翁词》

[水调歌头]《多景楼》可说是陆游词中唯一一篇真正吟咏三国事的作品,或于隆兴二年(1164)秋天,与镇江知府方滋游北固山时所赋。词凡95言: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飘渺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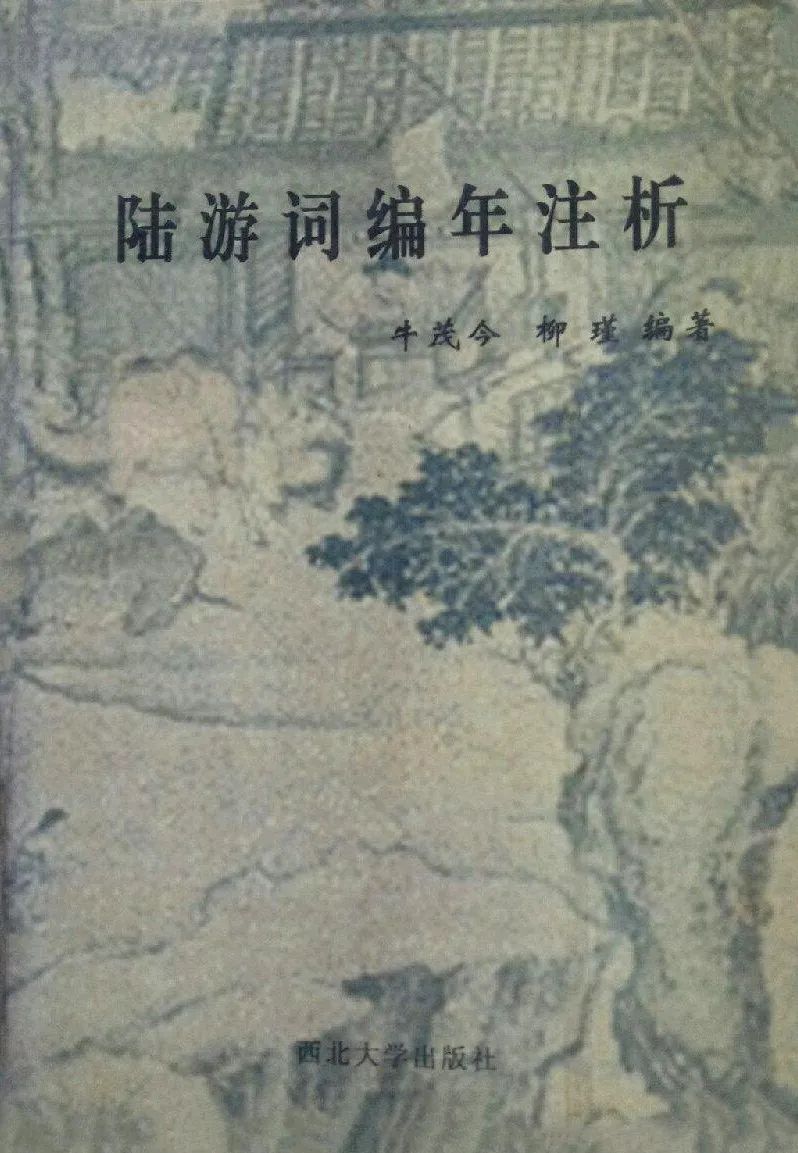
《陆游词编年注析》
古徐州即镇江,亦称南徐。多景楼在今镇江北固山后峰,始建于唐代。
中唐李德裕有《晚下北固山喜松径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有“多景悬窗牖”句(见存诗已不全),因以为楼名。多景楼临江而建,极目远眺,千里吴楚尽收眼底,宋人米芾有《多景楼》诗,颂之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其所书此七字匾额,至今尚见于多景楼门首。
作为江岸胜景,多景楼与黄鹤楼及岳阳楼并称长江三大名楼,历代迁客骚人,多有登临览胜,吟咏之作,不胜枚举。而镇江又与三国孙吴关系密切,尤其是北固山,有甘露寺,为所传孙吴联姻之处,乃千古佳话。
因此,凡登临北固山,必游甘露寺与多景楼,也必然会联想到三国故事。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也是如此。
词之上片,“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飘渺著危楼”数句,描写危楼高耸,江山如画,一开首即将占尽江南形胜的北固山与多景楼推至读者面前,颇有气势。
登高临远,极目吴楚,词人自然而然想到了千年前的三国相争。如今江水东逝,滚滚波涛,在当年却是辀橹云集、金戈铁马的战场。孙、刘两家,联合抗曹,何等的摄人心魄。置身于多景楼上,陆游仿佛听到了悲壮的鼓角,看到了连天的烽火。
显然,陆游于孙权、刘备是有崇敬之意的。其《渭南文集》卷四十三《入蜀记》云:“至甘露寺,饭僧。甘露,盖北固山也。有狠石,世传以为汉昭烈、吴大帝尝据此石共谋曹氏。”
可见,陆游登临北固山多景楼,千年往事顿时在心头涌现,“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四句,不仅再现了当年战争场景之酷烈悲壮,亦抒写了词人对孙、刘联手拒曹英雄气概的激赏之意。
词之上片,笔意贯通流畅,一气呵成,形像鲜明,意境也较为开阔远大,寓意和谐自然,读来颇有灵动之感。

《陆游传》
然而,换头后,词人在描述了江边秋景、与方滋纵论古今后,忽然写到了西晋初年名臣羊祜。
羊祜,字叔子,《晋书》卷三十四有传,云:“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机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1]1020
羊祜由魏入晋,力主伐吴,虽终不克成功,然为后来晋军灭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羊祜为人做官,极为清廉。《晋书》本传云:“祜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馀财。”[1]1021
羊祜曾出镇襄阳十年,有政绩,因此,深为当地民众敬爱。《晋书》本传云:“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荆州人为祜讳名,居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1]1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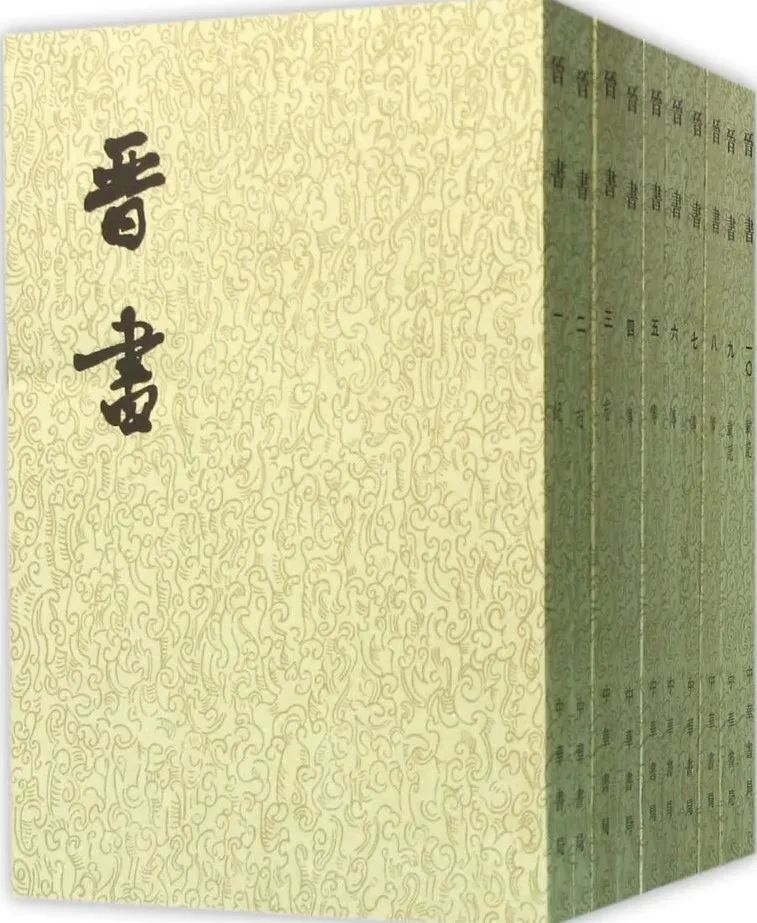
《晋书》
当是时,东吴已非旧日气像,早已不见孙仲谋之英雄豪气。孙皓昏庸暴虐,已是独夫。羊祜为晋师南渡灭吴所作贡献,自当赞颂。如今胜景依旧,而斯人已逝,凭吊千载羊叔子,放翁之感慨也就无以自抑。
所以,词中对羊祜的赞美,与上片所表达的对孙、刘之崇敬,并无矛盾。但是,此处更多的是在称道羊祜作为坐镇一方之大吏,为官清正,政绩卓著,深为万民景仰和怀念,而在这里,陆游显然是在借羊祜以赞誉方滋,人或谓其不免溢美之嫌。
其实,据宋人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一《墓志铭》载,方滋其人,以荫入仕,历知秀、楚、静江、广、福、明、庐、镇江、鄂、建康、荆南、绍兴、平江等州军府,所至务尽其职,发奸擿伏,严而不苛,经理财赋,缓而不弛,颇著政绩。尝入朝权刑部侍郎,兼权户部。又两度出使金国,吐论平正,应答自如,深为金人所推重。
所以,放翁此处赞誉方滋,还是出自衷情,尚不能视为阿谀之词。只是上下片着意有异,因此,全词给人的感觉是,上片所写,乃借景抒情,显得甚为自然合理,而下片转为赞颂方滋道德政绩,词意亦直露有馀,蕴藉不足,难孚人意。
北固山上多景楼,自是吊古伤今的绝佳所在。但是,平心而论,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一篇,较之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诸作,并无十分出色之处。这大概是陆游乃与方滋同游、赋词以赞太守有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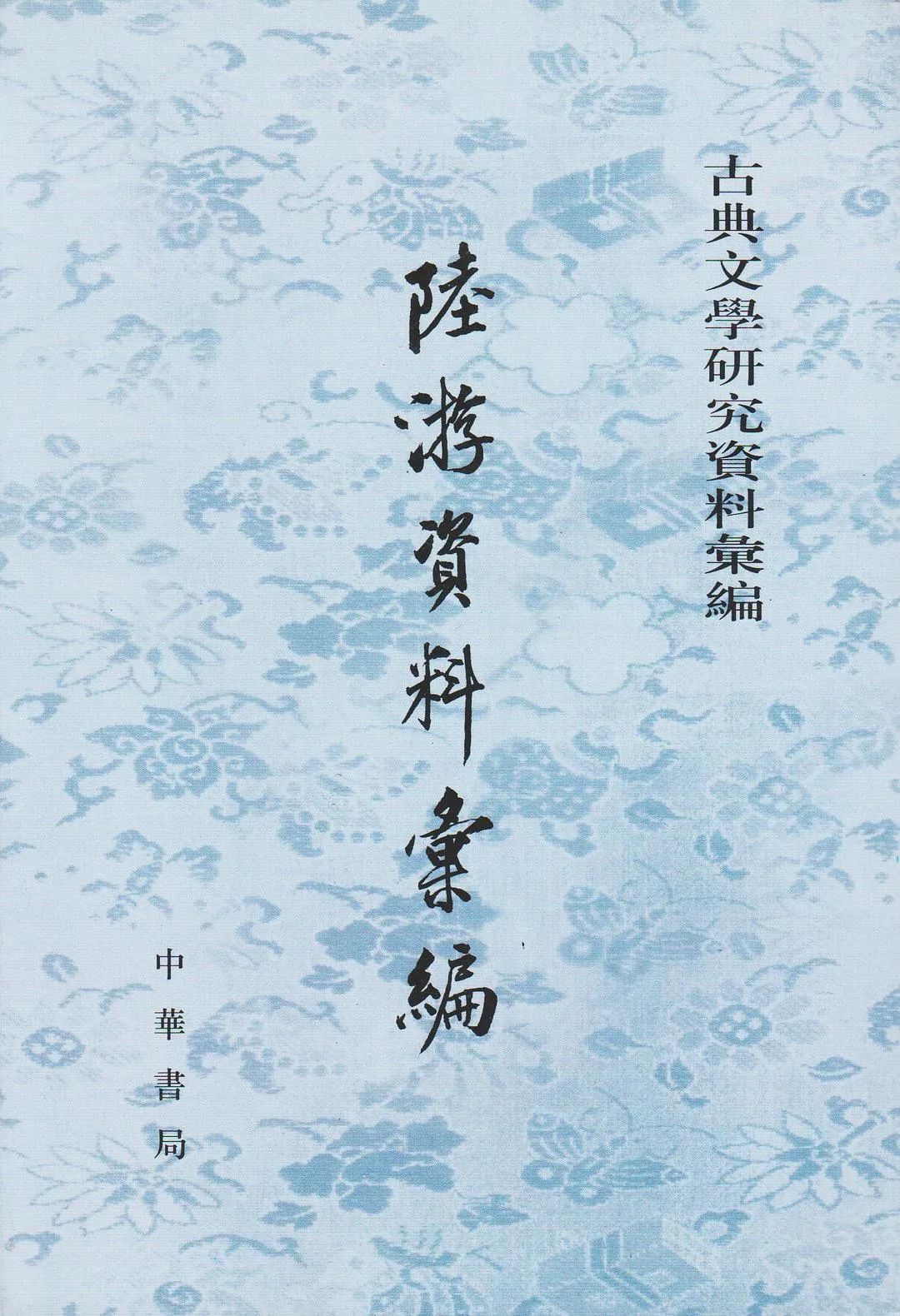
《陆游资料汇编》

陆游为南宋第一大诗人,诗名隆盛。其词作数量亦尚夥。当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陆游之词显然不及其诗歌成就之高。但是,其诗与词,在情感基调上,却基本上是统一的。
如上所述,放翁所填的6篇涉及三国事的词作,多为用典而已。而其[水调歌头]《多景楼》一篇,也是在宴游时,即情即景而作,因此,所谓与三国故事有关者,亦仅如此。
夏承焘曾这样说:“陆游一生,匡复志事,到老不衰,可谓不愧其言。说陆游之诗是他一生匡复志事之馀事,那么,他的词又该是他诗的馀事。以‘诗馀’称他的词,岂不是名符其实?这对作者来说,原是褒辞而不是贬辞。”[3]2
既然陆游填词,只是“他诗的馀事”,自然在艺术上会有所不足。陆游诗歌数量创作之多,在古代诗人中罕有其匹。
但作品既多,精力有限,不暇裁剪修饰,也就在所难免了。其诗如此,其词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在他的有些词作中,我们看到其状物绘景、抒发情气,变化不多,不过这并不是陆游词作的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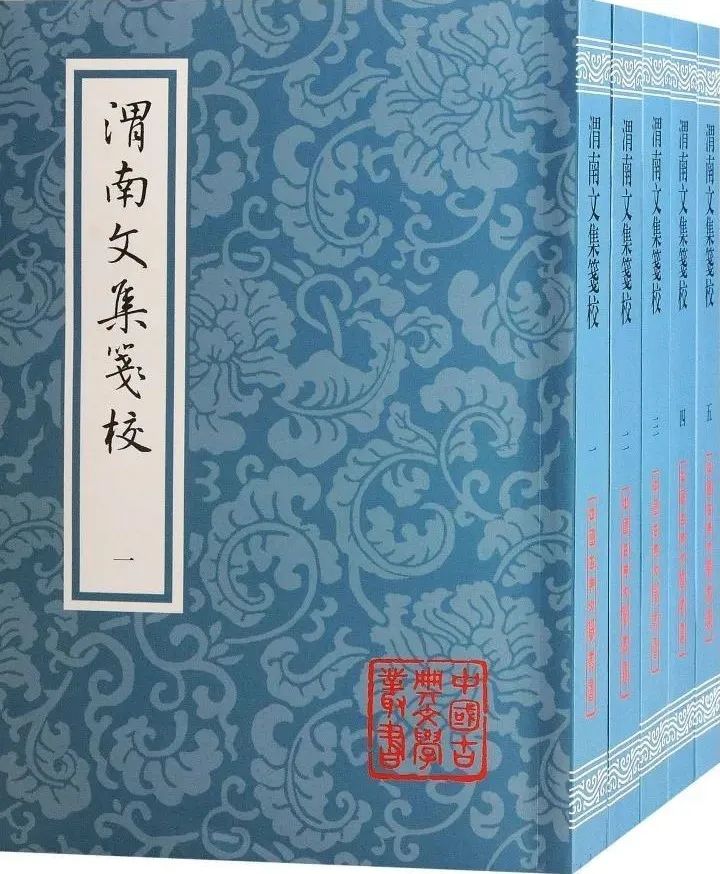
《渭南文集笺校》
此外,与稼轩词一样,陆游词作,用典之多,俯拾皆是。即如[水调歌头]《多景楼》,上下片95言,有典十处许。其馀诸篇,亦大抵如此。正如宋人刘克庄在《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中所批评的那样:“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词中用典,可使作品意蕴深厚,应是词家填词要遵循的一个法则。李清照《论词》,即有“典重”与“故实”的论点,在词中适当运用典故也是有必要的,赋予词作庄重的面貌,即所谓“一扫纤艳”。陆游词用典过多,为刘克庄诟病,但仅就这6篇作品看,尚未可讥之为掉书袋。
刘熙载《艺概》卷二谓“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其实,放翁何曾有意要做一个诗人,在他说来,无论是作诗,抑或填词,皆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初唐杨炯《从军行》所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黄仲则《吊杜甫墓》云:“埋才乱当世,并力作诗人。”也并不完全符合杜甫的心意,杜甫《旅夜抒怀》就明白说道:“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放翁的理想与前贤是一样的。陆游一生,念念不忘北伐抗战,恢复神州河山。这一精神,在其诗中,随处可见,即其词作,亦时见流露。他渴望驰骋沙场,驱逐金兵,为国效命。然而,终其一生,满腔热血,无以抛洒。报国无门,无奈而掉鞅诗坛,中心之愤懑感慨,可想而知。
辛弃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有这样的伤心语:“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而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更见其老泪纵横:“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正因为这样,在本文论述的6 篇涉及三国事之词作中,我们还是能看到放翁词作之壮伟豪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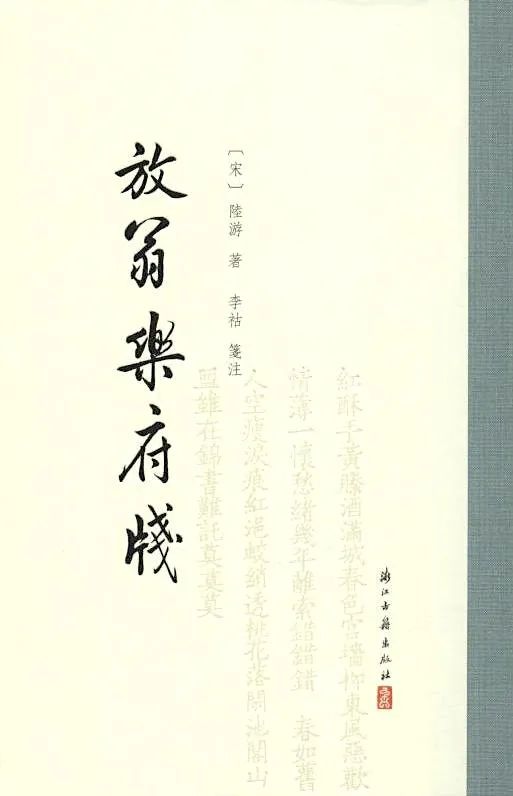
《放翁乐府笺》
在陆游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爱国忠君之作,但是,在他的词作中,这类篇什在比例上相对要少。
夏承焘认为陆游对填词一事,抱有鄙视态度[3]2,这是有道理的,陆游自己也是承认的。在陆游眼中,填词原是无聊之事,只是自己终不能免。所以,对于作词,较之赋诗,陆游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
这样,在其词作中,就多见歌咏宴游之篇,清人宋徵璧这样批评放翁词:“陆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4]234
然而,在总体上,陆游词作的情调与其诗歌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时见慷慨激昂之气,充满杀敌报国之豪情壮志,而词作之结构,亦多浑厚一体者。
所以,说陆游于“诗馀”一事不甚重视,并非是说其填词不认真,视作游戏文字,敷衍了事。相反,在陆游见存的130馀篇词作中,大部分作品还是精心结撰的。即如这6 篇涉及三国事的作品,无论写景状物、吊古抒情,其作品中流露的情感,仍然不乏激荡昂扬之气。
所以,夏承焘说放翁“不欲以词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于一般词人”[3]2,是很有见地的。

《放翁诗话》
汉末三国,近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云蒸霞蔚,慷慨悲壮,留下了众多的遗闻逸事,而在巴山蜀水,太湖之滨,以至黄河上下,故迹遗址,人所不及遍游。是以历代文人,多有吊古缅怀之作。
但是,正如本文开首所言,陆游一生生活的地方,就在三国东吴与西蜀故地,但似乎他对此不甚在意,吟咏之作亦寥寥。所以,放翁见存的六篇涉及三国事之词作,犹可窥见其内心世界,反映了其创作的多样性,亦是极富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三国志·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夏承焘. 放翁词编年笺注· 论陆游词(代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徐釚. 词苑丛谈:卷四品藻二[M]. 王百里校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