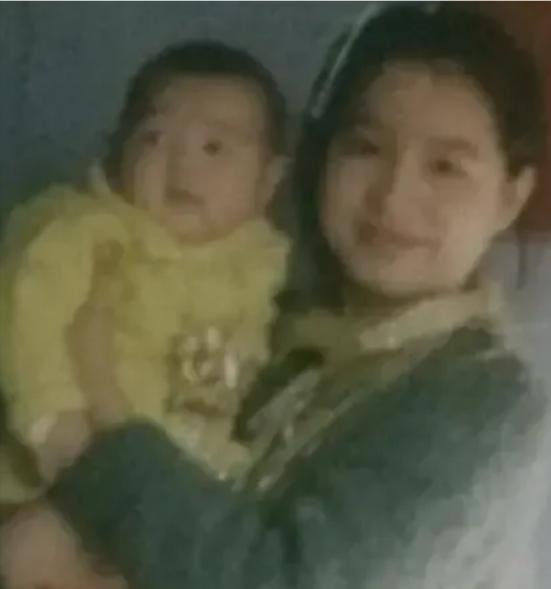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返城,母亲怒骂:未婚先孕,不知羞耻!可得知孩子身世后,竟然抱着孩子痛哭流涕,哥哥嫂子也抢着要抚养孩子...... 信源:顶端新闻——22岁未婚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回家被母亲指责,没想到,随后她却抱过孩子:我和你一起养 1976年夏天,北京东四胡同里突然炸开了锅——25岁的邵红梅背着帆布包,怀里还抱着个4岁的男娃,刚跨进家门,她妈抄起鸡毛掸子就朝她挥过来,嘴里喊着“你在乡下干的丢人事!未婚先孕,我们老邵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街坊邻居全扒着门缝看,有人指指点点说“这知青下乡几年,咋还带个野娃回来”,那娃吓得往邵红梅怀里缩,小脚上还沾着陕北的黄土,裤腿上打着眼生的补丁——这孩子到底是谁?邵红梅为啥非要带着他回北京? 这事得从7年前说起。1969年,18岁的邵红梅跟着知青队伍去了陕西延川的赵家沟,刚到那会,她差点哭了。 土窑洞黑得白天都得点煤油灯,炕上铺的芦苇席硌得人疼,下地干活时,她连锄头都握不稳,没几下就磨破了手,村民们看笑话似的哄笑,她蹲在田埂上偷偷抹眼泪。 是村里的赵砚田夫妇拉了她一把。赵砚田是生产队的会计,跟媳妇闫玉兰结婚多年没孩子,看这北京姑娘可怜,就把她领回了家。 闫玉兰手巧,每天早上都给她留个白面馒头,自己啃掺沙子的窝头;邵红梅水土不服上吐下泻,闫玉兰整夜守在炕边,用粗布蘸着热水给她擦身子;赵砚田更实在,天不亮就去公社粮站排队,就为了换点白面给她改善伙食。 邵红梅在那孔土窑里慢慢扎了根,三人同吃同住,她跟闫玉兰亲得像姐妹,赵砚田也总说“我要是有个妹妹,就该是你这样的”。 可好日子没过上几年,1971年冬天,闫玉兰怀孕了,夫妻俩高兴得在窑洞前种了棵枣树,盼着孩子出生。 谁知道腊月里,闫玉兰生孩子时大出血,拼尽全力生下个男娃,自己却没熬过来。 邵红梅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婴儿,眼泪掉在娃脸上,她给娃取名赵玉刚,想着要替闫玉兰看着他长大。 赵砚田怕她累着,总说“我来带”,可夜里娃哭,还是邵红梅爬起来冲米汤,用棉絮蘸着喂,硬生生把差点没保住的娃养得白白胖胖。 谁能想到,1976年春天又出了事。陕北下了场暴雨,生产队的粮仓眼看要塌,赵砚田拉着邵红梅去抢粮食,就在一根房梁往下砸的瞬间,他猛地把邵红梅推出去,自己却被砸在了底下。 等村民们把他挖出来,他手里还攥着半袋玉米种,最后说的话是“照顾好玉刚”。 那会儿知青返城的通知刚好下来,邵红梅的名字在名单上。 知青点的同伴劝她“你还年轻,回城重新开始,玉刚送福利院算了”,可她看着玉刚熟睡的脸,想起赵砚田夫妇的好,咬了咬牙——她不能丢了这孩子,这是他们用命护下来的根。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邵红梅没躲她妈的鸡毛掸子,只是把玉刚护在身后,等她妈骂累了,才从帆布包里掏出两样东西:一张皱巴巴的烈士证明,上面写着“赵砚田同志因公牺牲”;还有一只没做完的小虎头鞋,是闫玉兰生前给玉刚做的,针脚还歪歪扭扭的。 “妈,这不是我的娃,是赵大哥和闫姐的娃”,邵红梅声音发颤,把七年的事慢慢说——说他们怎么给她留白面,说闫姐怎么守着她生病,说赵大哥最后那一下推…… 她妈手里的鸡毛掸子“啪嗒”掉在地上,抓起那张烈士证明,又摸了摸玉刚冻得发红的小手,突然抱着娃就哭了“苦命的娃,姥姥对不住你”。 第二天一早,邵红梅她妈就扯了块新布,坐在院里给玉刚缝衣裳,街坊邻居再议论,她就杵着拐棍骂回去“这是我亲外孙!他爹娘是救集体的英雄!” 后来邵红梅在街道工厂糊纸盒,哥嫂也总来帮着带玉刚,再后来,她遇到个不嫌她带娃的铁路工人,俩人搭伙过日子,对玉刚跟亲儿子没两样。 20年后,1997年清明,已经考上大学的赵玉刚跟着邵红梅回了赵家沟,在两座孤坟前“咚”地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头。 邵红梅看着他,想起当年在窑洞前种的枣树,突然明白——有些承诺,真的能守一辈子;有些情分,比血缘还重。 现在再提这事,有人会问“值得吗?”可邵红梅总说“不是值得不值得,是我该做。他们给了我在黄土地上的家,我得给他们的娃一个家”。 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道理:你对我好,我就记一辈子,哪怕要扛着全世界的不解,也得把这份好,好好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