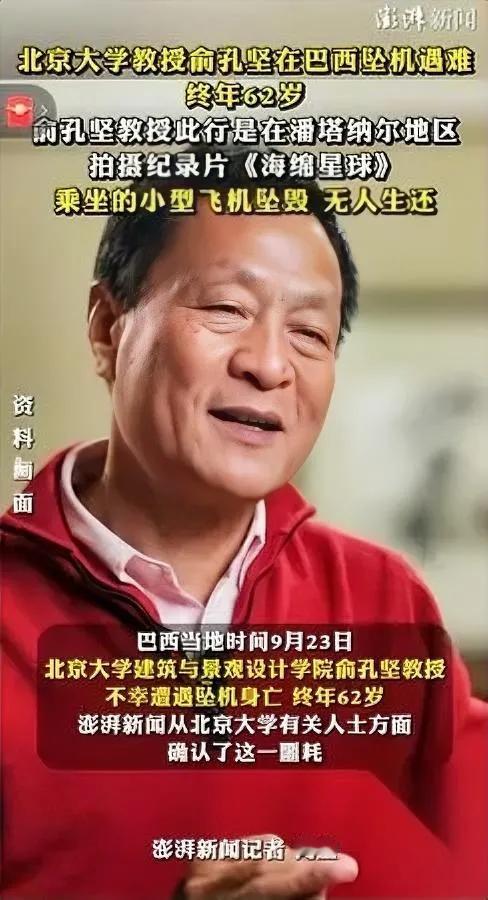我突然懂了 什么叫“天塌” 不是北大少了个教授,是一群学生的“光”灭了。 俞孔坚老师走的那天,他的硕士生小夏发了条朋友圈:“早上刚收到他寄的桂花糕——说我调研时总饿肚子,现在快递还在驿站,他却不在了。” 很多人说“换个导师就行”,可俞老师的学生都明白:他不是“指导你写论文”,是“把你的每一步都放在心上”。去年有个学生做湿地保护项目,熬夜改了八版方案还是通不过,俞老师拿着保温杯坐在他对面,说“我们去湿地待一天吧”——两个人蹲在芦苇丛里,看水鸟飞过来,俞老师指着说:“你写的不是‘生态指标’,是这些鸟的‘家’,要让方案‘会说话’。”后来那个方案拿了奖,可现在学生翻开方案里的批注,还能看到俞老师写的“再加句当地老人的话,更暖”。 早几年他评院士时,有人说他“太接地气”,可他跟学生说:“做景观的,先得把脚踩进泥里,再把心贴进人里。”现在这群踩过泥的学生,再也听不到那句“走,我陪你再去趟村里”了。 最疼的不是“要重新磨合”,是你刚摸到学术的“温度”,那个教你“怎么发热”的人,突然不见了。就像你学做饭时,后面站着个老人,你盐放多了,他不说“错了”,而是笑着递杯水:“没事,加点糖,照样好吃”——现在你做对了菜,却再也没人拍着你肩膀说“嗯,有我的味儿”。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导师?就是那种“把你的事当自己的事”的人?俞老师的学生现在改论文时,会不会想起他说“批注要红笔写,显眼,你能一眼看到”?会不会对着电脑里的聊天记录发呆:“昨天还在问我‘调研累不累’,今天就没了回音”? 俞孔坚 其实我们都懂,有些“光”灭了,可它留下的温度,会一直暖着那群学生——就像俞老师说的,“景观是有记忆的”,而他的学生,会把他的“温度”,写进每一个方案里。你们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