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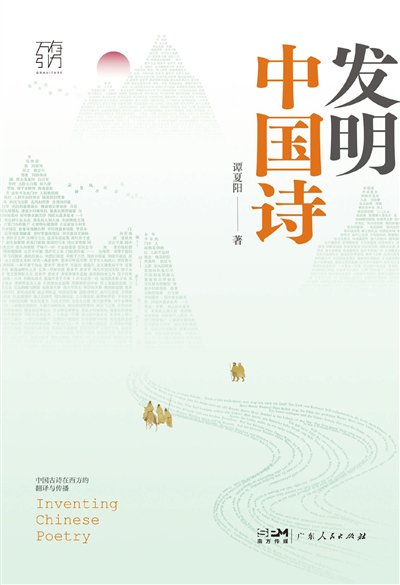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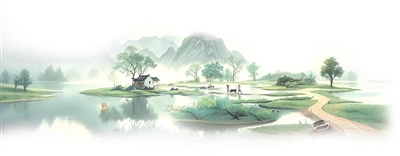
1913年至1915年的三个冬季,埃兹拉·庞德与叶芝同住在“石屋”——位于苏塞克斯的一座乡间别墅,距离伦敦需乘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周围环境幽静,适合读书写作。当时,叶芝得到一笔皇家补助金的资助,他邀请庞德来做他的秘书,帮他处理一些信件与公文,关键是他们有时间在一起讨论诗歌。
庞德此时正在阅读法文版的《四书》,儒家思想开始浸淫着他,使他感到“东方似乎正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他的预感得到了应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直接走进了“中国”。
那时庞德与妻子多萝西新婚不久,由于处于战争期间,“石屋”周边的荒地成了士兵的训练场。庞德是外国人,作为妻子的多萝西被警察限制前往“石屋”居住,大多数时间她居住在伦敦,因此庞德不时会去伦敦与妻子团聚,兼且访友。正是在伦敦萨洛姬妮·奈都夫人的家中,他认识了女诗人玛丽·麦克尼尔·费诺罗萨——她的另一重身份是诗人、东方学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遗孀。
这个欧内斯特·费诺罗萨大有来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到东京大学任教,从此改攻东方学,对中国文化相当关注,曾让朋友为他搜集中国早期的绘画作品。1890年费诺罗萨应聘返美,出任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东亚藏馆的馆长。1894年,他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美国第一次中国画展,开启了美国对东方艺术的研究。
1896年至1900年,费诺罗萨再次到日本游学,向有贺长雄、森槐南等著名学者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诗歌、诗剧,并做大量的笔记。1903年,费诺罗萨在美国作巡回演讲,演讲主题是“中国风景画与诗歌的关系”。1908年费诺罗萨和妻子玛丽访问伦敦,不料其心脏病突发,于当年9月在伦敦去世。1912年,玛丽整理出版了费诺罗萨的遗作《中日艺术史》,但他的笔记作为原始手稿没法出版,比如里面的中国诗笔记,每首诗标有原中文、日文读音,以及写上每个字的译义和全句串解,由于内容过于庞杂和潦草,如果不经过细心整理,外人根本无法读懂。
玛丽希望找到一位合适的诗人和她已故的丈夫来“共同翻译”。
庞德与玛丽初次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庞德的谈吐,特别是他对东方文化所流露出来的浓厚兴趣给玛丽留下了良好印象。她后来读到庞德的一些诗歌作品,在大加赞赏之余,认为庞德“关注的是诗歌,而不是语言学本身”,因此认定他就是“能够像我先夫所愿的那样处理他的笔记的唯一人选”,最终决定将笔记托付给他。
回到美国之后,玛丽从美国亚拉巴马州费氏老宅给庞德分批寄去了费诺罗萨的成箱遗稿,那时是1913年底。收到笔记的庞德如获至宝,用激动的心情给老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写信:“我从费诺罗萨遗孀那里得到了费诺罗萨的宝贵‘财富’”。
1914年整整一年时间,他几乎足不出户,埋头整理笔记,展开翻译中国诗的工作。
首先的工作是淘选。费诺罗萨的笔记太过于庞杂,在耶鲁大学的珍本馆里,就藏有费诺罗萨的笔记总共21本,包括汉语、中国思想、中国诗、日本诗、能剧等多个主题。
庞德主要挑选了笔记中关于中国诗的部分进行翻译。他从150多首诗中选取了19首编入《神州集》,仅占不到十分之一,分别为:《诗经·小雅》中的《采薇》、汉乐府民歌《青青河畔草》和《陌上桑》、陶渊明的《停云》、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郭璞的《游仙诗》,以及李白的《江上吟》《长干行》等12首诗。其中,庞德把《江上吟》与《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两首诗连在一起,当成一首翻译了。
为什么庞德会如此选择呢?
尽管当时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知之甚少,但他有自己的取舍标准。在选取的19首诗当中,抒写忧苦哀愁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比如《采薇》写的是战乱之苦愁,《长干行》和《玉阶怨》写的是闺妇之怨愁,《送元二使安西》《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写的是离别之思愁。经过改译加工之后,整个集子的主题向“悲愁”做了一次靠拢和强化——这也是这批中国诗最具“现代性”或者暗喻现实的地方。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也写愁,不过这种愁更多倾向于一种压抑的变相宣泄。在《神州集》中,庞德有意将“悲愁”的主题放大,这与当时意象派运动的诗学需求有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多利亚浪漫主义诗歌渐趋式微,空泛、抽象、藻饰而矫揉造作的抒情诗充斥着英国诗坛。在美国,拙劣地模仿英国诗的所谓高雅派诗人,创作出来的都是一些无病呻吟、过度宣泄的作品,可谓是浪漫主义的末流仿制品。庞德对此深恶痛绝。其实当时,英美诗坛所面临的危机他也了然于胸,并且一直在寻找解决之道,而他的意象主义诗学理想已初具雏形。为此,庞德试图以中国古典诗的言愁方式来纠正美国诗歌的积习流弊,来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进而为正在成长中的意象派诗人树立一种“悲愁”主题的诗歌典范。
中国式“悲愁”诗有着自身的形象特点。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往往将普通人的真挚情感与日常生活的细节相融合,从而达到最大的形象化。这与浪漫主义局限于歌唱自然与心灵,表现抽象无主的情绪,也与唯美主义仅停留在诗意空间内空洞地赞颂美与永恒,有着天渊之别。即是说,诗歌在表达情感的时候,注重的是具体细节与真实朴素,而不是浮泛的抒情。还有一点就是含蓄:以比兴为美学特征的中国古典诗,将客观意象的塑造作为言志抒情的自觉手段,通过外部物象的呈现,含蓄地指向内心感受,这正是有别于浪漫主义诗歌直接倾吐咏叹之处,也是与庞德的意象派理念共鸣最深的一点。
在庞德看来,中国古典诗更具现代性和启示性,他在那些诗篇里发现了合乎他需要的东西——以上就是他深层次的选题动机所在。
接下来,庞德便开始了“翻译”。这种“翻译”是带有再创作性质的,艾略特称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这里的“发明”有着双重含义:第一,是创造性的改译;第二,为英诗带来一种迥异于以往的新鲜句法结构。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许多句子都存在着意象并置的现象,例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典型的要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些诗句里,意象词或词组之间只是并列地排列出来,也无需动词或介词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式,然而又很简洁、直接,让人一目了然。
虽然庞德当时并不了解汉语诗句的构成,但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译诗时,他刻意将部分英文语法成分给省略掉,尽量去靠近或还原中国古诗的句法结构,比如省略英文中的谓语动词等,主要是为了隐去译诗中意象间的逻辑关系,以营造出一种与原诗相类似的美学效果。这样的译文采用一种“短语节奏”,简洁而含蓄,超越了传统英诗中的节奏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古典诗歌那种个人瞬间的体验,转化为普遍、恒常经验的诗意境界——这样的英语诗歌,在传统的英语世界里无疑是一种奇特的存在。
即是说,庞德通过翻译间接改造了传统的英语句法,其译诗由此在英诗的语境中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这样的翻译当然是独具创造性的。
1915年《神州集》出版之后,立即在西方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直到如今,评论界的论调颇为一致:“《神州集》是庞德出版的诗集中最为出色的一本。”其中,墨西哥大诗人帕斯对庞德的翻译评价十分精当,并且富有历史眼光:
庞德的诗是否忠实于原作?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正如艾略特所说,庞德“发明”了英语的中国诗歌。从中国古诗出发,一位伟大的诗人复活并更新了它们,其结果是不同的诗歌。不同的——却又正是相同的。庞德为数不多的翻译,却在很大意义上开创了英语现代诗,以及其他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在对西方诗歌传统的反思中,庞德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传统。
(作者为诗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