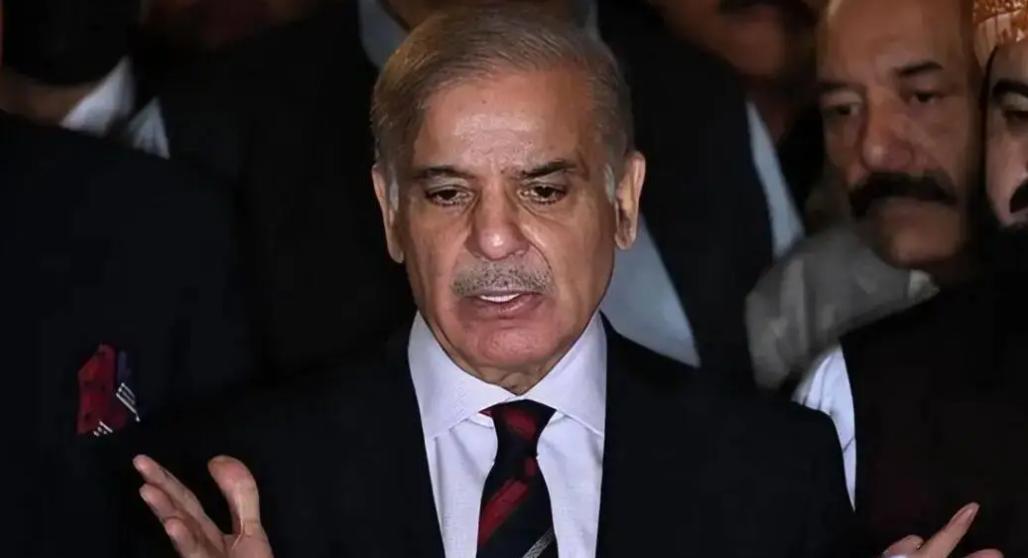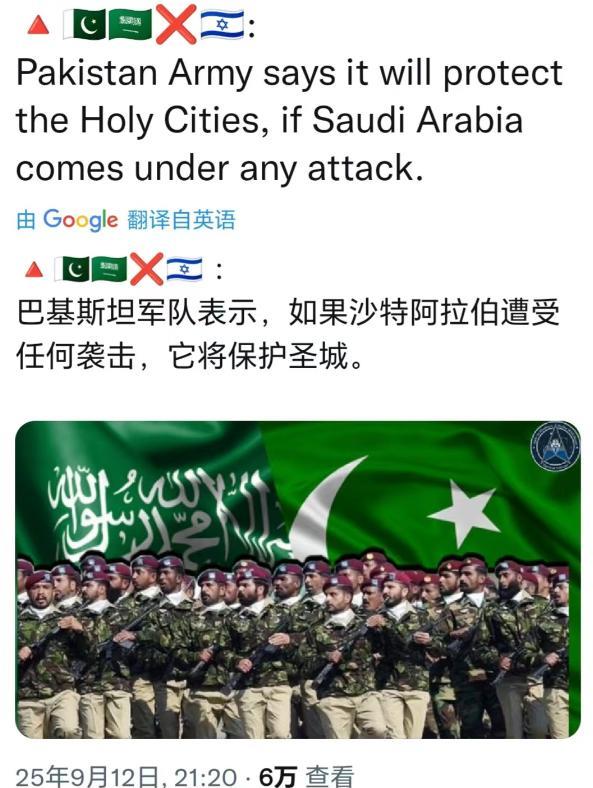尼泊尔的“耻辱”——巴迪种姓“世袭”卖淫! 在尼泊尔西部农村,经常能见到十几岁的女孩裹着旧纱丽坐在村口路边,看到路过的卡车或拖拉机就默默起身,中年妇女守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前,眼神麻木地等着能换几斤大米的客人。 这些巴迪种姓女性,从出生起就被绑在“世袭”卖淫的链条上,在这个以佛教平和、雪山纯净闻名的国家里,她们的苦难成了被刻意忽视的耻辱印记。 这种代代相传的悲剧,不是因为命运无常,而是被历史和制度牢牢钉死的结果。14世纪时,巴迪人的祖先还在印度比哈尔地区靠弹唱歌舞谋生,是能给人带来欢乐的民间艺人。 可18世纪尼泊尔统一后,种姓制度被强行加固,到1854年颁布的法典里,巴迪人被直接划为“不可接触者”。 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拥有一寸土地,不能走进学校读书,甚至连挑水的水井都要和高种姓人分开用。 从那以后,巴迪男人只能靠扛石头、修山路这种最苦的零工糊口,一天赚的钱还不够买半袋面粉;女人则被逼着用身体换生存资源,这种“谋生方式”像家族手艺一样,从母亲传给女儿,再传给孙女。 在村里,巴迪人的日子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取水要走两三公里到河边,因为村里的水井被高种姓人占着,他们说“巴迪人的手碰过的水会脏”。 去集市买东西,摊主会用破报纸裹他们的东西,收的价钱比别人贵两成,还得等所有高种姓人买完才能轮到他们。 生病更是煎熬,诊所医生看到他们来,要么说“没药了”,要么直接锁门。有记录显示,2017年有位巴迪孕妇宫缩时跑了三家医院,都被门卫拦在门外,最后在路边生下孩子,婴儿没活下来。 这样的事,在巴迪社区里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却很少有人真正关注。 对巴迪女性来说,身体是唯一能换钱的“资产”。她们大多从十三四岁开始接客,客人多是跑运输的司机、附近的低种姓农民,每次能拿到的钱只够买两三斤大米。 为了养活家里的老人和没成年的孩子,有些女人一天要接四五个客人,连生理期都不敢休息。长期下来,几乎所有巴迪妇女都有妇科病,却没钱去看医生,更别说做体检。 村里的老人说,她们很少有能活过45岁的,比村里其他种姓的女人要早走十几年。而这种生活是她们的“常态”。 小女孩看着母亲接客,听着大人说“这就是你的命”,慢慢就接受了这种未来,她们中的大多数,小学没读完就会辍学回家,等着“长大懂事”后接过母亲的活计。 这些年,外界开始注意到巴迪人的困境,也有过一些改变的尝试。2005年,尼泊尔最高法院判政府必须给巴迪人发身份证,让他们的孩子能正常上学;2007年巴迪人上街抗议后,政府还承诺分土地、教手艺。 可到了实际执行时,这些承诺大多成了“空话”。 分的土地全是山坡上石头多的地,种不出庄稼,只能长些野草;国际组织来教她们做裁缝、编竹篮,可做出来的东西拿到集市上,人家一听是巴迪人做的,连看都不看。 2025年初,政府成立了专门处理种姓问题的办公室,说要严查歧视行为,可在西部农村,实际情况没什么变化。 尼泊尔青年基金会在一些村子搞了种姓平等项目,帮巴迪孩子争取上学机会,教她们学电脑、做手工。项目报告里写着,2024年有237名巴迪孩子顺利读完小学,其中32人考上了初中。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却是过去十年里最多的一次。还有些国际组织帮巴迪妇女搞有机种植,联系城里的超市收购蔬菜,虽然赚的钱不多,但至少不用再靠接客生活,有些妇女说“现在睡觉能踏实些了”。 可这些改变太微弱,抵不过根深蒂固的偏见。在很多村子里,高种姓人家还是不让孩子和巴迪孩子一起玩,学校里老师会用粉笔画线,让巴迪学生坐在最后面。 就连医院,虽然不敢明着拒收,但给巴迪病人看病时,医生会戴两层手套,看完后还会反复洗手。这些细节里的歧视,比法律条文里的禁止规定更伤人,也更难改变。 巴迪妇女们也在悄悄努力。她们自己凑钱成立了互助小组,谁家有人生病就一起凑医药费,谁家孩子没人管就轮流照看;有些学会手艺的妇女,会把技术教给更多姐妹,希望大家能多一条路。 只是要真正打破这种“世袭”的苦难,光靠这些还不够。法律能禁止种姓歧视,却管不了人心里的偏见;政府能承诺政策,却保证不了每个村子都落实。 现在尼泊尔城市里已经很少能看到明目张胆的种姓歧视,可在西部农村,那些看不见的界线还在分割着人们的生活。 巴迪女性的苦难,像一道疤痕,刻在尼泊尔的社会里。要抹去这道疤痕,需要的不只是政策和项目,更是每个人心里对“平等”的真正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