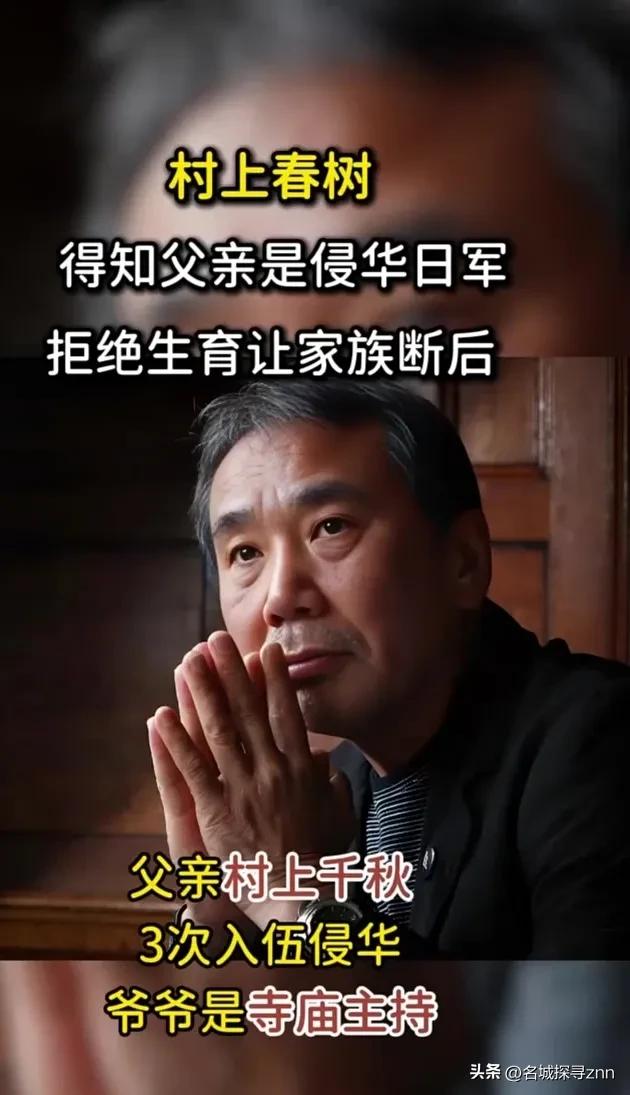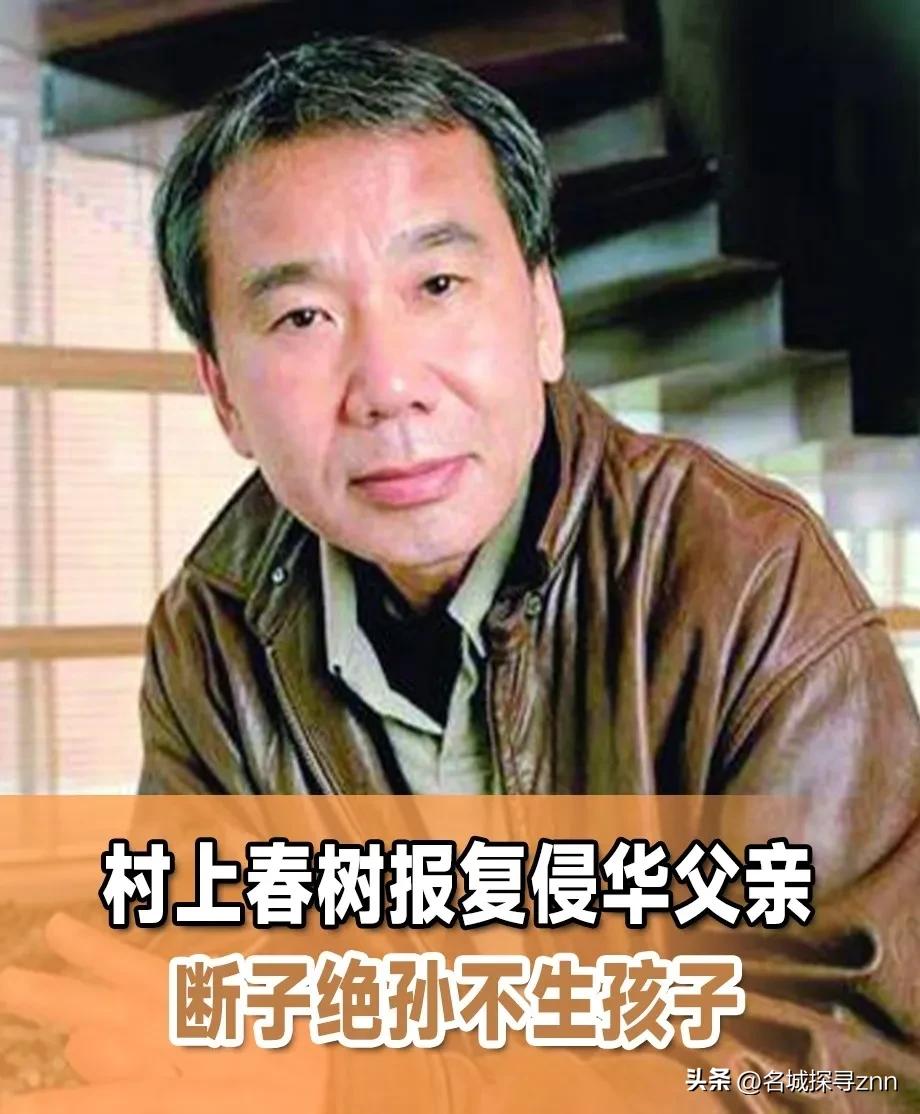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样的血脉,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很多人不知道,村上春树小时候其实常听父亲聊起战争,但父亲从来只说自己“在中国大陆待过几年”,语气里总带着说不清的沉重,却从没提过具体做了什么。那时候他年纪小,只觉得父亲是“去过远方的人”。 直到1970年他21岁,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翻到一本关于侵华战争的史料集——里面有关于日军侵占华北村庄、掠夺物资的记载,还有平民被伤害的照片,他盯着那些文字和图片,突然就想起父亲偶尔夜里惊醒时,嘴里念叨的“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才慢慢拼凑出父亲当年的经历: 父亲是1939年被征召入伍的,分配在华北方面军的后勤部队,负责给前线运输弹药和粮食,虽然没直接参与战斗,却亲眼见过战友闯进村民家里抢东西,甚至把村民的耕牛牵走,他没敢阻止,只能在夜里偷偷给村民塞点自己剩下的干粮。 从那天起,村上春树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他第一次主动问父亲“当年在大陆到底做了什么”,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句“那时候身不由己,可做错的事,就是做错了”,然后就红了眼。 那天晚上,村上春树在日记本上写了满满三页:“我知道父亲可能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被国家逼着上战场,可他毕竟是侵略者的一员,那些因为战争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人,他们的痛苦难道会因为‘身不由己’就消失吗?”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刻意避开中国菜——不是讨厌味道,是每次看到餐桌上的中餐,就会想起史料里那些没饭吃的村民,想起父亲可能参与过的掠夺,觉得自己“没资格安稳地享用这些”。 有次出版社的编辑请他去东京一家很有名的四川菜馆,他站在餐馆门口犹豫了半小时,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声音有点哑:“我吃不下,一想到那些可能连热饭都吃不上的受害者,我就觉得自己享受这些是种冒犯。” 关于不生孩子的决定,他其实纠结了很多年。年轻时他和妻子阳子也讨论过要不要孩子,阳子知道他的顾虑,说“孩子是无辜的,不该替上一辈的错买单”,可他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 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隐晦提过这件事:“我害怕孩子长大以后,有人指着他说‘你爷爷是侵华日军’,更害怕孩子自己了解历史后,会因为祖辈的过错陷入自我否定。我已经承受了这份愧疚,不想再把它传给下一代。” 他不是觉得“血脉是恶魔”,是太清楚这份血脉背后连着的痛苦——那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破碎,是无法弥补的历史伤痕,他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背着这样的“包袱”,更不想让这份可能带着“暴力记忆”的血脉继续延续。 很多人觉得他的做法太极端,甚至说他是“自我惩罚”,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把这份愧疚全融进了写作里。 《奇鸟行状录》里,他写主角在“井底”寻找真相,其实就是在隐喻自己对父亲战争经历的探寻;《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里,对“过错与救赎”的讨论,藏着他对历史责任的思考。 他还多次在采访中直言“日本必须正视侵华历史,不能把战争的暴力美化成‘解放’,更不能篡改教科书”,甚至因为这些话被日本右翼攻击“不爱国”,可他从没改口,说“爱国不是替错误遮羞,是有勇气承认错了,然后努力弥补”。 他其实也明白,父亲当年或许有无奈——那时候日本年轻人被军国主义宣传裹挟,很多人以为“参军是为了国家荣耀”,等上了战场才知道是侵略。 可他更清楚,“无奈”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就像他在随笔里写的:“就算父亲是被逼迫的,那些被伤害的人,他们的痛苦不会因此减少半分。我能做的,就是不回避这份血脉里的‘污点’,用自己的方式去承担责任。” 他不吃中国菜,不是对中国的排斥,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他不生孩子,不是对自己的否定,是对下一代的保护——他不想让孩子再经历这种“一边是亲情,一边是历史罪恶”的撕裂。 后来有人问他“会不会后悔这个决定”,他摇了摇头,说“我只后悔自己没能为那些受害者做更多”。 这些年,他一直默默资助着致力于中日战争历史研究的机构,还把自己部分版税捐给了战争遗孤援助项目,他说“我知道这些做不完弥补,但至少能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村上春树的选择,从来不是简单的“自我惩罚”,而是一个清醒者对历史的敬畏,对受害者的歉疚。 他用自己的方式提醒着所有人:历史不是过去的故事,是活着的记忆;承担责任不是为了沉溺于愧疚,是为了不让那些痛苦的经历,再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