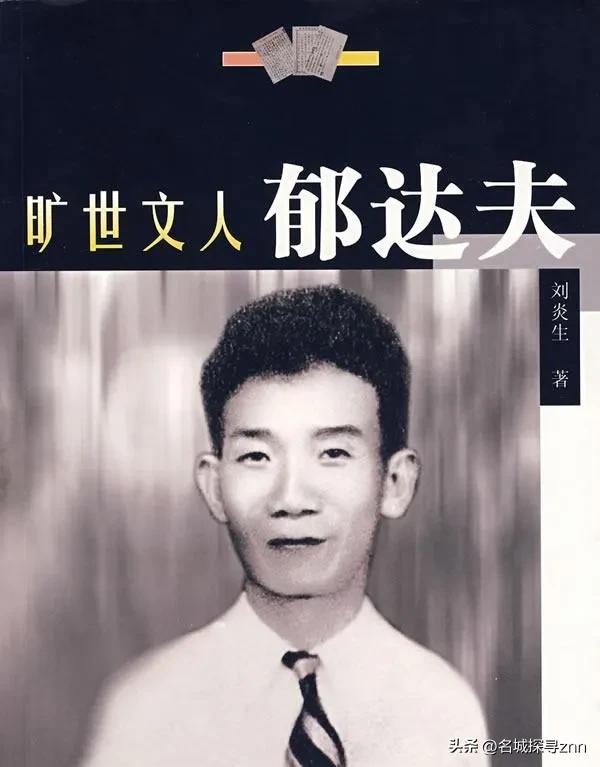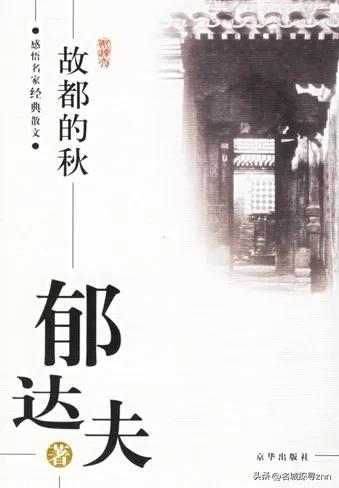1949年9月,有人在苏门答腊的丛林里发现了一具中国男子的尸体。经过辨认后,确认此人正是“以笔为枪”的爱国文人…郁达夫。 1931年的杭州,春寒还未散尽。酒馆里,35岁的郁达夫正和朋友推杯换盏。突然,一个消息传来,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决 那天酒馆里的喧闹一下子就静了。 郁达夫手里的青瓷酒杯“哐当”砸在地上,酒洒了一地,碎片溅到他的布鞋上,他却像没感觉一样。朋友想扶他坐下,他猛地甩开手,声音发颤:“龙华?秘密枪决?他们才多大年纪!” 胡也频他见过,去年在上海左联的会上,那小伙子握着他的手说“郁先生,您的《沉沦》让我敢写真话”;柔石还寄过稿子给他看,字里行间全是对底层人的同情。这些鲜活的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从那天起,郁达夫的笔锋变了。之前他写《沉沦》里青年的苦闷,写《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底层挣扎,文字里带着个人化的愁绪;可从1931年夏天开始,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全是带着火的呐喊。 他写“文人不能只躲在书斋里叹苦经,要把笔当成刀,割开这黑暗的口子”,写“左联的青年没白死,他们的血要让国人看清,什么是真正的敌人”。 有人劝他“小心点,别得罪人”,他却把这话登在文章里,说“怕得罪人,就别当爱国的文人”。 1937年夏天,上海的炮声响了。郁达夫把家里的字画、书籍打包寄回老家富阳,只带了一个装着换洗衣物和笔砚的小箱子,就往福建走。 当时他在福建省政府当参议,可没待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天天往各地跑——去厦门的码头动员华侨捐钱捐物,去泉州的学校给学生讲抗日,甚至跟着运输队往前线送物资。 有次在漳州遇到日军飞机轰炸,他把身边的孩子护在身下,自己的胳膊被弹片划了道大口子,血流了满袖子,他却笑着说“这点伤,比左联青年的血轻多了”。 1941年,香港也待不住了。日军占领香港前,郁达夫跟着一批文化人往东南亚撤,最后在印尼苏门答腊停了下来。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改了个名字叫“赵廉”,在当地一所华侨学校当老师,教孩子们中文。课堂上,他不只会教“人之初,性本善”,还会偷偷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把“还我河山”四个字写在黑板上,让孩子们一遍遍地念。 课后,他会把华侨们聚起来,说“国内在打仗,咱们在这儿不能看着,多捐一分钱,前线就多一颗子弹”,他自己更是把教书赚的钱全捐了出去,家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可这样的日子没藏住多久。1944年,日军在苏门答腊开始清查抗日分子,郁达夫之前帮华侨传递情报、支援国内的事被人告发了。 1945年8月29日晚上,几个日本宪兵闯进他的住处,把他架走的时候,他还在给学生批改作业,桌上摊着没改完的作业本,上面有他用红笔写的“有志气”。 邻居后来回忆,他被架走时没喊没闹,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黑板,像是在看那几个“还我河山”的字。 日军没说要把他带去哪里,也没说要干什么。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大家才发现郁达夫不见了,华侨们四处找,找了四年都没消息。 1949年9月,一个当地的农民在苏门答腊的丛林里砍柴,发现了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身上还穿着一件中式的对襟衫——那是郁达夫常穿的衣服,口袋里还有一支他用了多年的钢笔,笔帽上刻着一个“郁”字。 经过辨认,确认这就是失踪四年的郁达夫,而杀害他的,正是当年绑架他的日本宪兵,他们怕郁达夫泄露情报,在投降前把他秘密杀害,扔在了丛林里。 从1931年听到左联五烈士牺牲的那天起,郁达夫就没再为自己活过。他的笔,从写个人苦闷变成了抗日的号角;他的人,从书斋里的文人变成了奔波的救亡者。 他到死都没放下“爱国”这两个字,哪怕死在异国的丛林里,哪怕尸体四年后才被发现,他的骨头里,还是带着中国文人的风骨。后来有人说,郁达夫是“以笔为枪,以身殉国”,这话没错——他的笔唤醒了无数人,他的命,献给了他最爱的国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