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小说成为人生的试验场,冒险家与上班族站在同一座山下。雪山与社保,星辰与职级,鲜明对峙。
小说集里,一半是作为冒险家的普通人,在身体上克服地心引力,却逃脱不了社会框架的牵引;一半是作为普通人的冒险家,被固定在两点一线和朝九晚五,却在日常生活的平静角落,经历心理层面的非凡历险。
二者合一,共同指向普通人的存在: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人都要面对本质上的无聊,面对内心深处细小的恶、微弱的善,面对种种两面煎、两不舍、既要又要。无数一念之差,组成我们生命中的顿悟时刻,是命运的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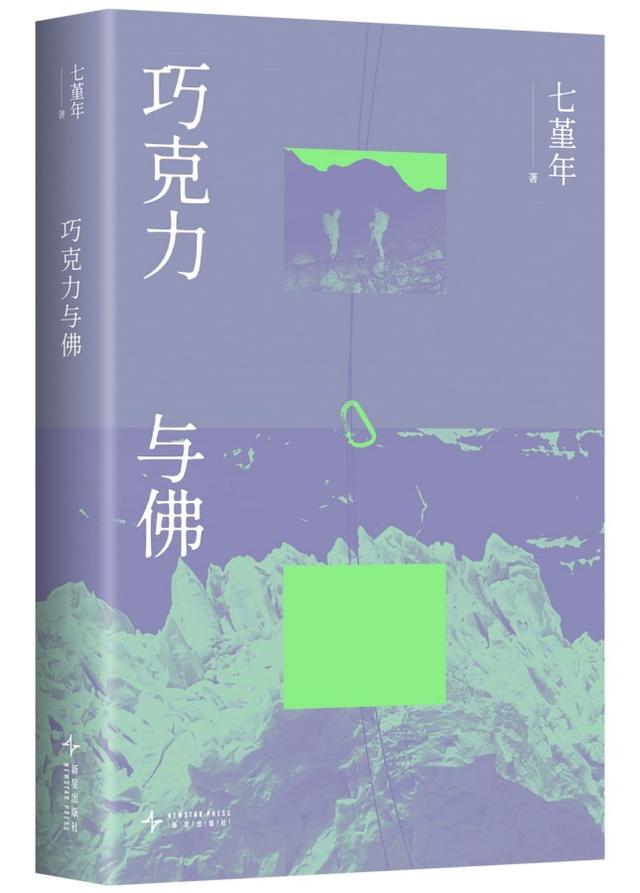
《巧克力与佛》,七堇年著,新经典|新星出版社2025年出版
>>内文选读:
自序(节选)
写作20年来,我已经从一个敏感而困顿的青少年,变成了那个“以山为乐”的作家。写作仍然是我的精神静脉,但在写作之外,我的动脉全都流向了山地运动——滑翔伞、攀岩、攀冰、登山、洞穴探险——它们是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没法合上。这样来说,也许可以打翻你对一位女性作家的刻板印象。
“攀岩是一种享受失败的运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心中震撼不已。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学会“享受失败”,我所在的文化中,也鲜有对失败的拥抱或肯定。那几年,我正身陷存在危机、虚无泥潭,感到一切都没有意义,活着也没有乐趣。我凭直觉走向自然,寻求答案,进而深入了一系列户外运动,从洞穴探险、滑翔伞到攀登……它们给了我存在意义上的出路和解脱。
在某次攀岩的下午,一个疲惫的“巧克力瞬间”,突然顿悟:既然我可以如此毫无功利心地热爱一项运动——哪怕它毫无意义、百无一用,自己注定成不了高手,仍然乐此不疲——那我还有什么“无意义”不能接受?
人生就像阿尔卑斯式攀登:亲力亲为,无有代者。终点是确切的,乐趣在于选择哪一条路,以怎样的方式上去。恰如攀登家刘洋老师所说:“攀登也是一种创作。”
辛辛苦苦上去(或不一定能上去),仅在顶峰停留一瞬就立刻下撤,什么也不图,就图个过程。每位高手都是这样:注定要身怀绝技地离开这个世界,但在离开之前,就要花费一生,认认真真,练就一身绝活。

图源:视觉中国
但何止是运动员呢?每个人不都是如此。山教会我的,正是如何从容面壁,彻底接纳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与此同时,倾尽全力而上。
生活是含糊的自我调适,而攀登是确切的自我肯定。与写作的主观性与模糊性相比,运动的成就感是确切的:一场马拉松,完赛了就是完赛了;一座山峰,登顶了就是登顶了;岩壁上的一条线,拿下了就是拿下了。这种确切的正反馈,以及运动过程中的心流感,如此迷人,让我欲罢不能。
所谓心流感,无非就是极致的专注、忘我,以至于完全感觉不到时间的状态。全身心溶解于当下,溶解到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中去。
我常觉得这种“哪点儿没对”又说不上来“是什么不对”的悬置状态,代表着现代人的普遍困境。不仅是登山者,任何人都处于一套社会定义的攀爬系统中:从讲师到院士,从墩子到厨师长,从P4到P8,是系统就有系统困境。户外人是这类困境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类:他/她显然心怀一个自由本真的世界,但又通常困于城市中,要对付工作、生活琐事、亲密关系,面临主流价值观的审视。
我想问题本质还是关于“存在”:一个不想被外在标准定义的现代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存在。在这过程中,户外运动只是一条路径,一条赋予自我价值的路径。
正因为以上的个人经历与思考,才有了这本小说集中的人物。

七堇年
栏目主编:朱自奋文字编辑: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