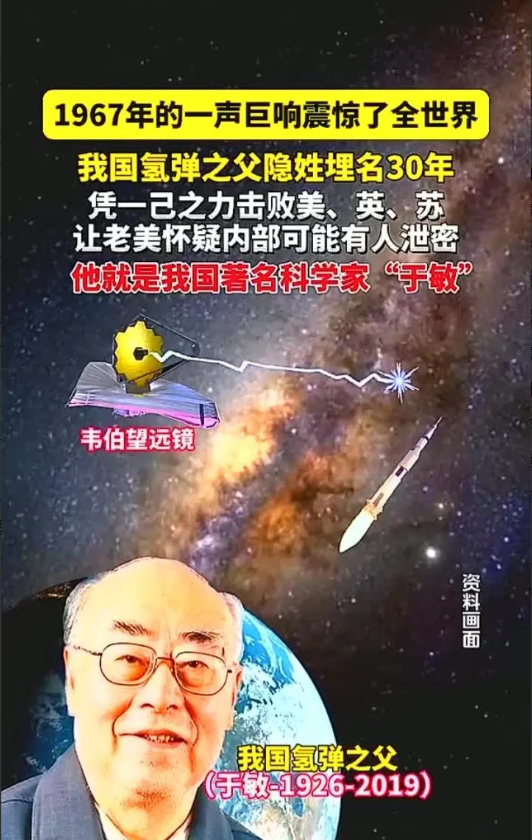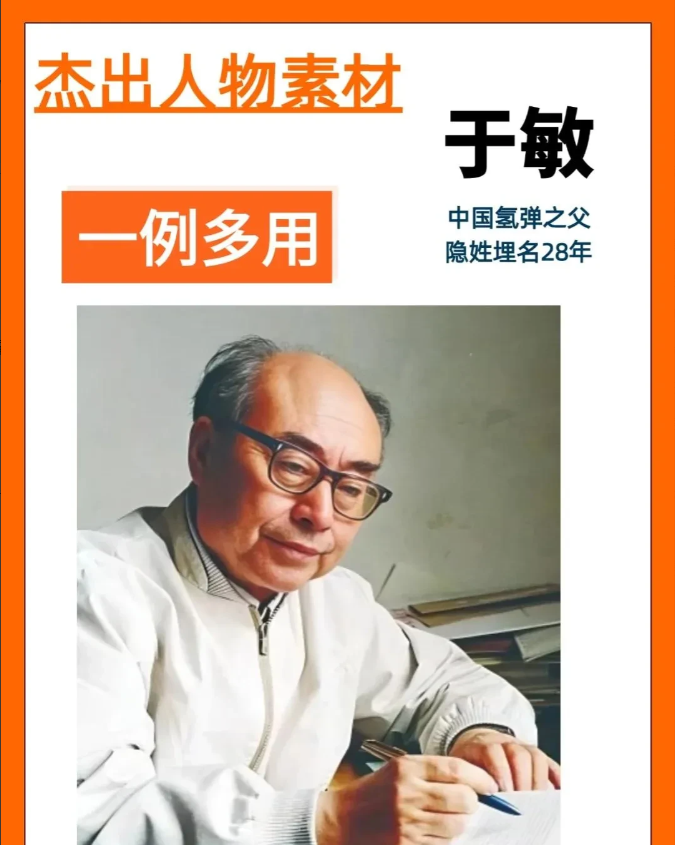于敏的超级大脑有多厉害呢?
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杜祥琬院士在一次采访时说:“有一次,我们和于敏在看核装置物理量的纸带,于敏突然就说这个量错了,这个得求助于华东计算所的同志们。 你可能不知道,那时候看的核装置物理量纸带,可不是普通的纸条。
每一条纹路、每一个脉冲信号,都是核反应过程的‘密码’,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数据分析系统,全靠人工对着纸带一点点核对,一个数字错了,整个核试验的预判都可能出偏差。
杜祥琬院士后来还提过,那天在青海221厂的实验室里,阳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一长卷米黄色纸带上,大家围着桌子看了快两个小时,没人发现异常,于敏只是蹲在旁边,手指顺着纸带上的刻度慢慢滑,突然就停住了。 他当时没大声说,只是把纸带往中间2挪了挪,指着其中一段对身边的人说:“这里的脉冲间隔不对,比理论值差了0.3微秒。”
在场的人都愣了,有人赶紧翻出厚厚的计算手册核对,算来算去没找出问题,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纸带打印时出了机械误差。
于敏没争,只是把自己的演算本递过去,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推导公式,最后一行标着“需复核初始参数输入”——那时候华东计算所承担着核数据的主要计算任务,用的是国内当时最先进的J-501型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能到1万次,但即便这样,也需要人工先输入参数,再等机器出结果。 华东计算所接到消息时已经是傍晚,工程师们连夜复查,直到凌晨三点才发现问题:输入时把一个中子截面参数的小数点后第三位输错了。
后来所长专门给221厂打了电话,说“于敏先生这双眼睛,比计算机的校验程序还准”。
没人知道,于敏为了熟悉这些数据,每天睡前都会把关键参数记在小本子上,走在路上、吃饭时都在默默背,时间长了,哪个参数对应哪个反应过程,哪个数值范围才算正常,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更让人佩服的是,于敏原本是学理论物理的,1961年接到调令转行搞核物理时,连核装置的实物都没见过。
他从北京出发去青海时,只带了两箱书和一摞演算纸,火车走了三天三夜,他就在车厢里对着公式推导。到了221厂,住的是土坯房,冬天没有暖气,晚上演算时手冻得握不住笔,他就把双手揣在怀里捂热了再写。
有次同事发现他的演算本上沾着血,问他怎么了,他才说刚才演算太投入,铅笔头戳破了手指都没察觉。 杜祥琬院士还回忆过另一件事,1967年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前,大家对着计算结果反复核对,有个数据始终存在微小偏差,没人敢拍板。
于敏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出来,出来时拿着一叠演算纸,说“问题出在辐射输运过程的忽略项上”,按照他修正后的公式重新计算,结果和理论值完全吻合。
后来试验成功,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时,于敏站在观测点,手里还攥着那张写满公式的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那时候他已经三年没回过家,妻子给他寄的家书,他都没时间拆。 于敏的“超级大脑”,从来不是天生的天赋,而是把国家需要刻进骨子里的坚持。
那时候国外对我国核技术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他就从最基础的理论开始啃,把上千万个数据记在脑子里,再通过无数次演算找到规律。
有人算过,他这辈子用过的演算纸,叠起来能比罗布泊的沙丘还高,而每一张纸上的公式,都藏着他为国家筑牢核盾牌的决心。 如今再提起那段岁月,杜祥琬院士总说:“于敏先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厉害不是有多聪明,而是能把聪明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那些曾经被他纠正过的数据、完善过的公式,如今都成了我国核科学领域的宝贵财富,而他的“超级大脑”背后,是一代科研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子之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