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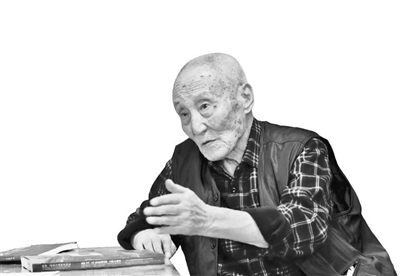
□李卓然靖广生
新闻背景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原名“奉天俘虏收容所”,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地坛街30-3号,其设立时间可追溯到二战期间。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次日美、英等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美、英等国实施“先欧后亚”政策,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遭受重大失利,日军迅速占领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等地,俘虏了大批盟军官兵。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是二战期间的日本在沈阳设立的一处专门用来关押太平洋战场上所俘获盟军战俘的战俘营,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中心战俘集中营,被称为“沈阳盟军战俘营”,也被称作“东方的奥斯维辛”。从1942年11月11日至1945年8月15日,共关押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法国和新加坡等盟军战俘2000多名。1942年11月11日,第一批到达沈阳的盟军战俘被关押在位于北大营的“奉天俘虏收容所”临时营区。1943年,为便于关押和利用战俘,日军建立了一座近5万平方米的新战俘营,即现存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盟军战俘在战俘营中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待遇。日军驱使美国战俘在劳役区制造军工产品,战俘们经常遭受搜身、掳财、辱骂、人格侮辱、体罚、毒打等摧残。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它记录人类的兴衰更替,记录时代的发展进程,也记录人们难以忘怀的尘封记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更好地收藏抗战历史记忆,向世界传递和平之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联合中共大东区委宣传部,开展口述历史“抢救性”搜集采访、拍摄、梳理工作。今年95岁高龄的关德全老人,是二战期间与盟军战俘在同一座工厂“工作”过的中国劳工,也是在沈阳最后一位健在的、能见证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历史的人。近日,关德全老人接受了采访组的专访。
历史讲述
在“满洲帆布株式会社”做劳工
当采访组到达位于铁西区一个居民小区,对关德全老人进行采访时,他听了我们的来意,做了简单准备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关德全老人虽然听力有些不便,但思维非常清晰,面对采访,老人眼神缓慢移向窗外,他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以生平为经,阅历为纬,揭开了那段尘封80载的跨国记忆。
1930年3月,关德全出生在辽宁省西丰县,他的父母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供他读完了小学,1944年又把他送到沈阳读中学。在沈阳读书期间,由于学校开设了“勤劳奉仕”课,关德全被强行送到一个叫“满洲帆布株式会社”的日本工厂当劳工。“奉仕”是日语服务、效力的意思,就是要求青少年毫无怨言地为日伪效力。所谓“勤劳奉仕”就是日本人采取强制手段逼迫青少年到矿山、工厂、田间、军营等地进行无偿劳动的一种奴役方式,目的是为日本侵略战争提供更多劳动力。
关德全至今还记得当年的遭遇:“工厂和学校就隔着一条马路,每天学校里的教官押着我们这些学生去工厂干活。日本人一边拿着我们家里交的学费和住宿费,一边强迫我们去日本工厂当免费劳动力,干不好还得挨打受罚。”关德全和工友们每天中午在工厂吃饭,“伙食很差,吃的是谷子皮和大白菜,根本不够吃,而且菜里经常有虫子。有一次,我们实在忍受不了,把菜都扣在了地上,向日本人提出抗议,要求改善伙食,结果不仅伙食没得到改善,全体中国工人还受了罚,日本人对我们从来都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与盟军战俘在工厂共同服劳役
关德全对于工厂里的外国劳工印象很深,“他们个子很高,可都瘦得脱了形,衣服破破烂烂的。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出工,中国劳工站成一排,外国劳工站成一排,列队等待分配工作。外国人的车间在二楼,我们的车间在三楼。”那时的关德全只有14岁,对这些外国人充满好奇,每当在工厂走廊遇到这些外国劳工,总会忍不住偷偷打量。后来,关德全从年长的工友口中了解到了真相:这些外国劳工都是日军从东南亚战场俘虏的盟军战俘。1942年11月,日军将1200余名盟军战俘从东南亚押送到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盟军战俘营,目的就是利用他们生产飞机配件、枪械武器、军用皮靴、帐篷等军用产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这批战俘在到达沈阳的第二个月就被强制驱赶到战俘营的直属劳役区“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服劳役(编者注:原“中捷友谊厂”厂区,现在的大东区龙之梦大酒店、龙之梦购物中心周边区域)。
实际上,盟军战俘的劳役场所不仅限于这一个地点,还有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的“满洲帆布株式会社”,由于这座工厂离战俘营路途较远,他们只能在工厂里吃住。“满洲帆布株式会社”主要生产军用帐篷,一共有180名盟军战俘在这座工厂里服劳役。日本人对他们的管理十分严苛,从来不允许他们跟中国人交流。在那里,沉重的劳作、恶劣的环境、无情的监工,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但他们偶尔与中国工友眼神交会时都明白,大家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这跨越国界的无声共鸣,正是他们对和平最真切的渴望。
与盟军战俘结下友谊
在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关德全老人不仅回忆了二战期间被迫在日本工厂做劳工的苦难经历,还向我们分享了一段跨越国界的友谊。
1945年8月,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沈阳街头瞬间化作欢乐的海洋。敲锣打鼓的、燃放鞭炮的,人们脸上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这个从小接受日本奴化教育,被迫称自己为“满洲国”人的少年,终于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我与盟军战俘的友谊是从战争胜利之后开始的”,老人对那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就在这片欢庆的浪潮中,关德全偶遇了工友陈文奇,“陈文奇说,他和工厂里认识的两个美国战俘关系不错,他们的战俘营解放了,问我要不要去看看。”老人轻笑一声,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午后。威廉姆斯、斯道,这两个英文名字他至今仍能清晰念出。尽管交流时需要在中文、英文和日文间来回切换,但语言的隔阂丝毫没有阻碍这群年轻人的相处。
在那段日子里,关德全经历了太多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见到驾驶B-29轰炸机的美国飞行员,他们衣服上缝着写有“我是美国人,希望得到你的帮助”的汉语布条;第一次看到曾经凶神恶煞的日本看守沦为阶下囚,在盟军士兵的监督下劳动。最难忘的,他们一同在战俘营里观看演出、欣赏电影,甚至被邀请到营房里翻阅画报、吃饭、洗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几个年轻人的足迹遍布沈阳城。关德全和陈文奇带着威廉姆斯、斯道穿行于沈阳的大街小巷,不仅游览了沈阳故宫、北陵,还一起去照相馆合影留念,笑声回荡在沈阳的古老街巷,几个年轻人尽情地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短短两周,他们跨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建立了友谊。
送别那日,在沈阳站的月台上,火车汽笛声中饱含着不舍。关德全与陈文奇紧握着友人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这段始于战火熄灭时的跨国友谊,成为他们心里最珍贵的回忆。
让被遗忘的往事得以重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德全进入辽宁省劳改局工作,并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生活回归正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俘营这段历史却渐渐被尘封在岁月深处,少有人问津。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关德全在《沈阳晚报》偶然看到一篇有关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报道。当“盟军战俘劳役工厂”这几个字映入眼帘时,仿佛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他立刻联系记者,补充提供了战俘服劳役的另一个工厂——“满洲帆布株式会社”的信息,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让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往事,得以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自那以后,关德全始终心系与盟军战俘营有关的消息,无论是战俘营旧址的发现与保护,还是战俘老兵回访沈阳,每一个环节都牵动着他的心。在老人心中,有着一个最质朴也最珍贵的心愿——祈愿世界和平,让战争的硝烟永不再起。
后记
采访结束后,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伐,坚持将众人送到门口,而后久久伫立。那身影里,满是对和平的珍视与对历史传承的殷切期盼。
如今,随着亲历那段历史的老人们日渐消逝,这场跨越时空的“记忆保卫战”显得愈发紧迫而庄严。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段真实发生的过往,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珍贵记忆。其中,那些与战争相关的历史记忆,更是以沉重而深刻的方式,警示着后人和平来之不易。
(李卓然,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副主任;靖广生,中共大东区委宣传部三级调研员、国防教育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