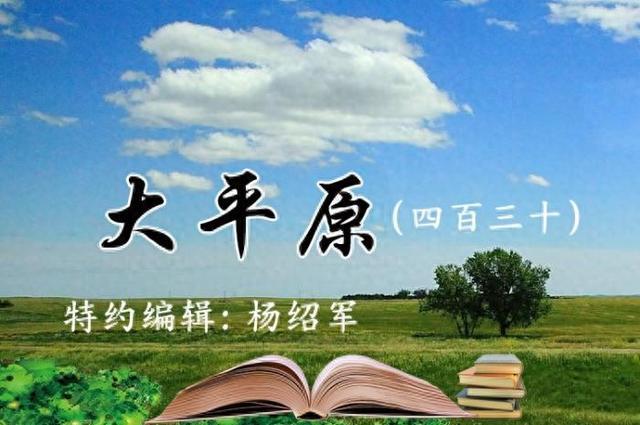
我的姥姥
文/程春燕
今天老师让我们写一件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事,看到题目首先让我想起的是我的姥姥。姥姥去世多年,每每想起她,便有一种温暖从心底涌出,如同冬日里的一碗热汤,不声不响地浸润了全身。
姥姥有一双裹过的小脚。那脚还没长大就被白布条紧紧缠过,骨骼早已变形,走路时只能靠着脚后跟,一步一步地挪。我幼时常常跟在姥姥身后,看她走路的样子,觉得甚是奇特。她走路极慢,仿佛时间在她脚下也变得黏稠起来。有时我跑得快了,回头一看,姥姥还在远处缓缓移动,像一只年迈的蜗牛,背负着岁月的壳。
“姥姥,您走快些。”我常常这样喊她。
“急什么,路又不会跑。”姥姥总是这样回答,脸上挂着温和的笑。
她的脚虽小,却踏过了许多路。从厨房到院子,从我家到舅舅家,从村东头到村西头。那些路,她走了几十年,每一步都留下深深的印记。
姥姥没有牙,吃饭时两颊凹陷,却吃得津津有味。她爱吃肥肉,说是“香”。每每家里炖肉,母亲总会特意挑些肥的给她。姥姥用牙龈慢慢磨着那肥腻的肉块,眼睛眯成一条缝,仿佛在享受人间至味。我那时不解,觉得肥肉恶心,现在想来,或许是缺牙之人口感所需,亦或是贫瘠岁月里对油脂的本能渴望。
姥姥的手极巧。她做的衣服针脚细密整齐,像是用尺子量过一般。邻居们常来求她帮忙做活计,今天帮这家缝被子,明天帮那家裁衣服。姥姥从不推辞,也不收钱,只是默默地做着。她的手粗糙却灵活,穿针引线时稳如磐石。我常常坐在一旁看她缝补,那针线在布料间穿梭,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如同春蚕食叶,令人心安。
姥姥还有一项神奇的本事——给孩子“收魂”。村里谁家孩子受了惊吓,夜啼不止,便会来请姥姥。她会让孩子坐在门槛上,手拿一碗清水,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将水洒在孩子头顶。说来也怪,经她这么一“收魂”,孩子多半就好了。我曾缠着姥姥要学这本事,她说我太小,等我长大了再教。可等我真长大了,她却不在了。那“叽里咕噜”的咒语,终究成了永远的秘密。
姥姥有时去舅舅家住几天。她不在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家里空落落的,像是少了一根主心骨。等她回来时,我就会扑上去抱住她,不知怎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姥姥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哭什么,姥姥这不是回来了吗?”她每一次离开,我总是会很落寞。
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嘴里发苦,什么也吃不下。姥姥用红糖和面,给我蒸了几个小饼子。那饼子甜而不腻,软而不粘,我竟一口气吃了三个。那时物资匮乏,点心是稀罕物,姥姥的糖饼便是世上最好的美味。后来我吃过许多精致的点心,却再没有那般滋味。小时候夜里睡觉,我和哥哥一左一右夹着姥姥,像两只小兽守着老树。我们睡相不好,总是不让姥姥翻身。姥姥便一整夜保持一个姿势,生怕惊醒了我们。第二天起来,她的身子都僵了,却从不抱怨,只是慢慢地活动筋骨,脸上依旧是那温和的笑。
更难忘的是那个傍晚,我背着一筐柴禾从外面回来。推开院门时,厨房的烟囱正冒着白烟,我知道姥姥一定在准备晚饭。“回来啦?”姥姥从灶台边转过身,她那双小脚稳稳地扎在地上,像两棵生了根的老树。我注意到她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笑容,眼睛眯成两道弯弯的缝。
“快去洗手,一会儿有好东西。”姥姥用粗糙的手掌拍了拍我的后背。我好奇地往灶台张望,却只看见平常的锅碗瓢盆。
洗手时,我听见灶膛里传来轻微的“噼啪”声,不像是柴火燃烧的声响。姥姥故意用身子挡着灶口,不让我看。我的好奇心像被猫抓似的痒。
“闭上眼睛。”姥姥命令道。我乖乖照做,听见她拿火钳在灶膛里翻动的声音。忽然,一股奇异的香气钻入鼻孔——是蛋白质遇热后特有的浓郁香味,还带着一丝焦香。
“可以睁眼了。”姥姥手里捧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表面还沾着灶灰。她轻轻一磕,黑壳裂开,露出里面雪白的蛋白和金黄的蛋黄——是一个烤鸡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鸡蛋是难得的营养品,更别说用这样特别的方式烹制。
“趁热吃。”姥姥把鸡蛋掰成两半,大的那半递给我。蛋黄金灿灿的,边缘微微焦黄,冒着热气。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外焦里嫩,香气在口腔里炸开。姥姥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得露出了光秃秃的牙床。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她把自己那一小半也塞进我手里。
现在想来,那个烤鸡蛋的滋味早已模糊,但姥姥偷偷给我开小灶时那种做坏事般的兴奋神情,她省下口粮时那种毫不犹豫的慷慨,以及我们共享秘密时那种心照不宣的亲密,这些感受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鲜明。灶膛里的火光,鸡蛋的香气,还有姥姥温暖的笑容,这些细碎的片段编织成了我对“爱”最原始的理解——它藏在生活的缝隙里,安静地发着光,等着我们在回忆时重新发现。
夏夜的星空格外迷人。姥姥拿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我便挨着她坐下。姥姥摇着蒲扇,那扇子边缘已经泛黄,扇面上还破了个小洞。她摇扇的动作很慢,一下,又一下,仿佛与夜风达成了某种默契。扇子带起的风不大,却刚好能驱散夏夜的闷热。我常常故意凑近些,好让那微风也拂过我的脸。
“姥姥,那颗最亮的是什么星?”我指着天空问道。
“那是织女星。”姥姥眯着眼望向天际,“你看那边,隔着银河,就是牛郎星。七月七,喜鹊搭桥,他们才能见上一面哩。”
我顺着姥姥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几颗星星排成一列,像是真的有一条天河横贯夜空。姥姥知道的真多,她虽不识字,却能说出许多星星的名字和故事。大角星、北斗星、天河、紫微星……这些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韵味。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蟋蟀在墙角“唧唧”地叫着。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夜的静谧。姥姥很少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偶尔叹口气,不知在想些什么。我也不敢多问,生怕打破了这美好的宁静。
露水渐渐重了,衣衫也沾了湿气。姥姥摸摸我的袖子,说:“回屋吧,露水伤身。”我却赖着不走,非要再看会儿星星。姥姥也不勉强,只是把外衣脱下来披在我肩上。那衣服带着姥姥的体温和一股淡淡的樟脑味,让我感到无比安心。如今想来,那些夏夜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满天繁星,更因为有姥姥在身边。她就像夜空中的北极星,恒定而温暖,让我的童年有了方向。
如今,姥姥已离开多年,那些温暖的记忆却愈发清晰。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而是那些细水长流的关怀;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姥姥用她缓慢的步伐、灵巧的双手和无声的爱,在我生命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那些记忆如同老照片,虽已泛黄,却愈发珍贵。姥姥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她给了我最宝贵的财富——一段被爱充盈的童年。
我想,所谓亲情,大概就是这样的存在:当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她给你的温暖却还在延续,如同永不熄灭的炉火,照亮你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