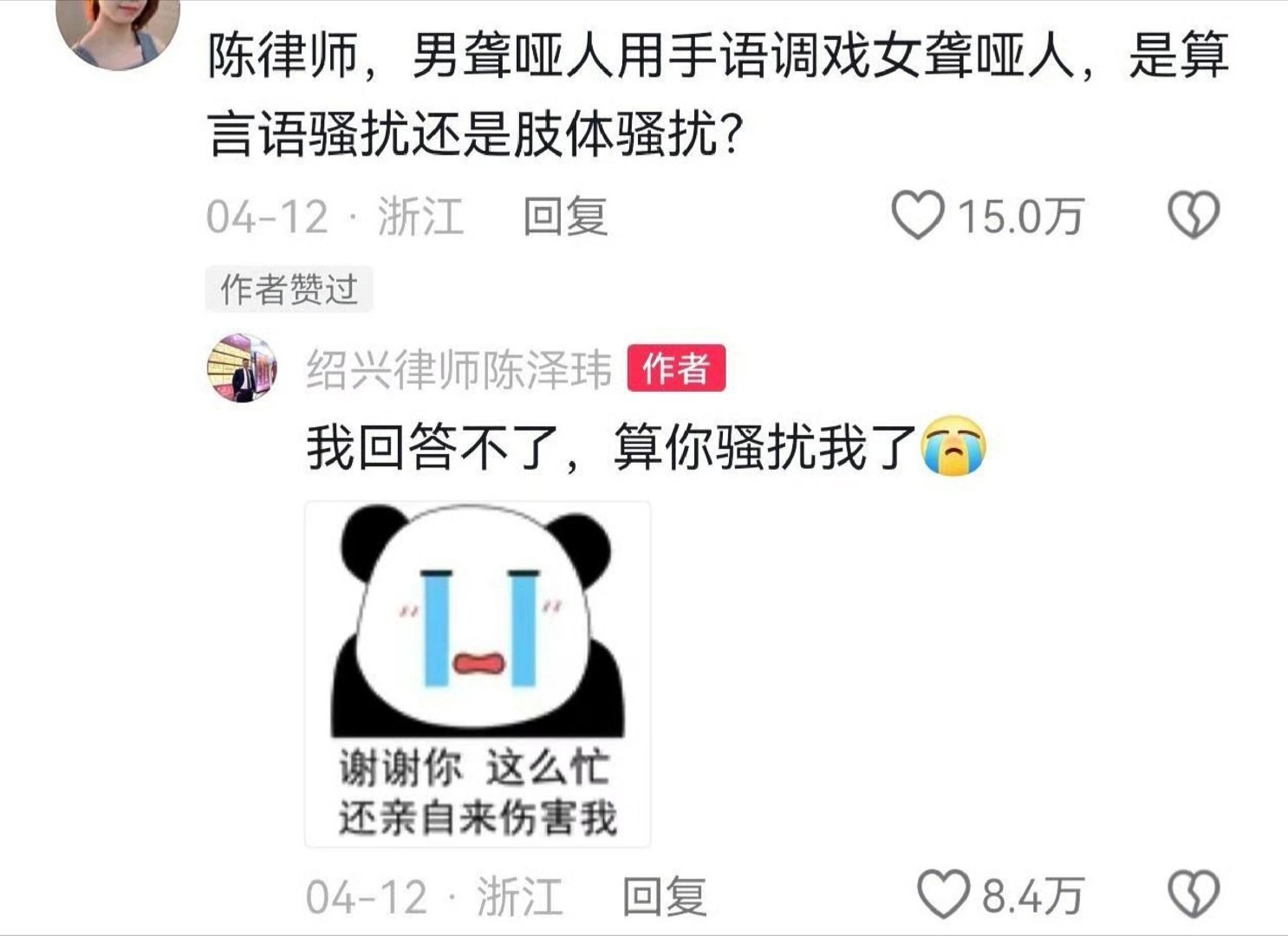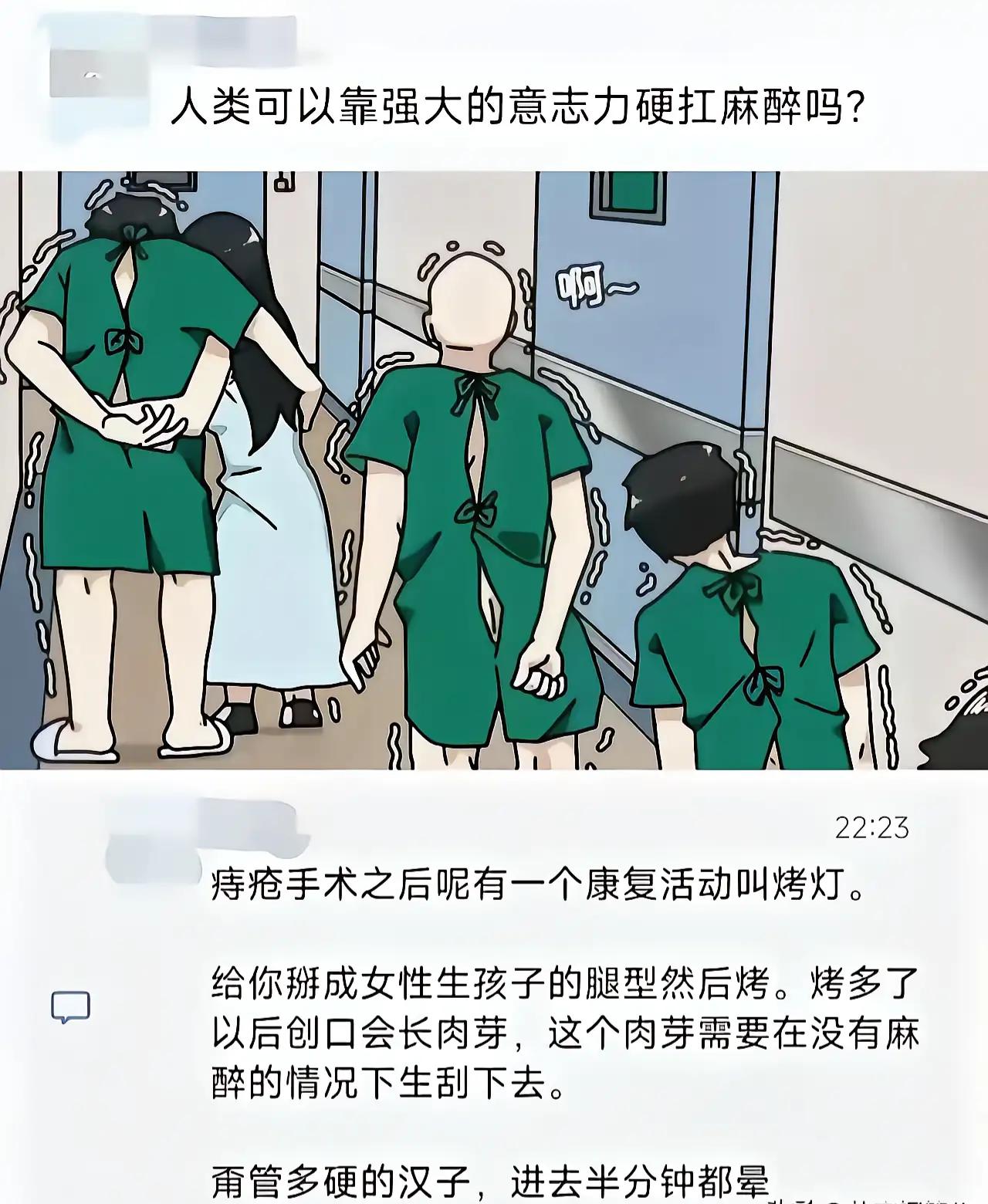1972年,泥瓦匠张复生娶了城里的女知青,晚上睡觉他发现妻子的腰变粗了,他以为妻子得了肿瘤,要带她去医院,谁知妻子是怀孕了,而得知妻子怀孕的他不仅大发雷霆,还要她改嫁他人。 三十五岁的泥瓦匠张复生,有的是力气,缺的是钱。村里没人想得到,他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光棍,竟真把北京来的女知青乔献华娶进了门。 乔献华和别的知青不一样。皮肤白净,说话轻声细语,走路都带着一股子墨水香。她被分到村里小学教书,往黑板前一站,娃娃们眼珠子都不转了。 村里的男人背后没少嘀咕,可谁也没那胆子往前凑——人家可是北京来的凤凰,能瞧得上这黄土地? 张复生到现在还觉得像在做梦。婚礼那天,他穿着借来的新褂子,黝黑的脸膛笑得快裂开。几桌粗菜,几碗老酒,窑洞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乡亲。 热闹是真热闹,可热闹底下,总有人窃窃私语。 “瞧见没?乔老师的腰身……” “这才几天?脸色也不大对。” 话头顺风钻进张复生耳朵里,他脸上的笑就有点挂不住了。 夜里并排躺下,窑洞黑漆漆一片。张复生翻身,手不经意滑过乔献华的腰。 硬邦邦的。他心里咯噔一下。又试着小心摸了摸,那团东西鼓囊囊的,藏在她瘦削的身子下头,异常显眼。他脑子里嗡地一声,只有一个念头:坏了!长瘤子了! 张复生一夜没合眼。天没亮透他就爬起来,一脚深一脚浅直奔公社。 他不敢问乔献华,臊得慌。在队长家门口蹲到队长出来,他慌慌张张把人扯到墙角,手心直冒汗:“我婆姨……腰里硬了老大一个疙瘩……队长,得送城里医院吧?” 队长看着他发白的嘴唇,沉默好一阵,才重重叹了口气:“……复生啊,回去问问她。” 她一口气全倒了出来:1969年,她下乡前,和村里探亲的青年船员李渝生好了。两人年轻气盛,情到浓时没忍住。 后来她发现自己怀了孩子,疯了一样给李渝生写信。信石沉大海。母亲哭着给她出主意:趁肚子没显,找个靠得住的男人嫁了。恰在这时,张复生出现了。他没多问一句,只说“愿意娶”。 张复生听完,像尊石像。他没吼,没闹。转身走出窑洞,在那棵老枣树下的石墩子上,从天擦黑坐到天亮。村里人看见他铁青的脸,绕道走。 日子照旧过。乔献华的肚子像吹气似的鼓起来。张复生仍旧天天下工干活,回家默默劈柴、烧火。他甚至从集上买了红糖回来,搁在炕头,瓮声瓮气地说:“听说……吃了好。” 孩子落地那天,张复生蹲在窑洞外头,耳朵贴着泥墙。接生婆掀帘子出来,喊了一声“是个千金!”。他眼眶猛地一热,扭头就往柴禾垛跑,把炉火烧得旺旺的,整个窑洞暖烘烘。 窑洞里的日子像加了炭的炉子,慢慢有了热气。她开始给他仔细缝补破褂子,窝头里多掺点细面。两口子话不多,但心贴在了一起。女儿第一次奶声奶气对着张复生叫“爹”时,这个泥瓦匠背过身去,使劲吸溜鼻子。 好日子刚焐热,老天爷又翻了脸。张复生砌墙时猛一阵咳嗽,竟咳出了一大口血。县医院诊室里冷冰冰的三个字砸下来:“肺癌,晚期。” 回到窑洞,他变得沉默,常常盯着跑进跑出的女儿发呆。深更半夜,他就坐在院子里的石墩子上抽旱烟,一点红光在浓墨般的夜里明明灭灭,像他飞快燃尽的生命。 乔献华的心揪成一团。她欠他的,还没还上一丁点啊。她咬咬牙,做了个决定:她得给他留下一条根,一个真正流着他张复生血脉的孩子。 又过了些日子,乔献华轻轻拉过张复生粗糙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又有了。” 张复生浑身一震,枯井似的眼睛瞬间红了。他没说一个谢字,转身就出门找活。 他干的比谁都狠,白天黑夜连轴转,挣来的钱一块块攒着,塞给乔献华:“收好……给娃买奶粉。” 二娃呱呱坠地那天,张复生抱着那红扑扑、皱巴巴的小小子,咧开干裂的嘴,笑得像个终于得了糖的孩子。那笑容亮堂得,村里老人都说几十年没在张复生脸上见过。 这笑容没能挂太久。窑洞门口那双他常穿的破旧布鞋还摆在原地,人却没再回来穿上它。张复生无声无息地走了。 第二年开春,李渝生终于风尘仆仆回来了。城里跑船这些年,他揣着攒下来的钱,记挂着当年在村里许下的承诺。一进村却当头挨了一棒:乔献华嫁了,娃都生了俩。他一路打听找到那口熟悉的破窑。 窑洞前头,乔献华正弯腰晾衣裳,两个小小的身影绕着她跑闹。李渝生喉头堵得死死的,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大一点的女娃跑过来,好奇地打量他。小点的男娃迈着小短腿扑过去抱住他小腿,仰起小脸冲他乐。 李渝生后来留在了村里。他帮乔献华挑水、种地,照应两个娃娃。大女儿像极了乔献华,可她叫张复生“爹”,叫得又甜又顺溜。李渝生听着,从没纠正过一个字。 小儿子眉眼有张复生的刚硬轮廓,却偏偏爱黏着李渝生,走哪跟哪。李渝生也由着他拽着衣角,一步一步地走。窑洞里的灯火,照样每天黄昏亮起。 【本文参考权威信源】中国知网《中国知青婚姻史》相关研究;《陕西日报》地方特稿《黄土地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