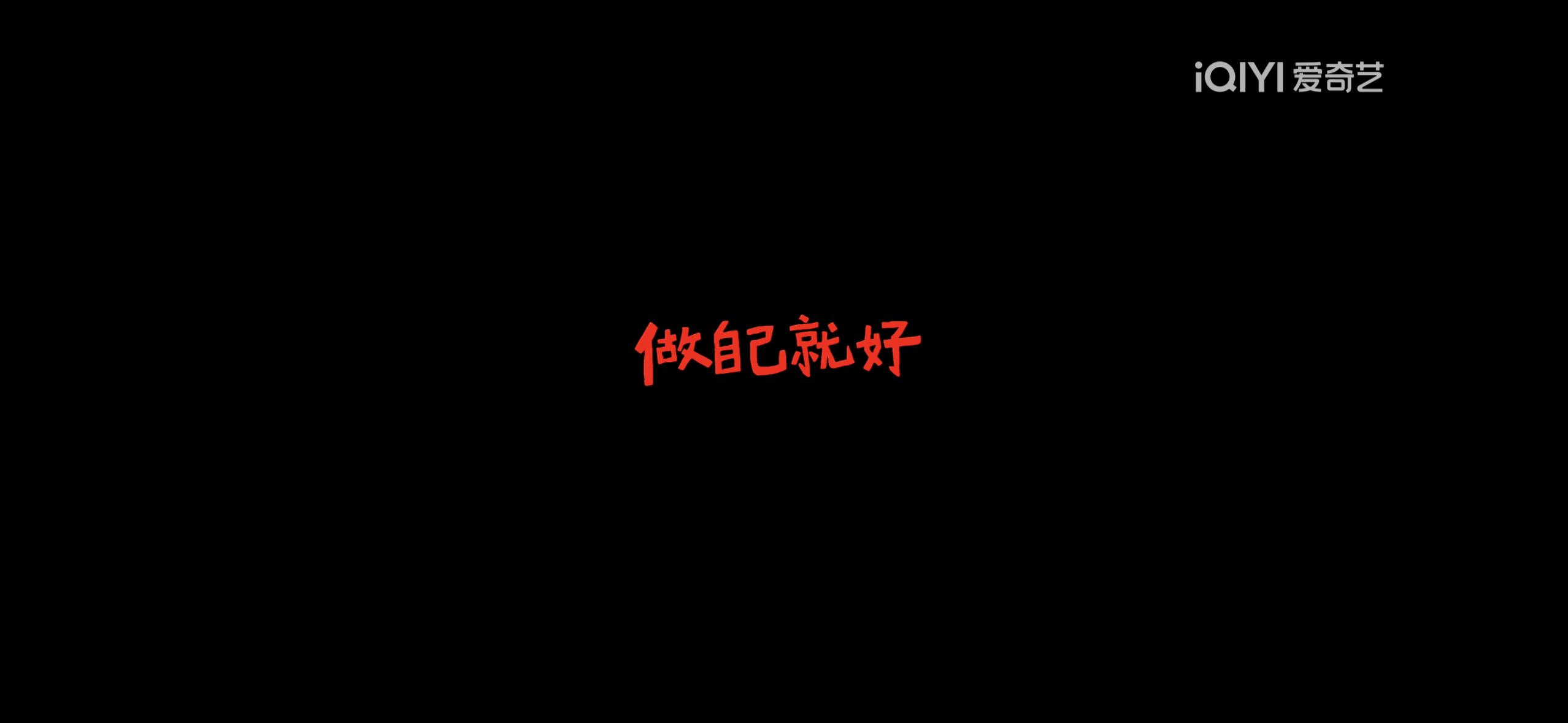刷到了老师发的微博,一时兴起想写点什么,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文字无意间也成为了我的“嘴替”(原文就不贴了,大意是他以为我是一心思细腻的女孩儿,没想到是一爷们儿[二哈])
我并非科班出身,踏入这行纯粹是因为对体育的热爱,又或者说是对体育记者这份职业的向往,具体的启蒙已经有些许模糊,可能是我爷爷广播里的一场球赛,也有可能是我爸妈带我去虹口足球场看的上海申花,去卢湾体育馆看的上海东方大鲨鱼。
时至今日,我的家里依旧留有很多以前的报纸和杂志,《东方体育日报》、《篮球先锋报》、《体坛周报》、《灌篮Hoops》等等。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养成读报的习惯,我只记得当其他同学上课偷偷翻阅小说的时候,我的桌兜里永远都摆着一张报纸,总会时不时拿出来看两眼,直到每个版面的每篇文章都看完为止,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是属于纸媒的“黄金时代”,即使未曾切身经历,但也有幸以读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我一直认为在记者这条路上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初入行不久就成为了报社的篮球条线记者。那年的源深体育馆,因为寂寞大神的到来,几乎场场爆满。被淘汰的那个夜晚,我写完稿之后在发布厅哭了很久,当时一同在一起码字的四位同行,如今只剩下了澎湃新闻的马作宇老师还在体育一线奋斗,他是我入行后就非常欣赏和尊敬的前辈,而剩下的三位有的选择了转行,有的则更换了条线,好在一直都没有断了联系,成为了生活中的挚友。
我记得曾经有相熟的媒体前辈说我是一个“球迷心态”的记者。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感性大于理性的另外一种说辞,利弊各有说法。在报社最初的那段做实习生的日子,偶尔也会帮着做一些校对的工作,如果能够读到首席记者沈坤彧老师采写的文稿,那是最开心不过的事情,文字细腻、内容扎实,她笔下的莫雷诺、曹赟定、王大雷等等,每个球员和教练,甚至到翻译和球队工作人员在油墨中都是有血有肉的存在。
不同于电视台记者,报纸记者是孤独而又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客场跟队期间,最多的时候可能也就三四家上海的媒体,最少的时候就我一个人。从这方面而言,我依旧感慨自己是个幸运儿,在纸媒逐渐没落的年代,报社依旧能够为我的每次出差申请“开绿灯”。
在这个流媒体时代,每个人都逐渐习惯于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或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更直接了当地收获讯息。而我依旧倾向于传统的阅读习惯,喜欢看一些人物报道,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我初始王晨征老师正是源于他写的一篇赵睿探访马尚的报道,又比如深圳晚报的郑志鹏老师,即使从未谋面,但他之前写的一篇有关辽宁球迷家庭的报道,让我印象深刻,类似的还有澎湃新闻胡杰老师写的浙江稠州翻译、殳海老师写的孙铭徽、李轶楠老师写的赵继伟、盛哲老师写的阿不都沙拉木等等,这些故事理应取代所谓的谩骂争吵,成为联赛宣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可惜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似乎并没有太多人愿意静下心来去看这些,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悲哀,但我觉得确实很惋惜。
在上海男篮战胜浙江稠州,将比分扮成2比2之后,我在微博上写了有关王哲林的一个小细节,是他将个人的随身物品留在了球馆的更衣室内,未曾想最后被形容为了“回旋镖”,沦为了笑柄。
有一瞬间,我曾怀疑过自己当时是不是不应该把这些内容诉诸于众,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旧会把这些放到我的稿件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重要,而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文字终究会让读懂它的人得到力量,就像学生时代的自己那样。
一转眼,下个赛季就将是跟队的第十个赛季。记录和发表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当时当下,而是当未来的你或我再次翻阅微博的时候,依旧会因为一张照片,一段故事而内心泛起波澜。暂且不知道自己还能用文笔记录上海男篮多久,但我觉得坚持本身就是一件挺酷的事情,做自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