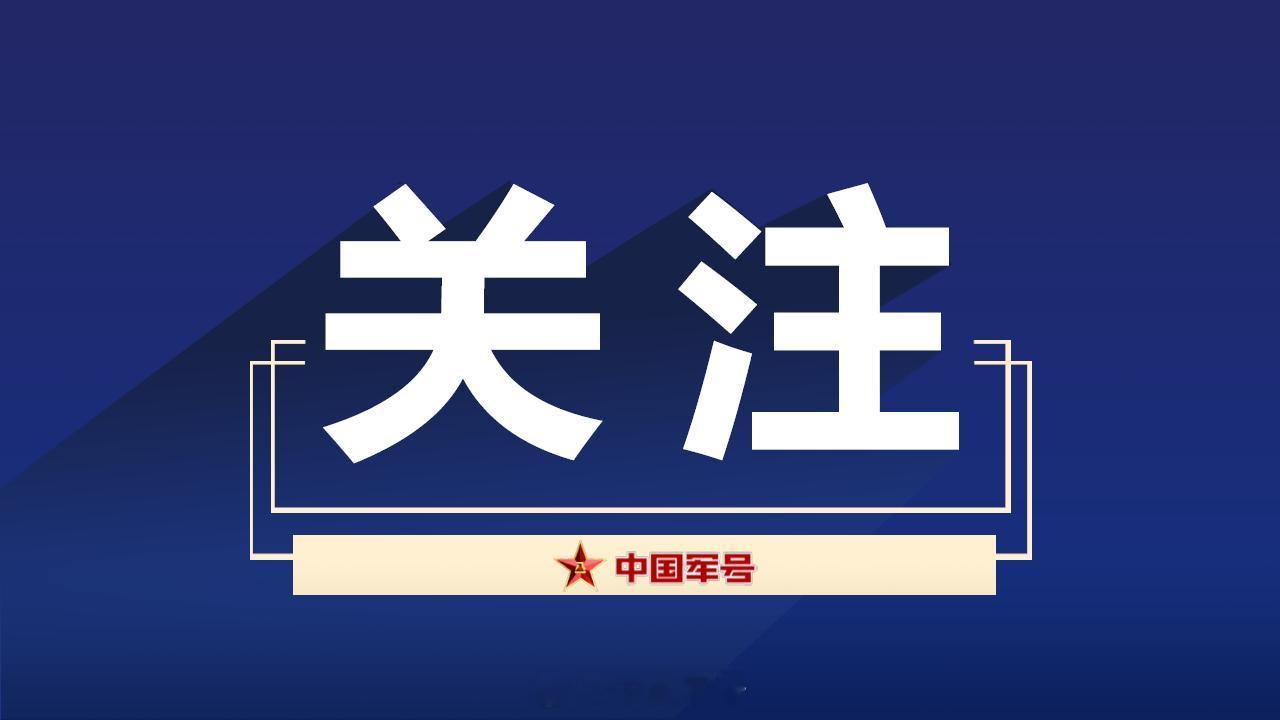【清白夫妻传家风】东北的夜寒冷而漫长,忙碌一天的高自立终于静下心来给远在江西萍乡的女儿写信。
凝视着信笺,高自立迟迟没有动笔。一想到女儿,他禁不住再次落泪。自1927年跟随部队出发,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离家时,女儿刚出生8个月。没想到,一年后,女儿身染恶疾,落下严重残疾。如今,女儿已经20多岁。
这些年来,虽然没有见过女儿,但高自立的心中始终藏着对女儿的爱。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高自立故居,我曾看到过1949年8月和11月,高自立写给女儿的两封信。
“馥英女儿,二十多年没有写信给你,也无法照顾你的生活,原因是环境不好,写信给你,反怕害了你,寄钱又怕被国民党没收。现在我县解放了,故可通信……如有机会,我可能回老家一趟,或者要你母亲回家接你来我处……”
“吾儿现已年过二十,不知已婚否?如未结婚,暂时可不结婚,我拟送你入学,求得一项专门技能,以便能在生活上自立……”
当高自立得知女儿因病致残、生活很是艰难的消息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在信中,一再勉励女儿要自立自强。高自立一直憧憬着新中国成立后,能尽早与女儿团聚。遗憾的是,因积劳成疾,他于1950年1月9日不幸在沈阳病逝,时年50岁。
对于高馥英来说,虽然对父亲没有印象,但父亲的信一直鼓舞着她自强不息、奋发图强。1983年8月,久病不愈的高馥英自感时日不多,她专门叮嘱儿子把两封家书和父亲生前用过的指南针、放大镜、钢笔等遗物,捐献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纪念馆的同志说,按规定要付一定报酬,高馥英不同意。她说,父亲穷尽家中的一切支持、参加革命,儿女们不可能拿父亲的遗物去换钱,否则就对不起为党为国尽忠的父亲。一句话,让工作人员眼眶湿润了。
高自立先后担任过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副部长、代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可以说,很长时间,他都担任着重要职务。然而,他始终过着清贫的日子,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穿了十几年。
由于高自立在长期的战斗中多次负伤,生活也十分艰苦,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虽然组织上有照顾,但他从来不搞特殊,即使有点钱也不舍得花,积攒下来捐给组织。他甚至还把妻子杨竞成做手工酱油赚来的吃饭钱,也都捐了公。
1950年1月,高自立病情加重。他看着泪眼婆娑的妻子,愧疚之意不时涌上心头。他参加革命后,与家人一别就是11年,家里人以为他早已牺牲,都劝杨竞成改嫁,但她坚决不肯。1938年,高自立辗转通过地下党组织给家里写去一封信,杨竞成才知道丈夫还活着。在组织的帮助下,她历经重重艰险才得以与丈夫相聚。弥留之际,高自立握住妻子的双手说:“如果我的病好不了,你就回源头村,照顾好家里的老母亲和残疾女儿,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一边是丈夫的临终嘱托,一边是组织的挽留,还有很多在北京的延安老姐妹也多次邀请,希望她去北京生活。杨竞成谢绝了大家的好意:“我丈夫为党和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临终前嘱咐我回家照顾老小,我得回去,既能照顾家人,也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党和国家做点事情。”于是,杨竞成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萍乡源头村,在那里当了一辈子农民。
位于萍乡源头村的高自立故居,是一幢普通的泥砖土房,四间两进。高自立曾在这里生活20多年,杨竞成从东北回到源头村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回到老家,杨竞成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但凭借在延安和东北的革命经历和见识,她积极给当地建言献策,为地方发展贡献了不少智慧。为此,她先后当选为县政协常委和省政协委员。
源头村距离县城来回60公里,每次开会时,杨竞成坚决不让接送。有时出差,看到别人吃剩的馒头,她悄悄捡起晒干,带回来分给孩子们。政府每个月发给她的补助,也被她捐给村里读书的孩子们。后来,县里提出给她安排住房、安装电话,都被她一一谢绝。
有一次,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来拜年,看到杨竞成家里生活艰难,很不忍心,劝她搬到南昌生活。杨竞成再次婉拒:“孩子们的文化水平低,比较适合在农村,不能给组织添麻烦。”邵式平听后很感动,多次在不同场合说:“作为革命先烈家属,本该享受优待,他们却甘愿扎根农村,还保持着淳朴的作风,永远值得学习。”这个魂永远不能丢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