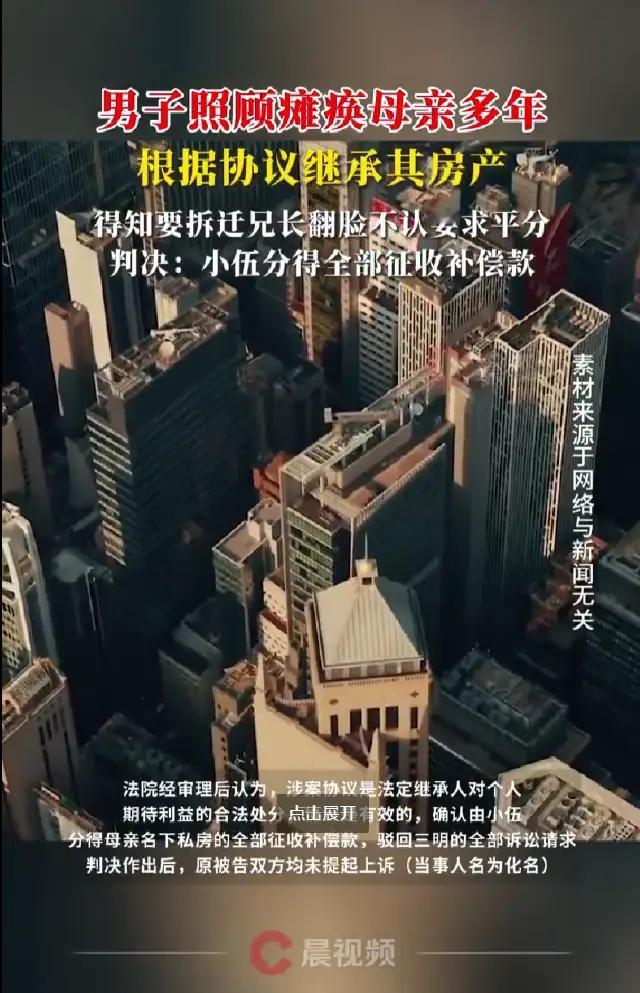上海黄浦,一男子苦心赡养瘫母5年,凭协议继承房产,20年后哥哥为拆迁款反悔,与弟弟对簿公堂。 家住上海的小伍,心里很不是滋味。明明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归自己的房产,如今却要因为一笔拆迁款,和自己的亲哥哥对簿公堂。说起这整件事他就心寒,没想到亲情在利益面前居然如此淡漠。 事情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那时候,小伍的母亲陈阿婆因病瘫痪,常年卧床不起,需要有人寸步不离地照顾。陈阿婆有五个子女,面对需要全天候照料的母亲,这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了让老人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和睦,五个子女坐在一起,遵照母亲的意愿,商量出了一个方案,并郑重地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 协议写得明明白白:由最小的儿子小伍,负责母亲此后全部的生活照料及所有相关费用(包括住院、医药、丧葬等);作为回报,母亲名下的这套私房,将来由小伍一人继承,其他四个兄姊都自愿放弃继承。 协议签好后,小伍二话不说,就将母亲接到身边。整整五年,他信守承诺,端茶倒水,喂饭喂药,处理大小便,无微不至。 那五年,他付出了全部的精力、时间和金钱,直到母亲安详离世,他又独自一人操持了所有丧葬事宜,尽到了为人子的全部孝道。 本以为母亲去世后,这件事就尘埃落定,兄友弟恭,各自安好。不料二十年后的2019年,一纸动迁公告打破了多年的平静。母亲留下的老房子要拆迁了,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征收补偿款。 问题就出在了这笔钱上。面对巨额的补偿款,哥哥三明的心思活络了。他突然跳出来,矢口否认当年那份协议的法律效力,要求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和小伍平分这笔拆迁款。 这让小伍又震惊又心寒。而其他几位兄弟姐妹则表示,当年确实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他们认可并尊重当年的协议,认为这笔钱理应全部归小伍所有。 这件事在街坊邻里间传开,有人就说了,这三明当年甩开手不管,现在看到钱了就回来认亲,这事做得不地道,完全不顾念弟弟的情分和辛苦。 也有人替小伍担心,说这种家庭内部的“君子协定”,没有经过公证,时隔二十年,到了法庭上真的还算数吗? 那么从法律上讲,这份20年前的家庭赡养与继承协议,究竟有没有效力呢? 法院最终支持了小伍,认定协议有效,确认由小伍分得母亲名下私房的全部征收补偿款,驳回三明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在法院判决的背后,蕴含着明确且专业的法律依据。 1、协议的性质是附带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 这份协议并非简单的道德承诺或单方面的继承权放弃声明,而是一份具有合同性质的、附带了对待给付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本案中,陈阿婆的五位子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赡养母亲的义务分配和未来遗产的归属达成了真实一致的意见。 协议内容旨在妥善安排老人晚年生活,弘扬孝道,完全符合公序良俗,因此,该协议自始有效,对所有签字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小伍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理应获得协议约定的全部权利。 2、兄长三明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被誉为“帝王条款”。《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在本案中,兄长三明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是协议的受益方。他因为这份协议的存在,免除了繁重且花费巨大的贴身照护义务。 他在享受了协议带来的利益后,却在需要履行其对价义务(即放弃继承权)时,因征收款的出现而反悔,试图获取其本已承诺放弃的财产。 这种行为是典型的“背信弃义”,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法律绝不支持这种享受权利却不履行义务的投机行为。 3. 判决结果体现了法律对孝亲行为的价值肯定与保障。 虽然本案主要依据合同法原理判决,但其结果也完全符合继承法鼓励孝亲的精神。《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这表明,法律在遗产分配上,本就向多尽了赡养义务的子女倾斜。而本案中的协议,更是将这种“可以多分”的原则,以全体继承人一致同意的形式,明确为了“全给”。 法院对这份协议效力的认定,是对孝子小伍付出的最大肯定,传递了司法温度与公正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