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知青因一首歌判死刑,被公审后,审判员给他的宣判竟然是“有期徒刑10年”,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很快,他就离开了“娃娃桥监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9年,一首歌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命运,这首歌不是革命歌曲,也不是宣传口号,它只是一个知青在思乡情绪中写下的旋律,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引发了一场风暴。 任毅出生在南京,从小喜欢音乐,是艺术团的活跃分子,他在南京市第五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被叫作“11号”,因为反应快、性格活泼,1968年,他高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被分配到江苏江浦永宁公社做知青,他和其他城市青年一样,满腔热血地奔赴农村,梦想着改变中国的乡村面貌。 最初的日子里,他们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任毅在农村干活积极,工分算是知青中挣得最多的之一,可新鲜劲过去后,现实的苦涩迅速显现出来,农村条件艰苦,住的是破屋,吃的是粗粮,干的是重体力活,精神上的孤独和生活上的不适应交织在一起,知青们的热情慢慢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怀念和郁闷,他们开始怀念城市的生活、课堂上的日子、家中的亲人。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里,任毅有了创作的冲动,那天晚上,他和几个知青朋友聚在小屋里,有人提议写首属于知青自己的歌,任毅很快被这个想法打动,他拿起吉他,抱着一腔情绪,熬了一夜,写下了一首叫《我的家乡》的歌曲,歌词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是讲述了一个知青对南京的想念,对往昔生活的回忆,旋律简单,情感真挚,很快就在知青中传开了,大家都喜欢这首歌,甚至给它起了个新名字——《知青之歌》。 这首歌成为知青点里的精神寄托,大家在农忙结束的晚上围坐在一起,弹唱这首表达心声的歌,仿佛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苦日子,任毅因此成了知青中的“文化人”,被大家称赞,也被频频邀请到其他知青点演唱。 谁也没想到,这首温和而朴素的歌会被政治风暴卷入,1969年底,任毅得知这首歌被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改编成了男声合唱,在国际电波中传播开来,从那一刻起,这首歌的命运就不再属于知青们的共鸣,而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国内对任何涉及苏联的内容都高度敏感,一首中国知青写的歌曲被苏联电台播放,立刻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不久,有关任毅的专案组成立,调查他是否与境外势力有勾结,任毅得知消息后极度恐慌,烧掉了歌词手稿、女友的信件、一本他收藏的圣经,并主动前往南京的娃娃桥监狱自首,然而,当时的看守并未收押他,只让他回家等待消息。 这种等待是漫长而压抑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几个月后,在元宵节的晚上,公安部门突袭将他抓捕,被带走时,他没有挣扎,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已经预感到这首歌带来的后果,他被押进监狱,编号3427,接受了长时间的审讯。 1970年春,南京公安机关提交报告,认定任毅为“现行反革命”,并建议判处死刑,几天后,南京市革委会批准了死刑决定,任毅被拉到公审大会上,面对数万人的口号声,他戴着手铐脚镣,站在台上,等待命运的宣判,他以为这就是生命的终点,却没想到事情发生了转折。 案件被逐级上报,最终送到了江苏省革委会审批,当时主持江苏事务的,是许世友将军,他在审阅死刑名单时注意到了这个案子,惊讶于一首歌竟然能让一个毫无前科的年轻人被判死刑,他坚持认为,这样的判决没有道理,他在批文上写下:“此人年轻,历史简单、清白,无死罪,” 正是这句话,让任毅从鬼门关上被拉了回来,1970年7月底,省里决定撤销死刑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十年,8月初,法院重新宣判,任毅站在法庭上,听到“十年有期徒刑”几个字时,一时反应不过来,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却忽然获得了生的机会,仿佛从梦中惊醒。 他被转移到溧阳的石佛寺劳改农场服刑,这一待就是九年,在那里,他每天干重活,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他不再唱歌,也不再写诗,只是默默等待命运的再次转机,1976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他开始尝试为自己申诉,他写下十四页的申诉材料,寄往最高法院,请求复查自己的案件。 1978年,南京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最终认定《我的家乡》并不具备“反革命”的性质,而是属于“情绪化表达”,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构成犯罪,任毅终于等来平反的那一刻,1979年1月4日,他被正式释放,重获自由。 回到南京后,任毅发现,生活已经面目全非,母亲苍老了许多,早年的恋人已经嫁作他人妻,妹妹也在他的服刑期间去世,他的家,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模样,他走在街头,像个异乡人般与这个城市重新磨合。 幸运的是,他的老同学并没有忘记他,很多人给予他帮助和安慰,南京一家绒线厂愿意接纳他,让他进入总务处工作,他开始从头再来,过着平凡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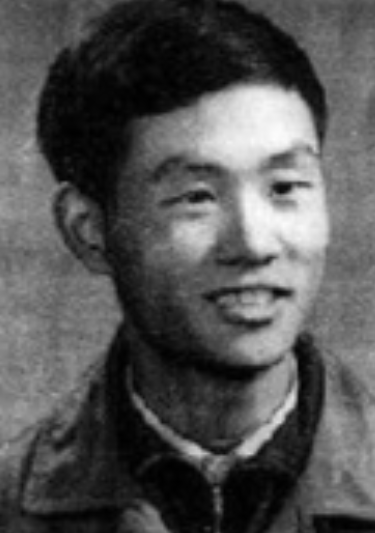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