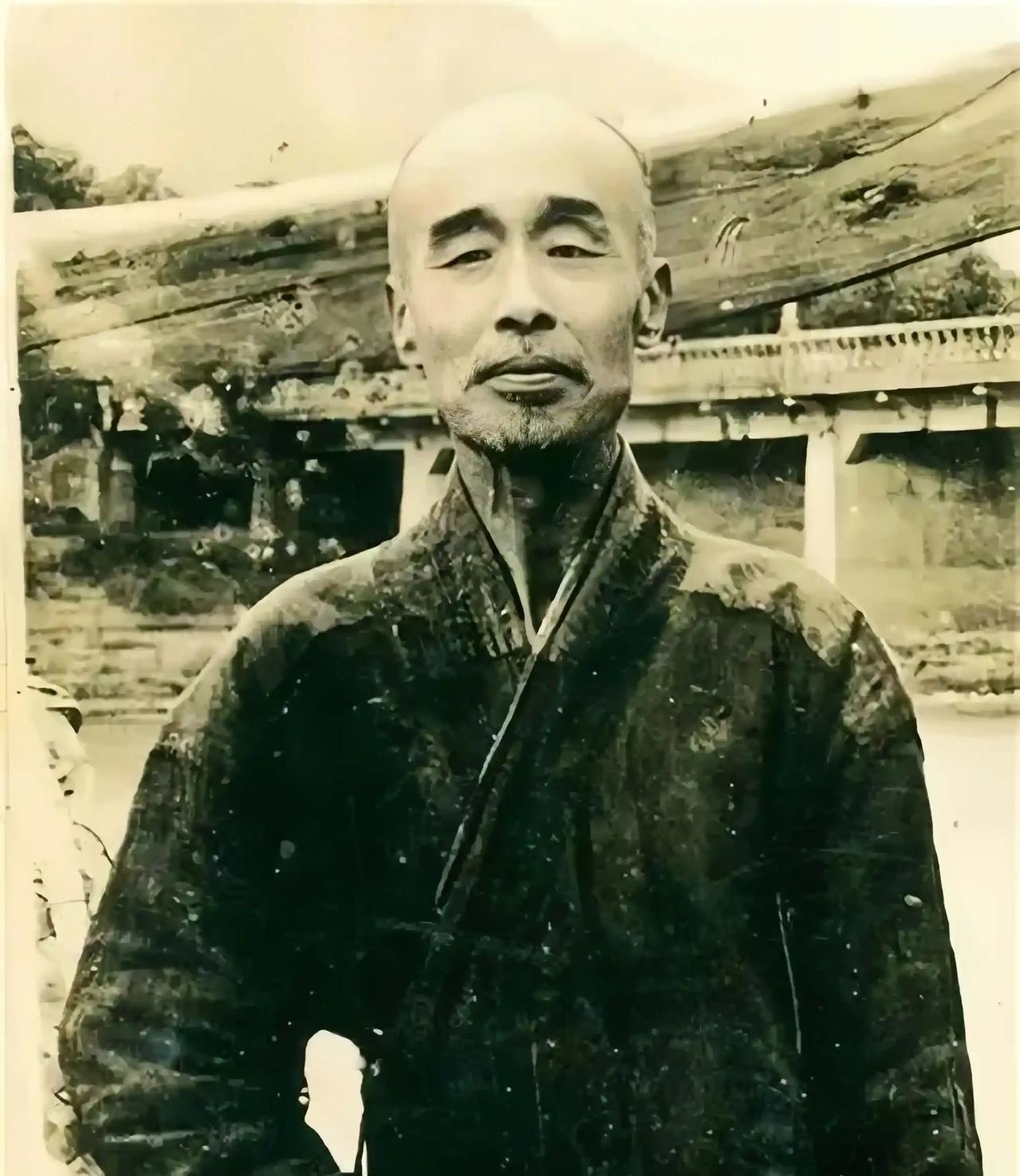俞氏第一次撞见那幅画时,正拎着铜壶进来送茶。画布上的女子侧身坐着,赤着双脚搭在榻榻米上,阳光从木格窗漏进来,照得肌肤泛着薄光。 她手里的铜壶“哐当”砸在地上,滚烫的茶水溅湿了裤脚,却顾不上疼,转身就往外跑,晚饭时扒拉两口就放下筷子,胸口像堵着团棉絮,喘不上气。 她嫁过来三年,李叔同待她温和有礼,教她读诗写字,可这幅画像根刺,扎得她夜里总做噩梦,梦见画里的女子从纸上走下来,对着她笑。 第五天傍晚,俞氏攥着抹布闯进房间,想趁李叔同不在把画摘下来。刚踩上板凳,就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李叔同站在门口,玄色长衫的下摆沾着些尘土,想来是刚从外面回来。“别动它。”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俞氏的手僵在半空,眼泪突然涌出来:“你是读书人,是要做大事的人 挂这个……传出去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她的指甲掐进掌心,“我知道你留过洋,可咱是中国人,总得守点规矩吧?” 李叔同没动怒,走到画前,指尖轻轻拂过画布边缘。那画布边角已经发脆,是他从日本带回来时,用牛皮纸层层裹着的,船在海上颠簸了二十多天,边角磨出了毛边。 “她叫雪子,是东京美术学校的模特。”他的声音低下去,带着些不易察觉的涩,“我在日本学西洋画时,连买颜料的钱都凑不齐,是她每天送和服去当铺,换了钱给我买画布。” 俞氏愣住了。她知道李叔同1905年赴日留学,学的是绘画和音乐,却从没听他提过这些。 “有次我发高烧,躺在漏雨的阁楼里,是她踩着雪跑了三里地,请医生来。” 李叔同的指尖停在画中女子的手腕处,那里画着串细银镯,“这镯子是她母亲留的遗物,她当掉换了药,后来我想赎回来,铺子早关了。” 他顿了顿,转身看向俞氏,“这幅画,是我毕业前画的最后一幅习作。 她坐着让我画了七天,每天从清晨到日暮,中间只喝两盏粗茶。” 俞氏的抹布“啪”地掉在地上。她突然想起去年冬天,李叔同从日本寄回一件和服,靛蓝色的底,绣着细碎的樱花,说是给她的礼物。 她嫌样式古怪,压在箱底没动过,现在才明白,那或许是雪子一针一线绣的。 “她知道我要回国,说‘你是要去做大事的,别记挂我’。” 李叔同的喉结动了动,“走的那天,她来送船,站在码头上,风把和服的下摆吹得像只白鸟。我没敢回头。” 他指着画中女子的眼睛,“你看她的眼神,不是放荡,是清亮。她知道我画这个,是为了学本事,将来教中国人画自己的画。” 俞氏慢慢走到画前,第一次敢仔细看。女子的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意,眼里却藏着点湿意,像有话没说出口。 她突然想起李叔同回国后,总在深夜对着空书桌发呆,手里捏着支日本产的狼毫笔,笔杆都被摩挲得发亮。那些她看不懂的沉默,原来都藏在这幅画里。 是怨自己从未懂过他——懂他揣着救国志远渡重洋的孤,懂他对着画中人时,那份藏在文人风骨下的柔软。 后来那幅画依旧挂在墙上,俞氏每天擦桌子时,都会特意绕开画布,生怕碰坏了。 有次儿子李准指着画问“这是谁”,她摸着孩子的头说:“是位好人,帮过你爹爹。” 一幅画,隔着东洋的海风与故土的礼教,藏着一个男人的理想与愧疚 也藏着一个女人从误解到体谅的过程。那些看似难以容忍的“出格”,背后往往是未曾言说的深情与担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