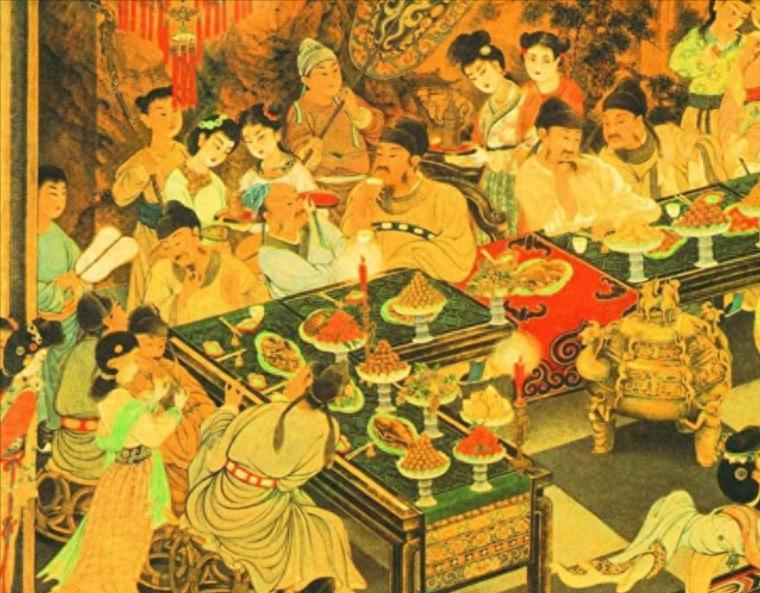五子登科有何典故?“五子”指的是哪五子?古人留下的祝福别用错 提到“五子登科”,人人盼着,满是喜气。但您听说了吗?这句吉祥话的主角窦燕山(真名窦禹钧),他的前半生,跟“喜庆”俩字完全不沾边! 他家境殷实却胡作非为,名声极差,直到四十多岁膝下无子,被说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 窦禹钧活在唐末五代那乱糟糟的年头,老家大概是今天津蓟州那块儿。《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估摸着也就知道他姓窦、住燕山,名字是啥,没太当回事儿。 早年的窦禹钧,那可真是个反面教材。家里有矿,钱多得能砸死人,可他呢?典型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就是不干正事。 家业传到他手上,经营上是一塌糊涂,为了捞钱,歪门邪道可没少走。看见别家生意好,他就暗地里使坏。顾客上门,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是家常便饭。这么一来,十里八乡谁不戳他脊梁骨?名声臭到了家。 怪就怪在,窦禹钧家财万贯,老婆小妾娶了四房,可都三十好几了,愣是一个娃都没有。街坊邻居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都说他缺德事干多了,这是老天爷不让他有后。 窦禹钧自个儿也慌了,到处求神拜佛,名医偏方试了个遍,可几个老婆的肚子就是没动静。 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窦禹钧做了个梦。梦里,他过世的老爹黑着脸来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说他前半辈子坏事做绝,惹怒了天帝,要罚他窦家断子绝孙。唯一的活路,就是从现在开始,立地回头,积德行善,兴许还有一线生机。 梦醒时分,枕头都湿了,也不知是汗还是泪。窦禹钧吓得一激灵,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棒,也像是灌了一碗苦药,一下子清醒了。他再也不敢耽搁,爬起来就琢磨着怎么改过自新,怎么把这天定的倒霉运给扭过来。 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自家门口搭了个棚子,熬粥施舍给过路的穷苦人。 起初啊,他那“恶名”在外,白给的粥都没人敢喝,生怕里头有诈。直到一个饿得眼冒金星的叫花子,实在扛不住了,哆哆嗦嗦地从他手里接过一碗粥喝下去,没事儿! 大家伙儿这才慢慢信了:这“窦恶霸”,好像真变了个人。想想以前他对乞丐那副爱搭不理的样儿,现在能亲手给人家盛粥,这弯儿转得可真够大的。 从那以后,窦禹钧的善事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件接一件。这一晃,就是二十四年。窦禹钧的善行一天都没断过。他早就不再是那个让人瞧不起的败家子,而是远近闻名的“窦大善人”了。 果不其然,窦禹钧五十五岁那年,奇迹发生了!他的五个老婆,竟然接二连三地给他生了五个儿子:窦仪、窦俨、窦侃、窦偁和窦僖。这五个小子,就是后来“五子登科”的正主儿。 窦燕山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那双眼睛,贼亮!爹妈啥样,他们就学啥样。所以啊,教这五个儿子,他从不来虚的,自己先做好榜样。 他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节俭,再也不碰那些花天酒地的事儿了,跟他年轻时比,简直是两个人。他要求儿子们对自己要严,对别人要宽。 家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谁敢铺张浪费,门都没有!哪个小子行为稍有不端,他立马指出来,逼着改,绝不惯着。 就这么着,窦燕山这种近乎严苛的家风,加上他自己雷打不动的善举和对学问的看重,像春雨点点滴滴,全渗进了五个孩子的心里。 五个儿子也没辜负他,一个个都成了人中龙凤,先后都考中了进士,当了官。大儿子窦仪,官做得最大,当到了礼部尚书,那可是相当风光。 这五个儿子不光会读书,更难得的是,都学了他们爹后半辈子的实在、勤快、心善。窦家一下子就成了当时的豪门望族,窦燕山自己呢,也安安稳稳活到八十二岁才走。 “五子登科”的故事,跟中国古代那个影响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分不开。隋朝开始有的这玩意儿,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鲤鱼跳龙门的唯一机会。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改变命运,在当时可不是一句空话。 唐宋时候科举最火,给国家挑了不少好苗子。可到了明清,这制度就越来越死板,选人也不再只看本事,出身背景啥的越来越重要,慢慢就没啥活力了。 回头再看“五子登科”,要是只把它当成盼着多子多福、升官发财,那就太小瞧这故事了。窦燕山这一辈子,简直就是一出逆天改命的大戏。前半辈子,坏事做尽。后半辈子,善行如山。 五个儿子能出人头地,科举制度当然是块敲门砖,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窦燕山用自己后半辈子的行动给孩子们上的那堂最生动的课,还有那场让他脱胎换骨的忏悔。 这故事好像在跟我们说,就算掉进过泥坑里,只要真心想爬出来,用好事实实在在地去弥补,老天爷也不会总板着脸。它强调的,可能不是结果多辉煌,而是过程中那份反省和修炼。 当爹妈的,与其天天琢磨怎么把孩子培养成天才,不如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像后来的窦燕山那样,对自己严点,对别人宽点,多做点好事? 毕竟,身教比嘴上说一万句都管用,爹妈的品行,就是孩子跟前最亮的一面镜子。 如今,再听到“五子登科”这句祝福,我们不妨少想点功名利禄,多琢磨琢磨里头劝人向善、父母如何用德行影响孩子的味道。这或许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更值钱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