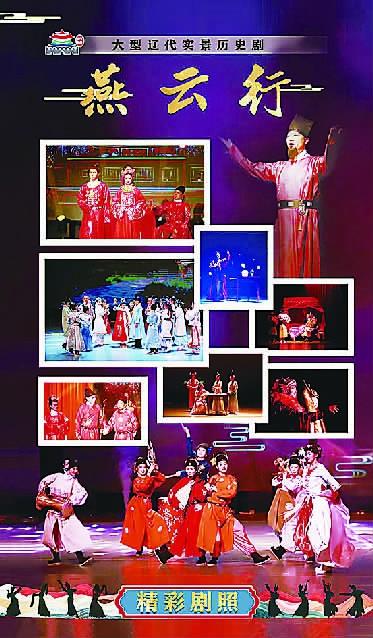艺途随笔 巩伟民 一个学手艺谋生的匠徒,常有“班门之外”的愧憾,生性好奇,心神难得稳定,东西看的越多愈觉得真正认识的艰难,信道“艺海无涯”的道理,承认自己永远是一个学生,或许就这样我能找到一个诚实的自己。 从前封闭状态,跨入开放大潮,惊讶、欣喜、困窘、惶惑兼而有之,不甘自闭于狭隘的艺术观念,不甘囿于旧习的表现模式,渴求在创新中获得自新,是同行的共同愿望,回顾几十年来自己走过的路,如同重温变幻莫测的许多梦境,明白自己什么都不行的人,急切地想把什么都了解一下。这些年我临摹过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荷尔拜因、门采尔,素描速写,同时也临摹过顾恺之、陈老莲、任伯年的线描,临摹过伦勃朗、维米尔、杜拉尔古典油画技法,凡·高、塞尚、毕加索、马蒂斯、德库宁的油画,同时也临摹过石涛、八大山人、黄宾虹、齐白石、李可染、徐悲鸿等大师的水墨画。外出观看各种画展、书法展、根雕展、中国古代壁画……东一手西一手地去摸索,深一脚浅一脚地去试探,有类于随见随爱,观后激动,不免喜新厌旧之谦,老子曰:“少则好,多则惑。”细思量,我杂乱学习,面面俱到,反而没到,兴趣和性格的原因,颇多情不自禁地任性,静定自省,我付出较多,几十年生命和精力试验,我得到最厚重的收获,使我心悦诚服地明白了,我正处在一个很浅薄的层面。我从学习过程中真正体会到,大师们对自然的虔诚,对艺术充满相互敬意和传承,明白了现如今画坛上一切标新立异的创造基点,正是源于人类二十世纪整个文明的背景。 于是悟到:一个浅薄的我,倒不必疑惑,因为杂学多师,而掩盖了自己原有的积习,以为最可怕的是故步自封,对浅薄的“自我”自满自足。 我相信大师们在艺术中,自我的高度是博览厚积的修行境界,功到气象自然形成,并非浅尝一技,活到老学到老,庆幸已在艺术道路上一直坚持追求、努力、创新,才有了这样一直当学生的可能性。 “行路难,多歧路”步履蹒跚地走下去,甘苦自知,虽然创作习作不少,可自慰作品不多,但扪心自问,我用心认真地去作的,选题材无论古代、现代、世情民俗、风景、静物、人物,寄托喜怒爱憎,各个画种的题材及形式,我都尝试过,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及作品,也许,我是一名教师,涉猎教材之多,门类齐全,理论、技巧作画之方法步骤都得懂,会操作,真情实感完成课堂教学及课件作品。 我自幼生长在农村,生活在乡下,务农不多,一直在求学路上,尝试过乡村生活的酸甜苦辣,人在困窘中生命本能的劲力,人与自然联系的密切,人与人在粗衣淡饭间诚实、坦然、醇厚的心灵感应,那些踏踏实实劳作在土地上的农民生活,在我心中已经形成一种永不消失的呼唤,我如不能自然地去揭示感受他们的真实性,也应自觉自愿地用画笔表现我对真实的感受。 作画时我每每奢望,而对不同题材内容的挑战,努力找到不同的表现方法和造型语言,常觉一幅作品的形成,犹如一个生命的诞生,每件作品有自己的生命和语言。艺术形式是作品精神内涵的自然选择。看大师之作,仿佛能看到他们作画时,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运笔中处处是笔底气韵。 我虽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艺术道路上坚持、追求、努力、创新,出了不少拙作,每件作品都认真完成,付出大量心血及汗水,今后继续刻苦,努力创作出理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