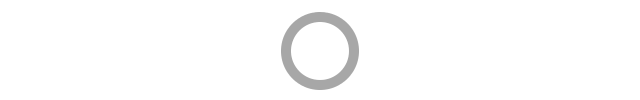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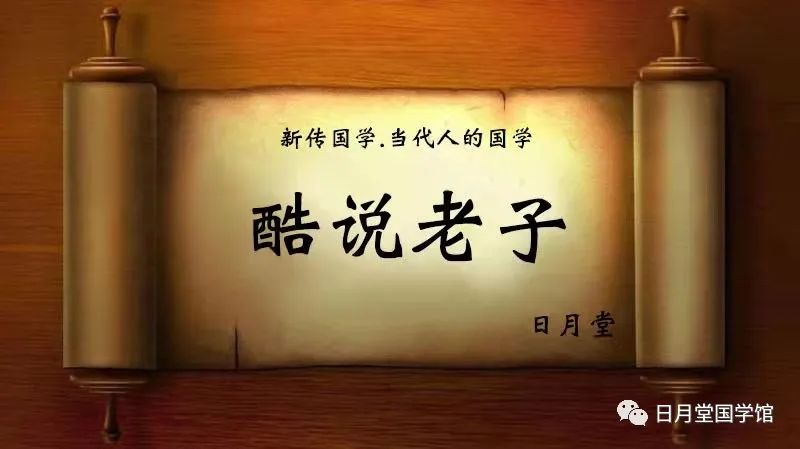
第一章 (第十三节)
孔子一句话竟然害惨了大诗人李白?
01
首先,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老子为什么会说“名可名非常名”?

上一节我们已经讲过“道可道非常道”,通过三个层面论述了“我们只能接近真理,而无法抵达真理”。因为这三个层面都不可靠:
第一个层面是:客观世界不可靠
第二个层面是:人本身不可靠。
第三个层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不可靠。
其实还有第四个层面:
就是即使客观世界可靠,主观的人可靠,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也可靠,我们可以百分之百抵达真理的彼岸,或者是你通过自己的修行能够体悟和觉知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么问题来了,你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
目前我们人类只有三种表达方法:
第一种是用言语,通俗的讲就是说话。
第二种是用语言,通俗的讲就是文字。
第三种是用沉默,通俗的讲就是暗示,也可以称之为眼神交流。

比如西周时期的暴君周厉王刚愎自用,听不得批评,于是就找了许多巫师充当特务,在大街小巷里偷听老百姓的谈话,只要谁敢妄议朝政,就立马抓起来处决。最后导致人们在路上遇见的时候都不敢开口打招呼,只好“道路以目”,用眼神互相交流①。
02
显而易见:
“道可道,非常道”,属于言语表达;
“名可名,非常名”,属于文字表达。
遗憾的是,无数的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不可靠。所以,最好的表达其实是“沉默”,但是老子他能用“沉默”表达吗?不能!因为在当时没有人能听的懂他“沉默的呼喊”。

孔子拜访他的时候才34岁,所以只能听懂他说出来的话,听不懂他说不出来的那些话。否则老子断然不会抛下芸芸众生,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隐居。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好老师都像释迦牟尼那么幸运,开坛讲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说,只需拈一朵花,就能换来迦叶尊者一个会心的微笑。从此,佛教就有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宗②。
03
后来孔子在晚年的时候终于觉悟了,于是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也当着众弟子的面说了一句话:
“予欲无言。”
意思就是:
“我不想再说话了。”
结果,满堂的学生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会心微笑的人。相反,子贡一听都急哭了,就问:
“老师您不说话,那我们上课怎么记录,怎么交流啊?”
孔子失望地仰天长叹: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③
对呀!天什么时候说过话?但四季照样交替,万物依旧生息,一切不都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吗?其实孔子这番话背后所要表达的是,老天爷不言不语,我依然能领悟“天之道” ,领会“天”的旨意,你们为什么就听不懂我的“沉默”呢?

04
孔子恐怕没有想到,一千年之后,自己的这句话竟然间接的害惨了大唐诗人李白。
话说李白三十岁的时候,夜夜笙歌,日日饮酒,喝醉之后经常吆五喝六,不知天高地厚。结果有一次半夜醉驾,骑着马耀武扬鞭,惊扰了当地长史(省参谋长)的车队。所以李白的酒品在十里八乡那一直是有口皆碑。

后来新长史裴宽上任,李白决定替自己辩白,你肯定想不到,他上书的第一句话就是: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也,安得不言而知乎?”④
裴长史不可能不知道孔子的这个典故,所以这个开篇就等于说:
我李白,不是天,也不是地,是人,所以我不能沉默,我不说你们一群笨蛋怎么知道我李白是什么样的人呢?
但凡是一个正常人,心里恐怕都会有一股扳掉李白门牙的冲动。不过,这个裴长史很有雅量,只是不予重用,并没有对李白怎么样。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借孔子的口吹自己的牛?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人能跟他进行“沉默的交流”。
没办法,“沉默”是最高级的语言,一般人一辈子都无法领会。
05
也正因如此,老子才迫不得已选择了前两种不那么好的表达方式:
“言语和文字。”
而且还特意地提醒我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就是他写《道德经》的初衷。
好,关于老子为什么要写“名可名非常名”问题解决了。接来下的问题就是:“名可名,这两个“名”究竟各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下一节论述。

1、《国语•周语上》
2、《五灯会元•卷一•七佛》
3、《论语·阳货》
4、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第一章 (第十四节)
西方走了两千年,才抵达东方哲学的起点?
01
好,上一节关于老子为什么要写“名可名非常名”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
“名可名”,这两个“名”究竟各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并不难理解:
第一个“名”,是名词,指“名称”。
第二个“名”,是动词,意思是“命名”。
但是,古人创造“名”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起源。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意思就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人在马路上狭路相逢,没有路灯,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其中一个人只好问: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另一个只好回答:
“我乃黑旋风李逵是也!”
这就是“名”的起源,等于是自报家门。既然是"自命",说明“名”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名和事物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只是在特定空间,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的对应关系。但是除了人以外,动物、植物以及石头不会说话怎么办?
没办法,我们只好来替它们说。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当我们替一个事物命名的时候,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吗?
02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生物:
两腿,有毛,能下蛋,会打鸣,我们将其命名为“鸡”。
但是我们将它称做“鸡”以后,鸡的本来面目就模糊化了,甚至是窄化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谈论“鸡”,脑海里想到的只是“两腿有毛能下蛋会打鸣”等等这一些鸡的表面化的特征。其实这些特征,只是我们通过自己的主观意愿为“鸡”贴上的“标签”而已。
事实上,鸡作为一种动物界的脊索动物鸟纲类,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百倍千倍。而且无论我们对鸡的基因、品种、生殖、发育、习性等等研究的多么深入,多么完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自始至终都无法全面的、准确的、百分之百的了解关于鸡的一切。
更为关键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完美的了解鸡的一切,也无法完美的把这一切表达出来。

03
那我们该怎么办?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做加法,提高语言描述的精确性。
甚至必要时创造新的词语,以便能更详尽、更周密地去了解和描述这个世界。
第二种是做减法,提高人类认识的全面性:
不用去创造任何新的词语,而是在现有的语言基础上,经过教育和培养,铲除我们心中的偏见,让我们不仅能看到浮在表面上“语言”,还能透视到“语言”背后所包裹着的“内涵”。
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加法——就是让语言数学化。
减法——就是让语言诗化。
那么请问,哪一种办法更好?
04
其实对于东方文化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答案很明显:
第二种,做减法更好。
所以中国一直推崇的最好表达方式是文言文,讲究言简意赅,比如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典故:
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有一天跟几个同僚出去游玩,在路上看到一匹受了惊的马踩死了一条狗,几个人就互相揶揄,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描述。
第一个人说了十二个字:
“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
第二个人想了半天,去了一个字,说了十一个字:
“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了哈哈大笑说:
“要是让你们写史书,恐怕一万卷也写不完。”
这些同僚就问那应该怎么描述?欧阳修只说了六个字:
“逸马杀犬于道。①”
没错,欧阳修只用了六个字就描写出了一个电影的动态超长镜头。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写历史的方法,但是我们能从古代文人的思想里读出一个文化传统就是:
斟字酌句,惜墨如金。
而且这个传统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从《周易》到《道德经》一脉相承。因为中国的哲学家很早就看到了“名”的局限性,所以在文字上讲求“因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
也正因如此,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代表人物像公孙龙和惠施虽然巧言善辩,伶牙俐齿,但是他们那一套哲学理论在中国完全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壤,所以很早便失传了。

05
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更偏向于第一种:
就是做加法。
尤其是在十七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欧洲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哲学家。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那些越著名的越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往往都出自同一个国家。
比如,我随便列举一个名单:
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恩格斯、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等。
没错,这些哲学家统统都是德国人,而且他们只是一部分,并非全部。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德国(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云南省),所产出哲学家在世界近代哲学史上能占据半壁江山?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有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
德语,是目前全世界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最细致、最精确、最严密的语言。
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比如康德写过一本名著叫《纯粹理性批判》,刚出版的时候有一个读者写信抱怨说:“尊敬的康德先生,你知道你的书有多难读吗?我每一个手指都会按住你的一个从句,结果十个手指头都用完了,你的一句话还没读完!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句话三分钟还没有看到句号是什么样的感觉?三分钟读不完一句话,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语言可以做得到?汉语做得到吗?英语做得到吗?法语做得到吗?
都做不到!但是德语就能。
06
然而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既然德语这么这么细、这么精确、这么严密,那么它解决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了呢?
答案是,没有!
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随着语言的越来越精确,导致问题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多,所以哲学上的流派也越来越多。直到二十世纪前后,西方的哲学才开始掉头,开始改变研究方向,开始研究语言本身的问题。
07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哲学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本体论阶段。
在本体论阶段,哲学家们走出神话,开始怀疑人生,追寻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阶段。
在认识论阶段,哲学家们又开始怀疑世界。因为他们认识到,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去追寻世界的本源,而是要追求如何才能认识这个本源。于是创造语言,发展逻辑,积累经验,制作各种科学机械和技术工具。
第三个阶段,是语言哲学阶段。

这个时候,哲学家们才开始怀疑语言!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语言表达的不够准确,那么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意义。于是研究语言,如何分析,如何表达,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西方人走过这三个阶段,从古希腊开始,走了两千五百多年。但是在东方,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印度的释迦牟尼就已经在菩提树下走完了,中国的老子也已经在周王朝的图书馆里走完了。所以中国不只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早熟,中国的哲学同样是早熟的儿童。
因此,哲学三阶段的划分只适合欧洲,并不适用于中国。
08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哲学好不容易发展到了语言哲学阶段的时期,没想到几十年之后又开始分裂了,大致分为两大流派:
一派主张做加法,通过逻辑来构建一套人工语言。
最早萌发于柏拉图,然后在莱布尼茨的著作里破土,到近代罗素的手里终于发展成熟,这一派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
另一派提倡做减法,通过研究来恢复日常语言的本义。
当然,在西方两千年来都没有土壤,由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奠定基础,被称为日常语言哲学②。
那么,究竟哪一种方法更好呢?我们下一节继续解读。

1、冯梦龙《古今谭概•书马犬事》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16节》
第一章 (第十五节)
东方哲学一出生就在喜马拉雅之巅?
01
上一节我们讲到,在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哲学好不容易发展到了语言哲学分为两大流派:
一派主张做加法,通过逻辑来构建一套人工语言。最早萌发于柏拉图,然后在莱布尼茨的著作里破土,到近代罗素的手里终于发展成熟,这一派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
另一派提倡做减法,通过研究来恢复日常语言的本义。当然,在西方两千年来都没有土壤,由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奠定基础,被称为日常语言哲学。
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
当我们无法完美地认识和表达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给“语言”做加法还是减法?
虽然这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道理,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我个人以为:
从哲学的终极意义上而言,减法的境界恐怕更高一筹。
因为减法更难,甚至减到最后,你不得不用“沉默”去表达。其实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前言里就说过一句充满了东方智慧的名言:

“凡是能够谈论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能够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
什么是“不可说的”?
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形而上的本体等等……一切可以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因为这些都超出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
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
“面对真正哲学上的东西,我们应该选择沉默。”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他所说的“沉默”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不闻不问不言不语”,而是一种更高级的表达方式。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除了“说话”和“文字”之外的第三种表达方式。维特根斯坦真正的想法是:
通过沉默的方式把那些不能说的东西“显示”出来。
02
不过很可惜,当时西方的哲学界普遍都无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包括他曾经的导师罗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本战俘营里写的《逻辑哲学论》后来正是他剑桥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1929年毕业答辩的时候,指导老师就是罗素和摩尔(英国分析哲学创始人)。三个人随便聊了聊,罗素和摩尔都很尬尴,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表示看不太懂维特根斯坦的论文。当时四十岁的维特根斯坦就笑着走到他们俩面前,拍了拍他俩的肩膀说:
“不要担心,你们永远都弄不懂这些问题的。”

当然,最后毕业答辩就以这样幽默的方式通过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罗素确实没有读懂维特根斯坦的核心思想。《逻辑哲学论》这本书就是罗素找人帮忙出版的,还亲自写了序言。他在序言里就表示很疑惑:
你维特根斯坦既然说凡是真正哲学上的东西都无法说出来,但你同时又说能够显示出来,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罗素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看了这本书有一种“理智上的不快”。说句题外话,维特根斯坦曾在一封信中声称,自己的《逻辑哲学论》其实是两本书,一本书写出来的“有字书”,另一本是没有写出来但暗示出来的“无字天书”①。而无字天书才是最重要的不可言说之物,结果当代许多的哲学家们天天都在教室里空谈。
显而易见,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空谈哲学家的名单里肯定有罗素,不知道如果罗素看到这封信会怎么想,恐怕不只是“理智上的不快”,可能是“精神上崩溃”。幸亏,维特根斯坦这封信一直都没有公开。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罗素虽然很推崇佛教,但是他对佛学的文化内涵并没有深层次的了解。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维特根斯坦的“矛盾”根本就不是问题。
比如“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用眼神交流,这不就是中国禅宗自古以来的日常生活吗②?再比如“相遇而不言,目击而道存”——通过暗示沟通,这更是自庄子以来中国就有的思想传统③。

所以,即使像罗素这样西方公认的天才哲学家都难以理解“沉默”这种最高级的表达方式。可以想象,我们中国的哲学是多么的超前,我们东方的哲学可以说一出生就在喜马拉雅的山顶上。
03
还有,如果我们从哲学最高层次上讲:
就算是被西方哲学界誉为“天才中的天才,哲学家的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也并没有登上珠穆朗玛最高峰,他的理论依然在半山坡上,尚未成熟。
他晚年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逻辑哲学论》给否定了,他终于认识到,语言和世界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情景以及不同的人之间,完全代表着不同的意义,用精密的逻辑“组装”出来的语言并不能解决哲学问题。
他甚至醒悟道:
哲学家企图用逻辑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其实所有哲学的问题都产生于人们对语言的误会,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消除人们对语言的误用,回归到日常语言的轨道上来④。
当然,他还没有来得及消除人们对语言的误会,就在1951年被上帝从世界上消除了,享年62岁。不得不说,维特根斯坦还是太天真了,难道我们恢复日常语言就能解决一切哲学问题了吗?我们下一节揭晓答案。

1、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第五章语言的界限》
2、《五灯会元•卷七》
3、《庄子•田子方》
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16节》
第一章 (第十六节)
智慧超凡的佛陀竟然不认识猪?
01
我们上一节讲到,维特根斯坦主张恢复日常语言的使用,从而解决哲学上的困境。那么,恢复日常语言就能解决一切哲学问题了吗?
答案是,不能!
其实早在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和释迦牟尼就已经给“语言”判了死刑。老子之所以说“名可名非常名”,就是为了表示: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能够靠语言描述出来的,包括一只鸡,一棵草,一块石头,哪怕它就是一个字。
因为只要是说出来的,就会同时造成两种结果:
一种是描述的不够精确,一种是理解的不够全面。
总而言之,但凡是说出来的或者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像摄像头三百六十度拍摄的那样完美,肯定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偏差。释迦牟尼也同样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为了教育弟子,经常会采用“沉默”的方法来暗示。

比如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正在精舍里打坐。到了中午,有两个屠夫抬着一头猪从他面前走过。
释迦牟尼睁开眼睛问道:
“这个是什么?”
当时好多弟子都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佛陀嘴里说出来的。其中有一个弟子听到以后,还忍不住笑了出来,说:
“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识。”①
这个发笑的弟子意思是说,佛应该具备天文地理人事的一切知识,怎么连猪也不认识呢?
释迦牟尼回答说:
“问了才知道。”
这个禅宗的公案历来都被解释成释迦牟尼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其实错了!为什么?因为除非是释迦牟尼二十九岁刚从皇宫里出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见过猪,所以不认识,才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三十五岁的时候才在菩提树下悟道,然后开始弘法传教。这中间有六七年的时间,除了苦修以外,他也拜访过很多名师,游历过很多地方,怎么可能没有见过猪?
所以,这个故事应该讲的是释迦牟尼第一次用这种特殊的“沉默”来寻找知音,可惜那个时候摩诃迦叶不在身边。结果等来的不是会心一笑,而是捂着脸的嘲笑。

02
那么请问:
释迦牟尼为什么不直接说“猪”的名称,而只是说“这个”?
因为他知道“猪”这个字一旦说出来,立马就会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笨、懒、肥”等等的许多猪的表面化特征,而且这是代代相传,耳闻目见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没有几个人能逃脱古人的“思维惯性”。造成的结果就是:
人们完全忽略了“猪”的本来面目。
所以他想通过这种“指着一个东西却说不出来”的方式,来引导弟子们转变思维,看取世界的本质。如果众弟子中有人能回答一句“不知道”,或许就会成为佛教中的第二个摩诃迦叶。

03
讲到这里,我们就应该知道:
当我们说到“猪”的时候,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猪,并非真正的猪。只是我们主观意识上所以为的猪,只是猪的一部分特征的集合而已。
所以斯宾诺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

“规定就是否定。②”
意思就是,只要我们给一个事物下了定义,就等于是同时否定了这个事物的本质。为什么?因为凡是能被下定义的事物,其所定义的必定是它的一些表面化特征。而事物真正的本质如果用语言和逻辑去描述的话,那是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借用佛家的话说那叫“不可思议”,所以事物的本质是无法被准确地描述和定义的。
而且关键的一点是:
我们人类的大脑,只能通过逻辑去认识这个世界,而逻辑又只能通过语言来记录和表述。
也就是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那些定义出来的表面化的特征去认识和想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那么请问,当我们一心一意地盯着事物的那些表面化特征的时候,还能够透视到事物背后的本质吗?
答案是,根本无法做到!
我们的心理其实就好比是一台电影摄像机,如果你把镜头聚焦到某一个点,那么这个点的周围的场景就会自动模糊化。就好像当我们欣赏一幅画的时候,如果你把目光聚焦到某一笔某一画,那么你反而看不清画的全貌。
结果就是:
我们会误把局部当做整体,误把片面当做全部,误把现象当作本质。
04
所以,从语言学上来说,像人狗牛羊、父母兄弟、仁义礼智、山水花鸟、历史、化学、地理等等,甚至包括文字本身。这些所有形形色色的各种观念上的“名”,都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纯粹只是我们主观意识上为其量身定做的“衣服”而已。
我们不能说“名称”就是“名”本身,就像我们不能说“人的衣服”就是“人”一样。
语言给内容穿上了衣服,方便认识内容的同时,也遮蔽了内容。佛教里的一部无上经典《金刚经》其实就是为了阐释这个道理:
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③。
什么意思呢?如来用语言说出来的这个“世界”,不是本来的世界,是人们约定俗称的、名义上的“世界”。所以,老子才同样提醒说:
“名可名,非常名。”

1、《指月录•卷一》
2、《斯宾诺莎书信集•第50封》
3、《金刚经第•三十品》
你好!欢迎来到新统国学的世界,这里是当代人的国学院!我是紫侠狼,一个立志复兴传统文化的90后,研究《道德经》十四年,累计读书2.5万小时,目前正在全网连载《酷说老子》,每天更新,预计全书120万字。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会竭尽全力,不做任何保留,秉持“用科学开释国学,以新统承继传统”的理念,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帮你打通各个学科之间的理论壁垒,用我十几年来搭建的知识体系为你架构一条通往《道德经》的天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