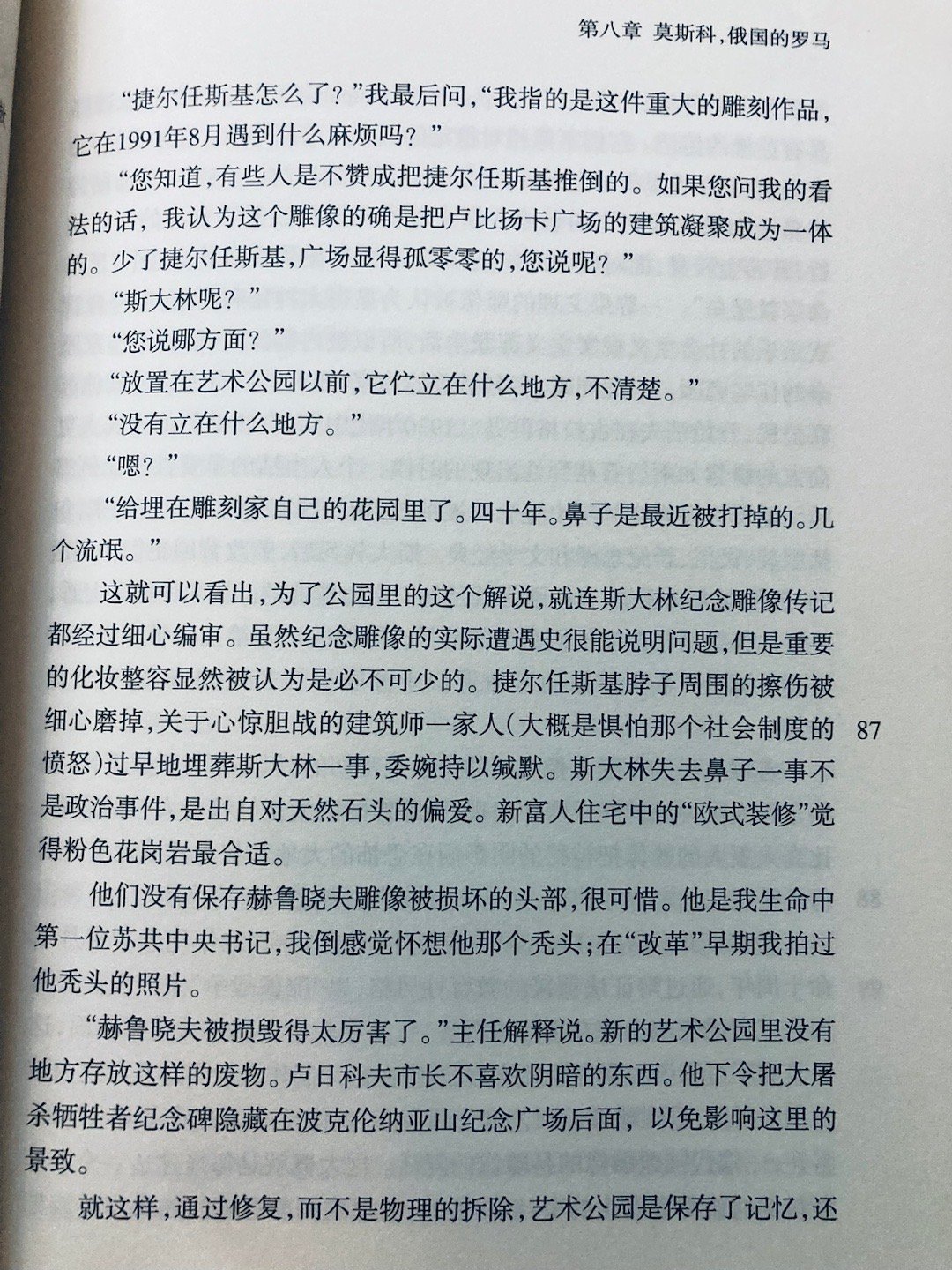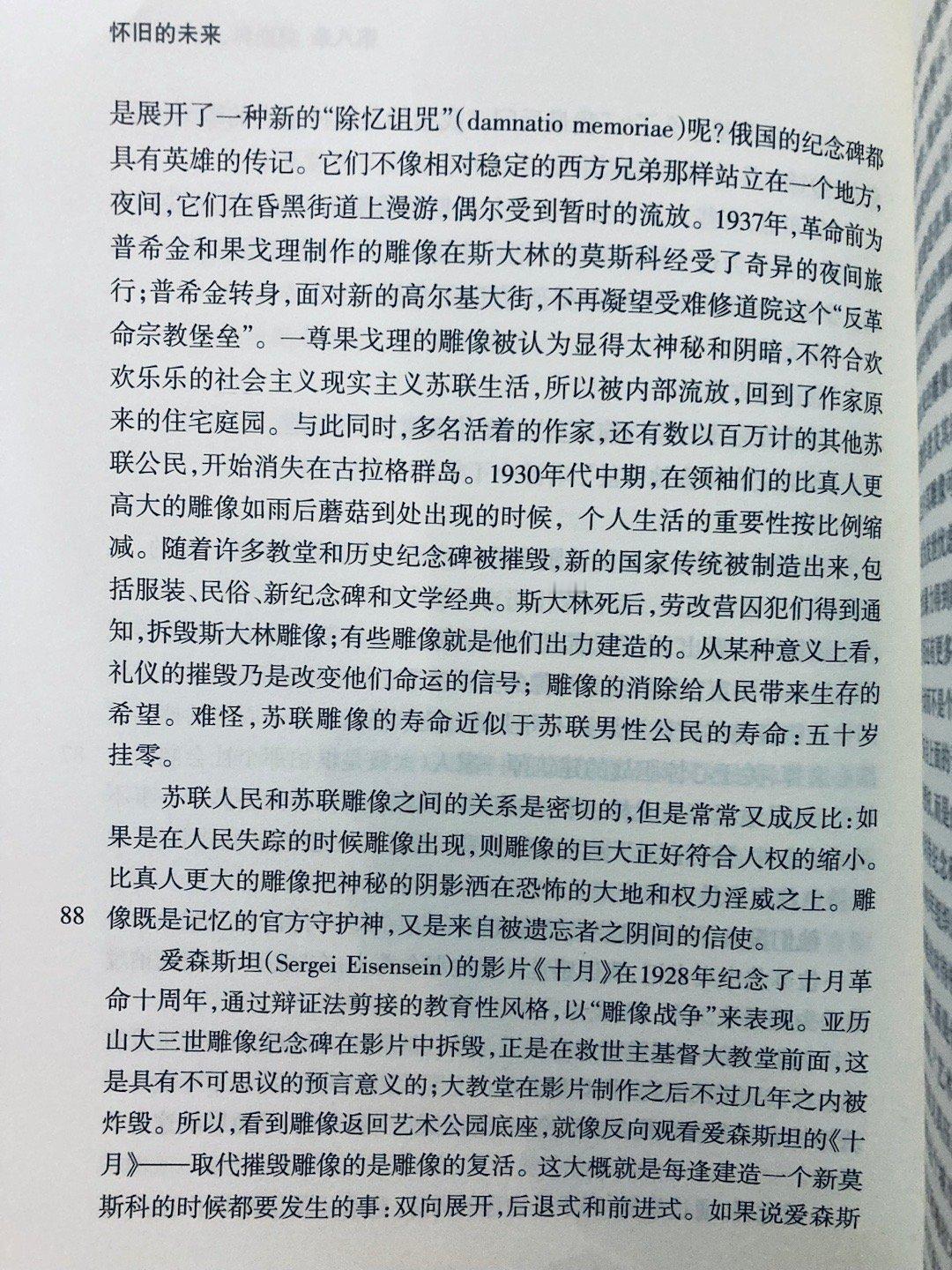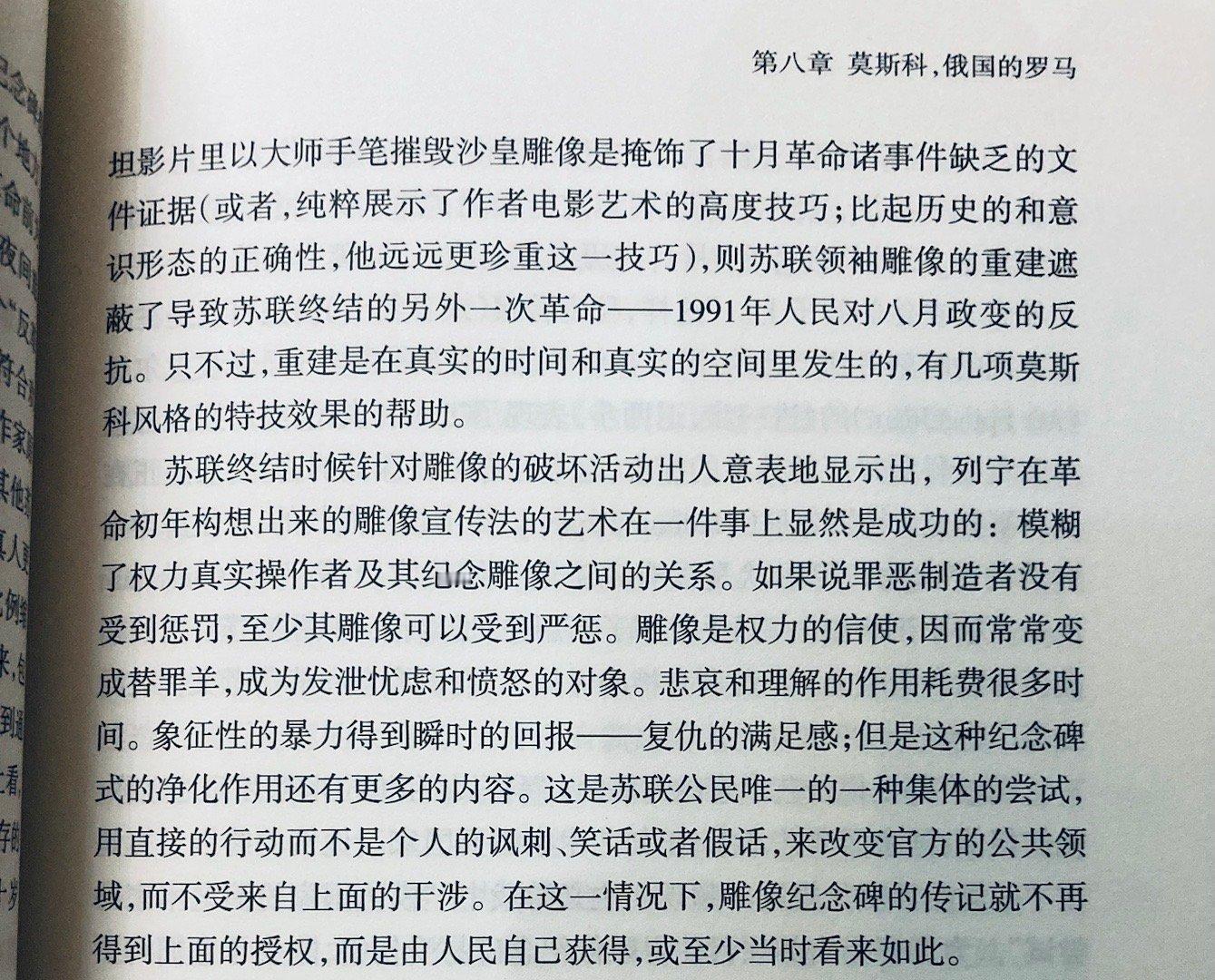苏联人民和苏联雕像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是常常又成反比:如果是在人民失踪的时候雕像出现,则雕像的巨大正好符合人权的缩小。比真人更大的雕像把神秘的阴影洒在恐怖的大地和权力淫威之上。雕像既是记忆的官方守护神,又是来自被遗忘者之阴间的信使。……苏联终结时候针对雕像的破坏活动出人意表地显示出,列宁在革命初年构想出来的雕像宣传法的艺术在一件事上显然是成功的:模糊了权力真实操作者及其纪念雕像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罪恶制造者没有受到惩罚,至少其雕像可以受到严惩。雕像是权力的信使,因而常常变成替罪羊,成为发泄忧虑和愤怒的对象。悲哀和理解的作用耗费很多时间。象征性的暴力得到瞬时的回报——复仇的满足感;但是这种纪念碑式的净化作用还有更多的内容。这是苏联公民唯一的一种集体的尝试,用直接的行动而不是个人的讽刺、笑话或者假话,来改变官方的公共领域,而不受来自上面的干涉。在这一情况下,雕像纪念碑的传记就不再得到上面的授权,而是由人民自己获得,或至少当时看来如此。(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