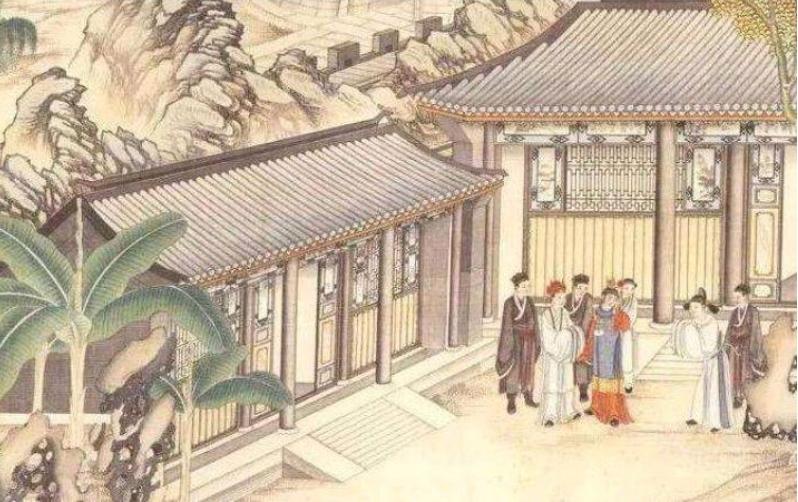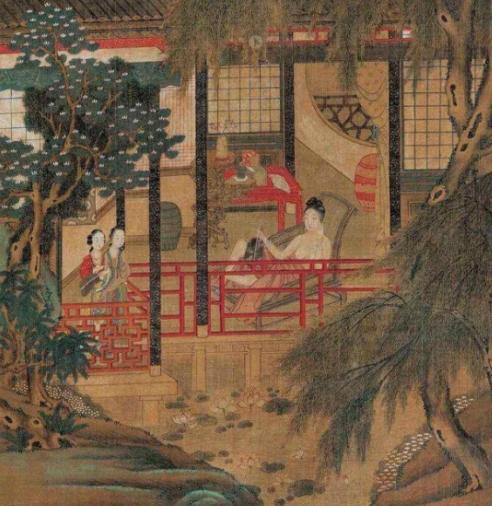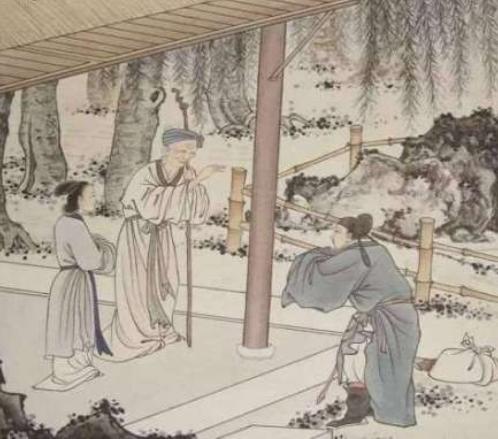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歌文章都是文人的笔墨,那不懂读书识字的普通人,日常用什么语言交流呢?不会文言文的老百姓,交流信息只能打手势吗? 先秦时期,在《诗经》编纂成书之后,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其内容来了解民生疾苦和地方风俗,上层贵族和统治者还将《诗经》的文字作为外交辞令,在重要场合见面会谈时,人们会首先引用《诗经》的相关诗句来开启话头。 在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诸子争鸣时代,各家学派也喜欢在辩论时引经据典,被使用最多的就是《诗经》的内容,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诗经》成为了人们交流思想、辩论学术的重要语言材料。 不过,以上事例都是接受过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要让普通群众在谈话时寻章摘句难度很大,其实古人日常交流的语言和近代的白话很相似,明清时期,不少通俗小说里人物的对白就是古人日常说话的现实写照。 唐代有位诗人叫王梵志,他的诗歌虽然知名度不高,也不太为文人群体接受,但百姓却很喜欢听,因为非常通俗易懂。 在现在的敦煌文献中收录了300多首王梵志的白话诗,他的诗词即使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都能轻松读懂,如“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或者“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不要小瞧这些接地气的白话诗,这种通俗直白的日常语言风格对后来的文艺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红楼梦》中妙玉最早居住的地方就叫“馒头庵”,这所尼姑庵名字来源于南宋文人范成大的诗歌《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其中那句“纵有千年铁门坎,终须一个土馒头”。 范成大“土馒头”的意象和灵感,就来源于王梵志的馒头诗,可见王梵志的诗歌在宋明文坛的影响力。 而普通百姓日常用语,嬉笑怒骂其实和今人差不多,最早收录在《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讲述了民间一起离奇曲折、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无辜冤死的书生就叫崔宁。 小说中人物的对白就是日常口语,妻子对离家的丈夫说:“得官不得官,早早回来。”面对丈夫另结新欢,妻子反唇相讥:“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个小老公。”如此种种充满烟火气息的对白在书中比比皆是,可见古人的日常说话并不是咬文嚼字、文绉绉的。 《红楼梦》中各色人物的刻画非常写实,我们通过说话风格能够清晰地判断他们的身份地位。如文化修养不高的王熙凤,生气撒泼时骂人“天打五雷劈五鬼分尸没良心的种子”“死娼妇”“狗肏的”等,简直和现在泼妇骂街别无二致。 甚至地位尊贵、温文尔雅夫人小姐们,在气急败坏时也会“出口成脏”。一次贾母欢天喜地给王熙凤过生日,结果贾琏被捉奸在床,贾母气得大骂他“下流东西,还不去挺尸去”。 宝玉做错了事,母亲王夫人骂他“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就连娇滴滴的黛玉,在和宝玉私下玩闹时都会说几句脏话,一次宝玉要睡黛玉的枕头,絮絮叨叨说个没完,黛玉嫌他多事,就骂他“放屁”。 在明代通俗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太后见到因战乱走失的公主,因质疑她的真实身份,便问她:“柔福在虏中受不得苦楚,死已多年,是我亲看见的。” 可见古人日常生活时,无论文人雅士还是贩夫走卒,口头用语都是非常直白接地气的,基本等同于现在日常交流的口头语。 更有意思的是,古人很多日常用语在现代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络热词,比如曾经流行的“囧”字,这个字并非新造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囧是光明的意思,现代人之所以喜欢用它,因为从字形上看,这个字就像一个很愁闷的垂头丧气的表情。 另一个词“悲催”也成为了网络热词,在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中有“阿母大悲摧”的诗句。 除了小说,古人在文章里也会用到白话,如朱熹的《朱子语类》,在谈论“格物致知”时说:所以格物,便要闲时理会,不要临时理会。 这和我们以前读到的诘屈聱牙、深奥难懂的古文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可见古人为了说理清晰流畅,也会使用白话,让读者一看便能领会其中含义,完全不需要翻译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