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朱德动用“特权”调用了一架直升机。随后,他赶紧写信向组织上检讨:“因为我女儿受伤非常严重,我想救她,为此我严重违反了纪律,请求组织上惩罚!” 1926年4月18日,一个小女婴在莫斯科啼哭的第一声,宣告了朱敏的来到这个世界,她的父亲朱德已经40岁了,对这个晚年得来的女儿倍加疼爱,给她取名“四旬”,寓意她是父亲四十岁时的掌上明珠。 然而好景不长,朱德必须立即回国参与革命,他的妻子贺治华对朱德早已厌倦,带着朱敏留在了苏联,不久后贺治华与另一男子结婚,并把朱敏托付给自己的姐姐,让她带回中国照料。 自此,朱敏被抛弃,在成都外婆家度过了童年,她的名字也改为“贺飞飞”,不再提起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次,邻里孩子问她:“你的爸爸妈妈呢?怎么从不来接你?”这让朱敏意识到自己与普通孩子的不同。 外婆和姨妈对她遮遮掩掩,不肯说起她的身世,直到有一天,她在街上无意间看到悬赏海报,上面印着“朱毛”二字,姨妈才悄悄告诉她,海报中的“朱”字,就是她亲生父亲的名字。 想见父亲的心情萦绕在朱敏心头,成为她第一个牵挂的念想。 1938年,周恩来总理在重庆辗转打听到朱敏的下落,立即派人将12岁的朱敏接到延安,当周恩来第一次看到朱敏时,不禁感慨地对邓颖超说:“这个孩子长得真像朱老总!” 1940年11月,朱敏满怀喜悦来到延安,四处张望着父亲的身影,这时,她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高高的土墩上,顿时确信就是自己思念已久的父亲,朱敏开心地大喊:“爸爸,爸爸!”朱德也一眼认出女儿,大步跑过来紧紧抱住了她。 在父亲身边,朱敏感受到了朱德内心的温暖,明白他之所以离开自己,是为了革命大业,朱德也尽力弥补这些年的遗憾,细致入微地照顾女儿,向她诉说着对新中国的期盼。 见到女儿让朱德欣喜不已,他立刻打电报告诉远在苏联的毛岸英这个喜讯,叫他转告朱伯伯放心,毛岸英这样做后,朱德喜极而泣,给女儿写了封信,表达了思念和歉意。 1941年1月,按照组织安排,朱敏与其他革命后代一同前往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为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赤英”。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朱敏与20名不同国家的孩子一起被德军关押,成为小囚徒,1943年,14岁的朱敏与5名女孩被送往德国一个残酷的纳粹集中营。 集中营内,朱敏目睹了无数残忍的杀戮,深感绝望,为了自保,她装作哑巴,很少说话,生怕泄露身份。这导致她语言能力退化,说话不再流利。 在营内,朱敏与其他孩子过着牲口般的生活,仅能食用发黑发霉的面包充饥,长期营养不良使她头发脱落,发育停滞,身高不再长高。 还患上了颈部淋巴结核,集中营的医生对她实施不人道手术,导致脖子上留下永久的疤痕。朱敏在绝望中学习着坚强,渴望早日重见天日。 1945年1月,在苏联红军解放下,朱敏离开了集中营,她在难民收容所继续隐姓埋名。一个政委终于认出她的身份,立即报告苏联政府,斯大林亲自下令,护送朱敏去莫斯科。 在莫斯科,朱敏收到父亲的来信,两人隔空相认,女儿的委屈与父亲的内疚都在信件中倾泻而出。 战后,朱敏选择留在苏联继续未完成的学业,1950年,她回国探望父亲,两人别离已有10年。朱德开心地傻笑,眼中却含着泪花,朱敏提起被德军搜走的派克笔,朱德安慰她要珍惜现在。 1953年,朱敏学成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65年,她主动参加到山西农村的调研工作,一天晚上,朱敏在崎岖山路上不慎坠崖,重伤濒危。 同事们知道朱德十分反对特权,但此时刻不容缓,他们还是联系上了朱德,请求派直升机将朱敏紧急送医。 朱德在电话那头踌躇许久,他原则极严,从不轻易动用特权,然而女儿的安危关乎自己一世的幸福,他最终还是忍痛同意。 在医生救治下四旬幸免于难,但右眼已毁损无法复原,当父亲问起伤势时,医生说再晚些送来恐怕就救不回性命,朱德这才松了一口气,也因破例动用直升机而深感自责。 这是朱德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动用特权,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尽管组织没有对他处罚,但他的内心却永远无法释怀。 在四旬心中,父亲是威严的,也是慈爱的,正因这样的父亲,她活了下来,也坚定了为革命奋斗的信念,成为一名老师,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以报答父亲与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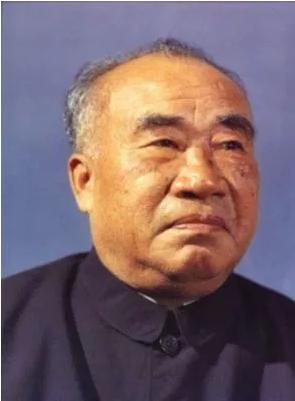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