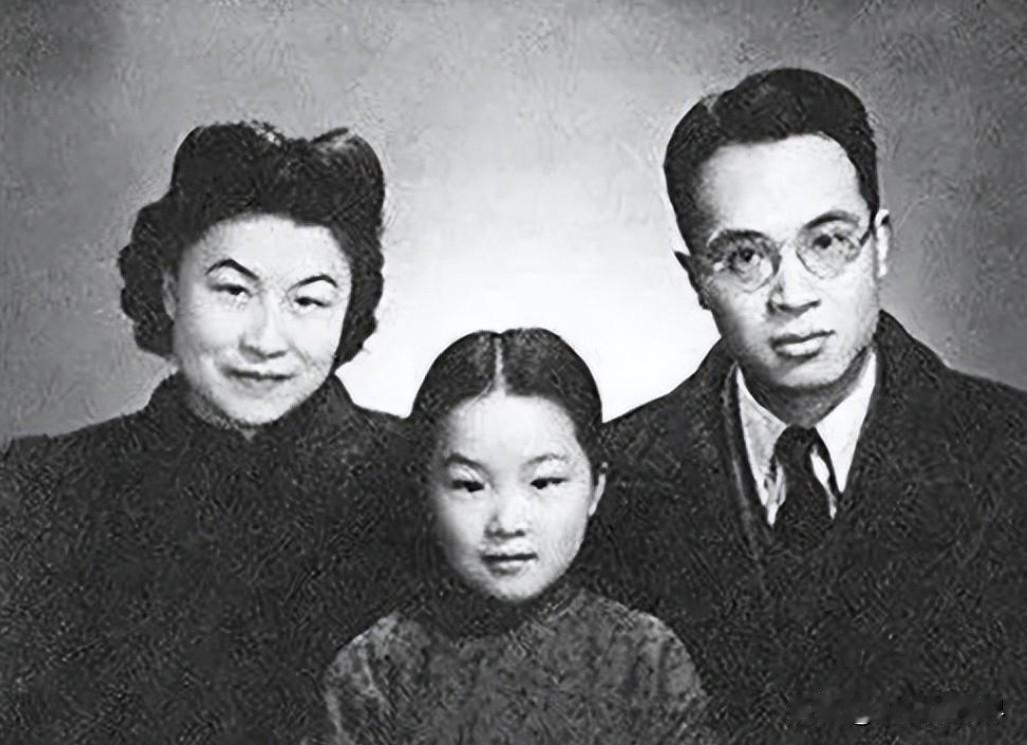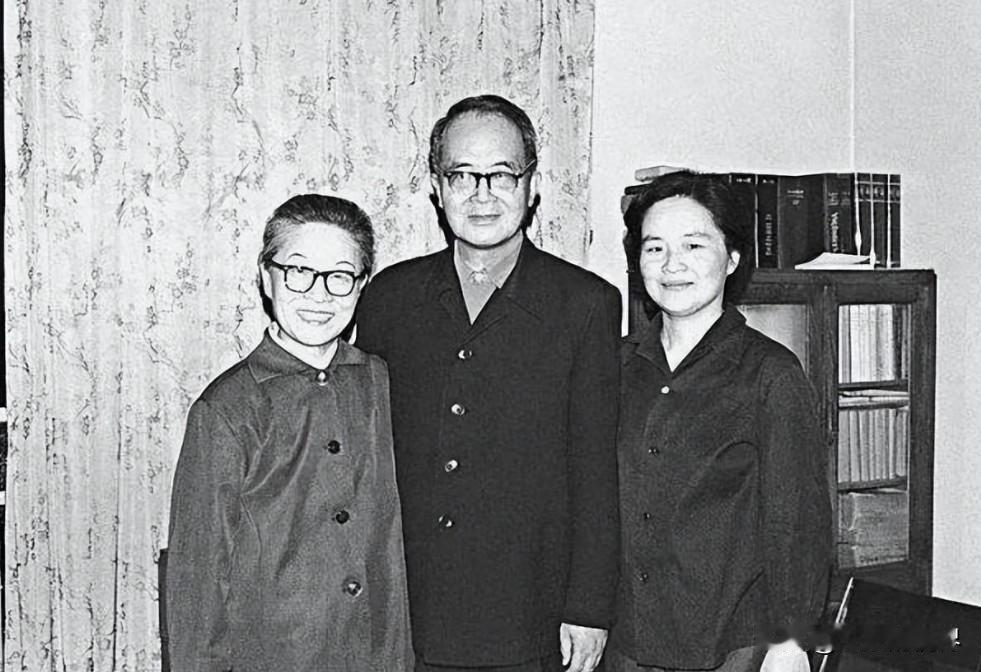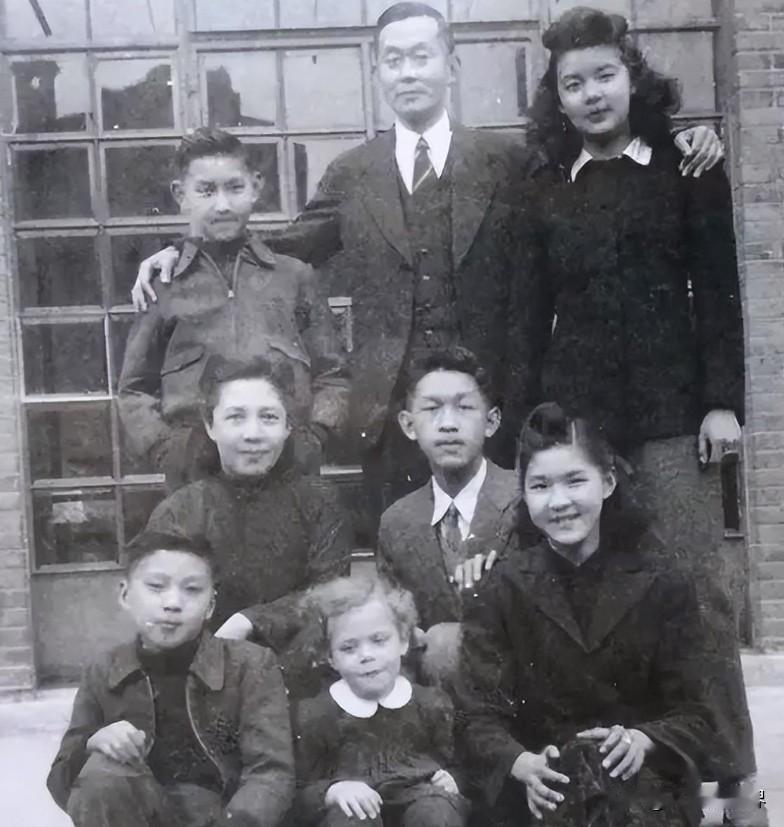1997年3月3日,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去世。杨绛瞒了4个月,开始小心翼翼地,一天透露一点消息给钱钟书:“圆圆现在没病了”“圆圆能安眠了……”其实,躺在病床上的钱钟书,心里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但到第7天,杨绛明说:“她已去了”,钱钟书的体温立即上升,身体不住地颤抖! 杨绛泪流满面,问丈夫:“如果我聪明点,能够骗过你吗?” 1994年,随着秋风的到来,钱锺书的健康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家庭,钱锺书随即被送往一家专业医院接受治疗。 仅仅一年之后的1995年,当家庭还在为钱锺书的病情担忧时,另一个不幸的消息又悄然降临。钱瑗这位才华洋溢的女儿,也因为癌症而不得不住院治疗。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杨绛承担起了双重角色,她成了家庭与外界之间的桥梁,这位文学家的伴侣,用她的笔,记录下这段家庭的苦难历程。 每天她往返于两家医院之间,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联络员”,她的双脚踏破了无数条前往医院的路,心里装着对家人的深深牵挂。 面对钱锺书杨绛选择了沉默,她没有勇气告诉他,他们的女儿也正面临着生命中的巨大挑战。她只字未提关于疾病的恐惧,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阿瑗住院了,而心中的忧虑与不安,却只能深藏不露。 在那个艰难的时期,钱锺书的心中充满了对女儿深深的挂念。尽管病魔侵蚀着他的身体,使得他日渐衰弱,但他的父爱如同坚不可摧的灯塔,照亮着黑暗中的希望。 1996年7月,钱锺书已是病床上的常客,身体的疲惫几乎让他难以承受坐立的重量。对女儿的深切思念驱使着他,挣扎着坐起来,手握笔给女儿书信。 与此同时,钱瑗在未收到父亲的信之前,已经预感到了父亲的劳累,心怀柔情地回信,嘱咐爸爸不必再费力书写。在与病魔抗争的同时,她试图以孩童般的乐观安慰父母的心。她的信中总是画着笑脸,那简单的笔触却承载着深深的爱与安慰,如同在告诉父母,无论生活有多苦,她仍能以微笑面对。 钱瑗在信中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她尝试以轻松诙谐的语气缓解父母的担忧。 她谈到自己最新的体检结果,如同向父母报告一场小胜利:“星期一我去做了CT,医生说胸水又少了,骨头的情况也有所改善。” 随着1996年10月的来临,钱瑗深感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时光正在缓缓流逝。在这生命的黄昏时刻,她心中升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用文字留下与父母共度的宝贵记忆。在她眼中,这些日子虽然平凡,却充满了爱与温暖,是她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于是,她向母亲杨绛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够用《我们仨》这个题目,亲手书写一个关于她与父母生活的故事。 在病床上,钱瑗开始了她的写作旅程。尽管疾病让她的身体日渐虚弱,但她的心灵却异常坚强。她的笔下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庭的深情。她以断断续续的力量,完成了五篇文章,这些文字如同她生命中最后的烛光,闪烁着温柔而坚定的光芒。 2月26日,杨绛轻声地对她说,是时候放下笔了,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休息与恢复。 面对母亲的关切劝告,她展现出了难得的顺从,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将那支一直伴随她记录生活点滴的笔放在一旁。仅仅五天后,她在无声无息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深深的梦乡,永远不再醒来。 女儿钱瑗的逝世,给这个已经饱受病痛折磨的家庭带来了无法言喻的痛苦。 对于身处病榻之上的钱锺书,这个消息仿佛是一场即将降临的风暴,杨绛深知这对他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重击。因此,她选择了暂时守护这个秘密,不让悲痛的阴影笼罩在钱锺书的康复之路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绛继续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她的心里承载着沉重的秘密,却依然坚强地站在丈夫的身边。她时常给钱锺书念读阿瑗生前写下的文章,这些文字充满了女儿的智慧与温暖,仿佛阿瑗还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分享着生活的点滴。 经历了四个月的漫长时间,钱锺书的健康状况终于开始出现了稳定的迹象,杨绛试图以最温柔的方式,逐渐向钱锺书揭开真相。 “圆圆现在没病了”,她轻声地说,接着又补充,“圆圆能安眠了……” 躺在病床上的钱锺书,并非毫无察觉。这些日子里,他的心如同静水深潭,表面平静,内心却波涛汹涌。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些温柔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段无法接受的事实。 直到第七天,当杨绛终于鼓起勇气,明确地告诉他:“她已去了”,那一刻,钱锺书的反应强烈而直接。他的体温骤然上升,整个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如同内心所有的防线在那一刻全部崩溃。 面对丈夫如此强烈的身体与情绪反应,杨绛的心也跟着沉重下来。 泪水不自觉地从她的眼角滑落,她带着一种几乎是自责的语气问丈夫:“如果我聪明点,能够骗过你吗?” 1998年的冬季,钱锺书也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面对着亲人相继离去的现实,杨绛感慨万千地说:“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一家三口,曾经相互扶持,共同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如今却只剩她一人独自面对寂寞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