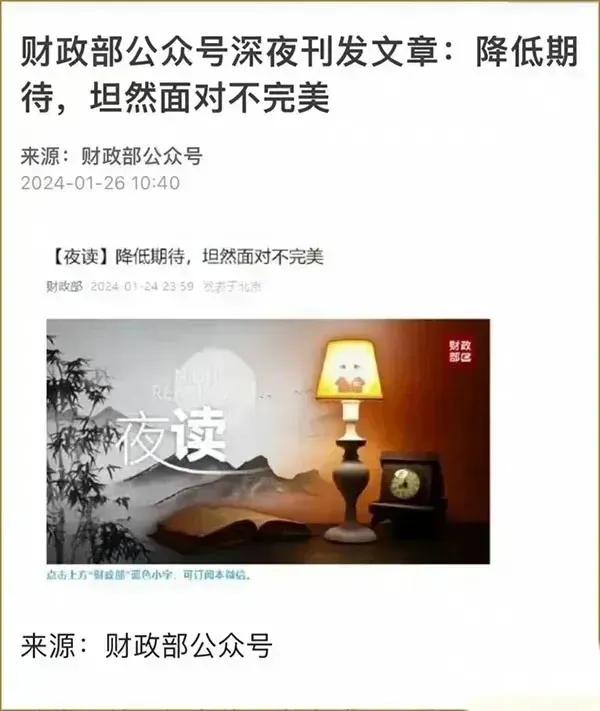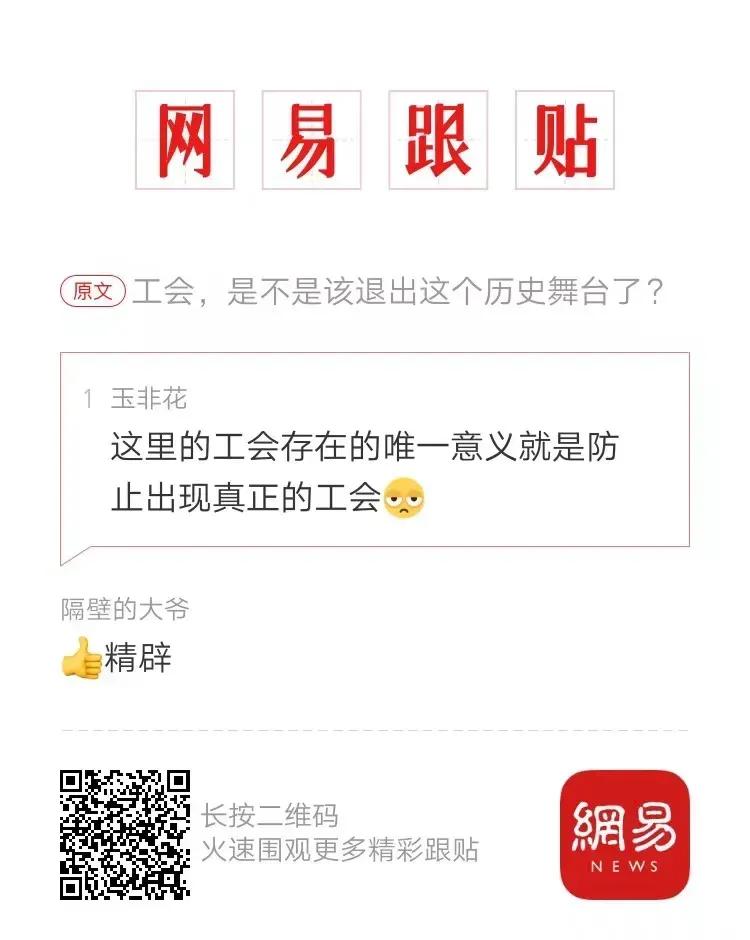“智库”一词,简而言之,是用政策研究成果服务政府决策的一类社会组织,一般为非营利性质。据考证,“智库”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人士和文职方面的专家一起开会讨论并制订战略计划的活动,因而具有某种军事和战略色彩。 对智库的内在运行逻辑,可以简单概括为:募集社会资金,生产研究产品,提供政策建议,推动政策优化,从而实现自身的公益价值。 就其性质而言,美国智库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讲,美国智库是指以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目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研究机构、研究型大学和独立智库三种类型。官方研究机构是美国政府体系之中各部门依照法律或命令设立的各种研究机构,主要为国会、总统和其他独立管制机构提供政策咨询和服务,类似于中国政府各个部门当中的研究室或者研究中心。但这些机构在美国特定的政治语境当中,逐渐呈现出边缘化的特征。 研究型大学即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大学,特别是一些知名高校当中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如针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有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耶鲁大学的中国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外交政策研究所等,其主要特征在于运用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及政治运作提供智力支持。 从狭义上讲,一般用语中的智库主要指第三种类型,即独立智库。这种智库是诞生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一种特殊民间组织,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为目的,多呈现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政策研究机构。这类智库最大的特征是其“独立性”,独立性是保证研究质量和打造影响力的前提,也是高质量智库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立足的重要基础。 具体而言,独立智库有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独立智库一般独立于政府,也就是有其政治上的独立性。正如余章宝教授所言,独立智库“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不是政府科层中的一个等级。政府既不能影响组织成员的构成,也不能决定它们所研究的问题,更不能左右它所做出的研究结论,尽管有些结论是政府不愿意和不喜欢的”。只有独立于政府之外,智库才能获得至为宝贵的立场上的独立性,保证其研究成果以质量为上,而不是一味地逢迎、解读。 其次,这些智库虽然需要资金的支持,但并不是为了谋取利润而从事政策研究,更不为特定的捐款人服务,也就是有其财务上的独立性。换言之,智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公益组织,而不是商业团体的代言人,其本身不是一种拿钱办事的经济组织,而是依靠社会捐助进行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因而,智库试图在接受捐款的同时保证其自身的独立性,不像利益集团一样为某种特定利益团体服务,不是资本的代言人。并且,一般的捐款规则也造就了一种职业伦理,即捐款人无权在立场或结果上对接受捐款的智库的研究成果提出要求。 最后,独立智库,即便是意识形态智库,也应该有其立场上的独立性。立场上的独立性要求智库不能从属于政党和政治意识形态,尤其要求智库从事实出发,依靠可靠的证据、严密的逻辑、科学的分析寻找问题的真实答案。与此相反,则是先从特定的立场出发选出自己想要的答案,然后再寻找数据支持自己的答案。 独立并非对立。智库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也需与政府决策者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私人关系,而且对决策提出优化建议也并非是对政策制定者的否定。大量的美国独立智库尽管在财务或政治上是独立的,实际上也有着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背景,也就是说,独立不等于中立。不过,有政治立场的智库同样强调独立性。比如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由于其自身贴有鲜明的党派标签,其研究的客观性很容易受到质疑,这些意识形态智库反而更加强调研究的独立性。正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对笔者强调的:“我们与共和党分享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唯命是从。我们依靠优秀的研究来阐述观点,所以我们对于共和党来说应该算是忠诚的反对派。”当然,沃尔特·罗曼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无论如何,明显的政治倾向还是会或多或少地伤害意识形态智库,让其信任度大打折扣。在里奇近期的一项调查中,传统基金会的信任度排名第九,远远落后于布鲁金斯学会(该学会的信任度得分最高)。 独立性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相比欧洲和日本,这种特色显得更为明显。如在德国,智库基本都属于政府资助,并与政党有着直接的联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就与著名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有着直接的隶属关系;社会民主党(SPD)旗下则有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则拥有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巴伐利亚);自由民主党(FDP)则有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而在日本,类似美国智库的政策研究功能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智库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有限。非官方智库也多由企业主导设立,比如野村、瑞穗、佳能集团等,旗下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2000年之后,日本智库发展经历重组期,由于资金不足(国库补助金削减)等原因,部分智库解散、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