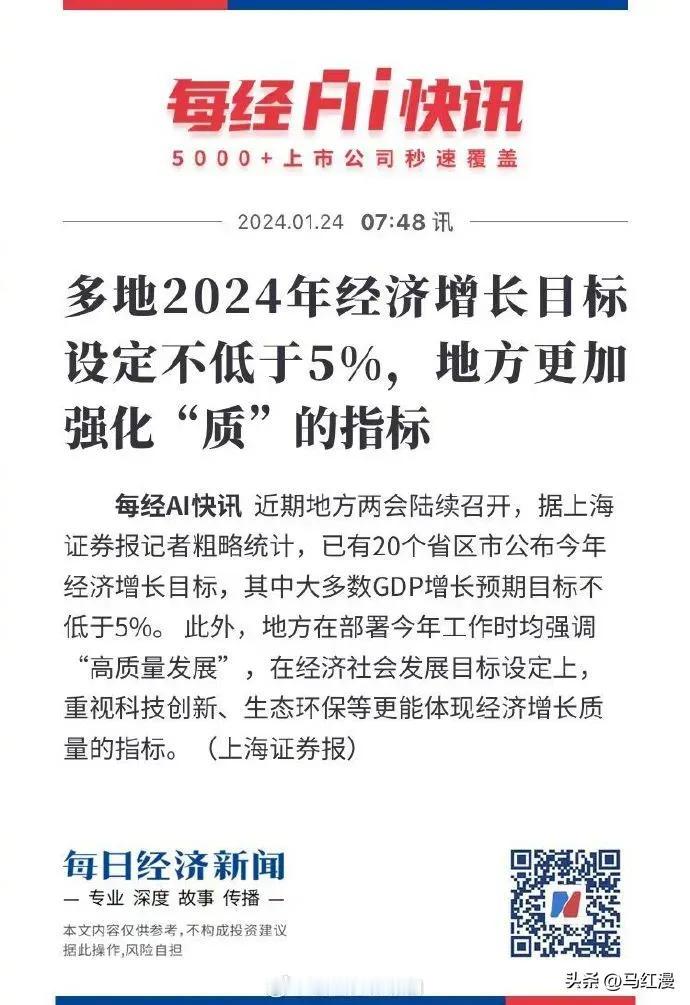文丨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从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流入中国的外资(FDI)由正转负。市场都认识到这是基本面的一大变化。但很多关于外资的讨论是情绪驱动的,并不代表长期趋势。 过去30年,外资对中国的意义已经转变,从最初的市场引领者变为和中国企业旗鼓相当的参与者。然而,即使中国能够自给自足,外资仍然至关重要。 在经济下行期,市场悲观情绪严重,外资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冲悲观预期的稳定器。 因此我们想要加入这个讨论,澄清关于外资的四个误区。 第一,FDI不等于跨境资本流动。 美国经济历史学家Kindleberger在1969年的经典论文中指出,FDI本质上是对生产资料控制权的转移,而非资本本身的跨境流动(包括跨境金融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本流动)。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巴西和墨西哥,跨境资本流动和FDI的波动性差距极大。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资本流出为389亿美元(金融账户负债净产生),但FDI流入为155亿美元。 国际资本流动会被境内外利差和汇率等因素影响,其中有套利动机。但实体经济关注的是市场容量、增长潜力、产业链便利性和地缘政治等,并不是单纯的金融指标。 这是为什么FDI和跨境资本流动经常不是一个方向。 第二,外资不等于经济增长。 海内外学术研究关注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但并未得出“外资会带来经济增长”这个结论。 由于增长强劲的国家总是会吸引更多的外资,因此会高估外资的积极影响。跨国公司的目标是最大化股东权益,会通过总部重新分配、利润转移和利用空壳公司降低税收等方式调整在不同国家的投资组合。而这些目标和当地经济发展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 外资引进需要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超越阶段的投资并不一定能带来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书中提到过一个例子。世界银行在1970年代帮助坦桑尼亚造了一个鞋厂,使用进口机器和最新的制鞋技术,最初目标是大部分的鞋出口欧洲,其余供应当地市场。然而自建成以后,从来没有出口过一只鞋。这个工厂的设计并不适合坦桑的气候,当地也没有原材料和配套零部件。自建成后,该厂从未使用超过4%的产能,后来就关停了。这说明,仅仅引进外资是不够的。 外资有时会带来贫困化增长。也就是说,外资涌入投资建厂能拉动GDP,但是普通人的收入没有提高。因为外资利润没有继续投入接受国,也没有消费,而是汇回母国。比如,墨西哥由于不重视技术转让,事实上成为外企的加工厂,并没有从中得到额外的好处。 第三,外资不只在离开中国。 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不仅在离开中国,也在离开欧洲。从欧洲流出的资本规模更大,这主要是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引起的。从欧洲流出的外资大都去了美国,第二、三大目的地是分别是东盟和拉美,也有一部分转移至中国。例如瑞士的特种化工产品公司克莱恩和英力士,荷兰化工巨头阿克苏诺贝尔等公司都在加速在欧洲以外的市场投资。其中,全球最大的聚合物生产商德国科思创、德国默克和巴斯夫均在2022年将部分产能转移至中国。瑞士克莱恩也在2022年底对其位于广东惠州大亚湾的工厂追加第二条生产线。 近几年,全球吸引FDI流入最多的地方是美国。特朗普当政期间,美国吸引外资达到历史新高,之后拜登总统上台后有所放缓,但在俄乌冲突之后又创新高。有不少美国企业投资回流,包括GM,Ford这样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也包括Intel这种涉及芯片制造的企业。另外,由于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美国吸引金融投资也是全球最高。 美国的劣势非常明显。因为工会势力大,劳动力成本高,不少制造业企业事实上无法达到最初的目标。比如富士康在2017年宣布要在美国威斯康辛投资100亿美元创造1.3万个工作岗位,然而2021年计划就调整为投资672万美元,最多创造1454个工作岗位。这其中的一大障碍就是无法满足当地工会对于工资的要求。 但美国的优势也同样突出。 首先,美国能源价格低,对于高耗能企业有吸引力。比如德国钢铁公司ArcelorMittal减少了在德国的投资,因为其在美国德州工厂的表现好于预期。 其次,美国的产业政策补贴加码。比如,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为低碳生产技术提供慷慨的补贴,荷兰的化肥制造商OCI计划在美国德州扩产。 2022年,特斯拉也暂停了德国工厂建设,将目光转向美国。 第四,长期增长的源泉不是资本,而是技术进步。 长期来看,资本不可能成为增长的源泉,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 因为资本投入边际收益递减。 但为什么美国的资本更多却仍在增长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技术进步抵消了资本收益递减。 刚刚去世的诺奖获得者索罗(Solow)极为简练的总结了这个规律: 能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唯一途径。#畅谈国际投资# #资本市场的贡献# #经济学讨论# #经济该如何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