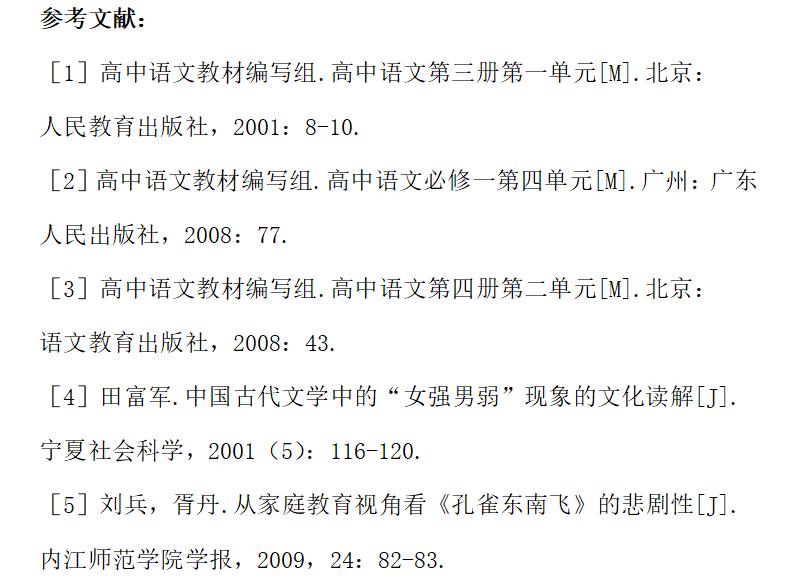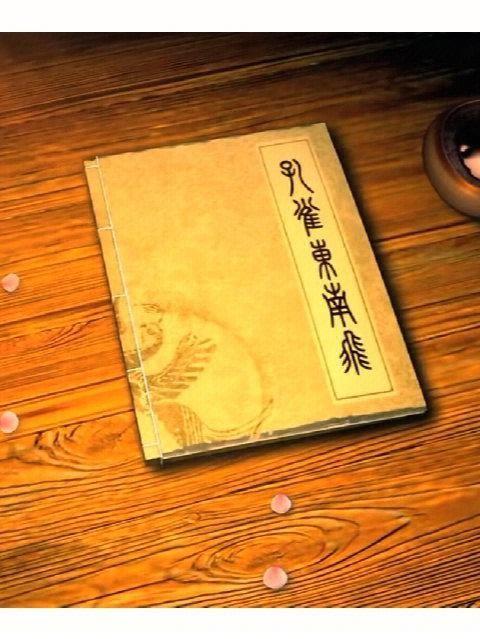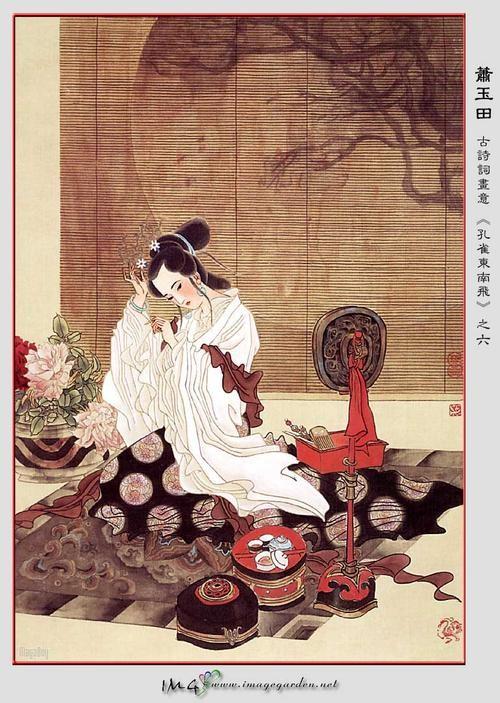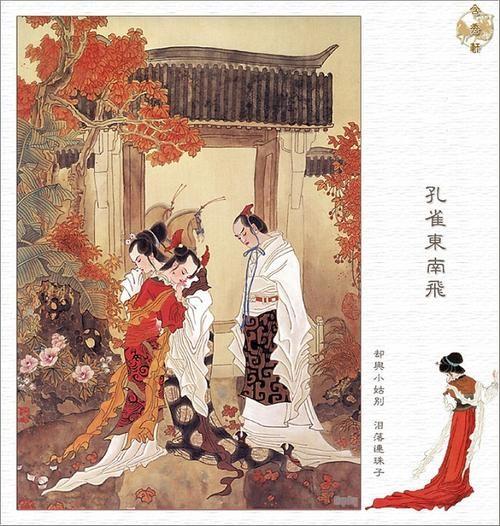作为古代民间文学,《孔雀东南飞》中有哪些塑造上的“女强男弱”现象? 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的光辉诗篇,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因其对后世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常收录于高中语文教材。 后世以爱情为主题的叙事诗、传奇、话本、戏曲、小说等作品中,我们常能发现《孔雀东南飞》的影响痕迹。 在中国古代爱情类叙事文学较有影响的作品中,较突出、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女主人公的形象比男主人公更丰满、动人、突出,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女强男弱”。 就整个中国文学来看,写女性之强,在先秦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偶见之,例如《山海经》中的精卫,留给读者的是其意志坚定、不畏艰难的精神。 又如西汉刘向所编的《列女传》,记载了上古至西汉约百余位具有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的女子。 只是,当时的单部作品往往仅涉及女之“强”,极少甚至没有涉及男之“弱”,因而不能形成鲜明的“女强男弱”对比。 而且,我们这里所说的“女强男弱”,是指爱情类题材、并且男女处于同部作品中,才具有可比性。 可以说,《孔雀东南飞》是开创“女强男弱”这一典型模式的最早作品之一。 我们在体会到悲剧美的同时,也能发现全诗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别出心裁。 对于全诗的中心人物刘兰芝,作者借鉴汉赋的铺陈手法,采用骈俪之词,在容貌、装饰、作息、才情上进行细致描述。 因此相对于其他人物,刘兰芝这一人物形象能够脱颖而出,显得更为丰满、动人。 对于男主人公焦仲卿以及婆婆等其余人物并不作外貌、才情的描写,而是直接以动作或对话的形式展现。 因此除了对他们性格特征的掌握以外,我们对他们的其余方面并不熟悉,如此,全诗“女强男弱”的对比就十分鲜明。 诚然,《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拥有理想女性的一切优秀条件。 诗中对其外貌不惜一切溢美之辞:“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读到这里,一个天生丽质的美人形象仿佛向我们徐徐走来。 “女为悦己者容”,刘兰芝的着装打扮也可谓无可挑剔:“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 先天的优越加上后天的点缀,一位绝代佳人仿佛款款走到我们面前。 对于其内在修养方面,记叙其“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其能力才情更是令读者赞叹不已。 可见,作者重墨描写了刘兰芝的内外兼修,目的在于强调如此难得佳人,竟然无法博得婆婆的青睐,以增世人同情惋惜之意。 尽管外表看似柔弱,刘兰芝骨子里却是一个自信、自我、为爱坚贞不屈的女子。 首先,刘兰芝是充满自信的。诗的开篇就是她的一段自我评价,内在修养高,做事又勤恳,在刘兰芝自己看来,这样的媳妇本应是无可挑剔的。 其次,刘兰芝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在对丈夫的诉说中,她提到“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一个“故”字可见刘兰芝对婆婆的观察入微。 另外,分别时她提到兄长“性行暴如雷”,担心不能如愿,事后也证明了这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再次,刘兰芝具有独立主见,不肯屈服于强恶势力。这点从她的语言和行为上都能体会得到。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段痛苦的申述,已经显示出她不能受婆母驱使之气,自请归家的意图。 被休后,刘兰芝先是断然拒绝了第一次的说媒,就连第二次说媒的答应,也是哥哥在征得她同意后才进行的。 当心爱之人误会自己,为了证明其爱“纫如丝”,更是留下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激烈言辞。 最后刘兰芝在婚礼前夕的“举身赴清池”,竟如此毅然、决绝,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相比刘兰芝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外柔内刚,男主角的形象则相对单薄许多。 诗中并没有涉及焦仲卿的外貌着装,因此我们只能从他的行为举止上了解这个人物。 诗中,焦仲卿不论是说话还是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甚至有些畏手畏脚。 其实,焦仲卿的表现也并非是他对残酷的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而是他的懦弱,他行为方式抉择的女性化使然。 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认为“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面对母亲无理的“休妻”要求时,他也曾为妻子辩护:“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甚至放出了“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的言论。 然而单亲家庭长大的焦仲卿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于依赖母亲的性格。 在处理母亲与妻子的矛盾时,焦仲卿往往表现出优柔寡断,在爱情与亲情的夹攻下迟疑不决。 当母亲槌床大怒:“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时,孝顺的焦仲卿也只能选择“默无声”“哽咽不能语”,让妻子暂回娘家:“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 这一段自我辩白,也充分显示了焦仲卿在判断问题上的迟疑性。 就连最后的殉情,焦仲卿也没有刘兰芝那样果断决绝,而是“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可见他到死还是无法摆脱那份迟疑与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