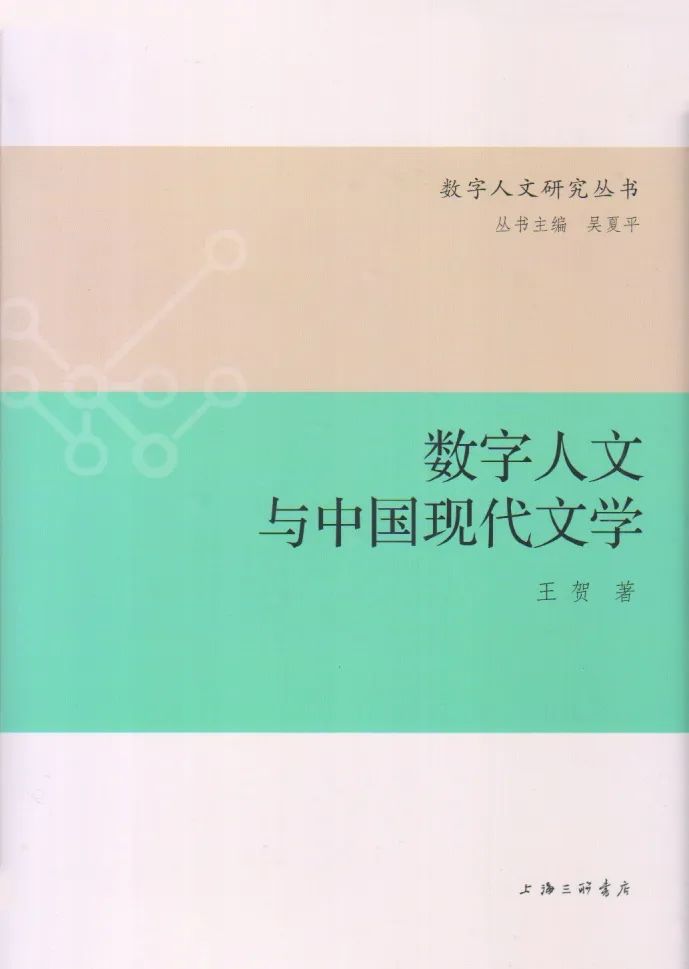
《数字人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王贺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8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首度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数字人文的概念、理论、方法、工具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并以多个数字人文取向的现代文学研究个案,开拓了“数字现代文学”及其相关新领域的研究。
该书作者为中国大陆学术界较早开始数字人文研究的知名青年学者,曾首倡数字人文应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结合、建构“数字现代文学”等一系列观点,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书也是从数字人文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可供数字人文、中国文学、文献学等领域研究者参考。

目 录前言
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何谓数字人文?数字人文何为?
第二章 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
第二部分 历史、理论、方法与技术
第三章 数字人文与现代文学研究
第四章 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数据库、网络资源与数字工具
第五章 现代文学研究史的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第三部分 专题研究
第六章 制作“数字鲁迅”:文本、机器与机器人
第七章 朝向数字人文:现代文学手稿研究之省思
第八章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予数字人文研究之启示
第四部分 数字人文内外
第九章 从研究资料集的编纂到专题数据库的建立
第十章 “数字读写能力”的作育

内容节选
大多数学者对互联网、数据库的利用只限于一般性的浏览、下载和引用,但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研究方法,顶多只是一种利用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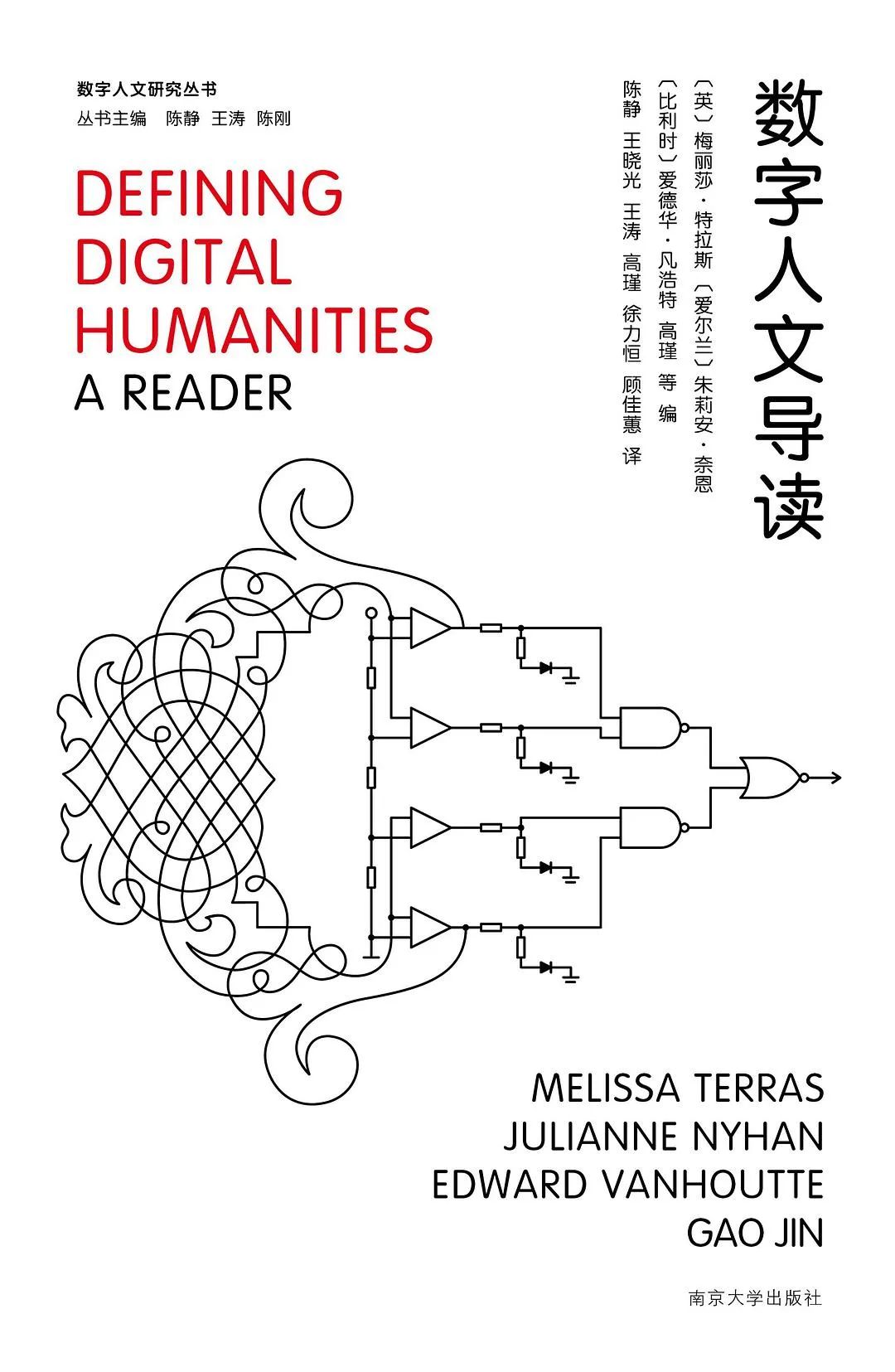
《数字人文导读》
例如许馨《网络资源下的学术研究——以丁玲研究为例》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示了从材料搜集、分析、组织到写作(相对较少)各个环节如何利用网络资源的过程。
但也正如前文所述,此著代表了十余年前学界对网络资源之于学术研究的一般认识,未能考虑、处理这样的问题:除了书中所举资源,在国内外还有哪些数字资源可以利用?不同的数字资源之间,有何性质、形式和内容的不同?有了全文检索资料库,研究者还需要什么?应该怎么做?……
同时,更有论者发现,该书引用文献多为传统文献的电子化、数字化版本,但这些传统文献并非源自近现代图书、报刊等处的原始文献,而是当代期刊论文数据库中的二手资料,[1]忽略了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资源乃是原始文献,可谓问题多多。
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著亦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它的出版表明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互联网、数据库所扮演的角色绝不限于材料搜集一方面,且相关研究取向、方法的探究迟至2008年已引起学者(尽管来自图书馆学领域,而非是专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注意,此后势必也将激发同人更多、更深入的理论思考与研究实践。

《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
总而言之,与传统的、依赖纸质文献进行的专题研究不同,互联网、数据库不仅极大地扩充了我们的研究资料,而且使得我们获取这些研究资料的途径变为线上,以更加即时、便捷的方式取得全文(对此我们或已习焉不察),帮助我们重新理解那些相对比较熟悉的文献资料(亦即笔者所谓的“常见书”)的意涵,更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的实验空间。
这一基于互联网、数据库的学术研究的变革,也部分地解释了何以近年来文学、史学各领域专题研究不断加增、愈益趋于精耕细作,且研究论文和著作(包括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字数、体量不断扩大的普遍趋势。其实这同样也是下文所述“互联网研究方法”及“数字人文”等取向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根源。
从互联网、数据库中寻获现代文学文献的全文,并对其进行整理、研究,是另一种常见的研究取向。[2]这种研究取向,与古文献学的“辑佚”类似,因此也被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研究称为现代文学辑佚之学。
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基本上源自传统的辑佚学、考证学、辨伪学、校勘学等领域。具体做法是先检索到所需要的目标文献(即“发掘”),然后进行考证、辨伪、辑录、校勘(即“整理”),并作初步阐释或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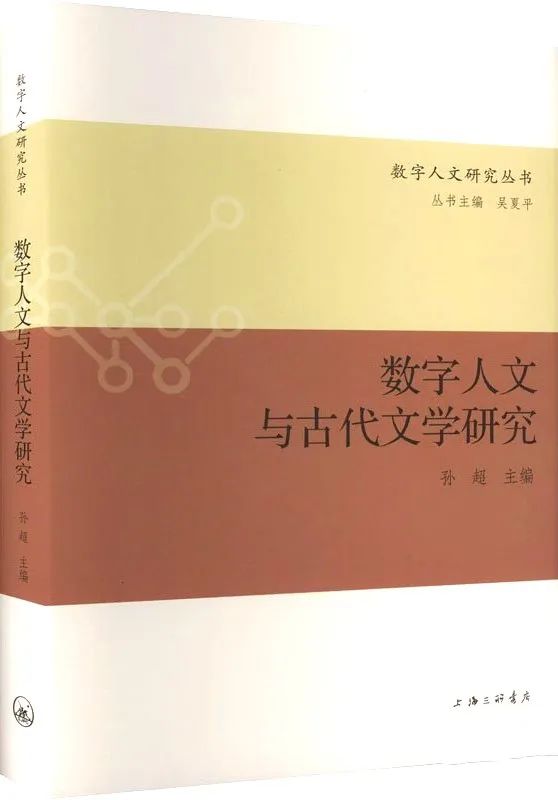
《数字人文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般表现为“发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订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史实,解决或部分解决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悬案或疑案。”[3]尤其辑佚实践在近年来成绩显著,可谓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文献学卓有成效的一个部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争议,如有学者批评其间存在的“伪发掘”、“伪佚文”及“不少赝品‘史料学问’”等问题,[4]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也不能因此否定此一研究取向的合法性、可行性、有效性。
其间能够运用的检索策略大体已如上述,但除此之外,对于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及研究而言,在互联网、数据库中采取“漫无边际”式的阅读(desultory reading)这一传统的阅读方式有时仍然需要。
其与“大海捞针式”的检索不同,后者仍是以检索所需研究资料为导向、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是一旦找到自己的研究资料,就停下脚步,然后转身去建构自己的学术伟业;而“漫无边际”式的阅读,则近似于鲁迅所谓的“随便翻翻”[5],即指我们置身学校、图书馆、书店甚至自宅时的随便翻翻,只不过我们的学校、图书馆、书店和书斋此际已变成了在线的web世界,我们的目的非为检索、查找资料,专事学术生产,而是为了获得知识所进行的至为普通不过的浏览、阅读,抑或藉以消遣、满足自己好奇心的需要。

《数字人文与语言文学研究》
但在同时,作为专业人士,出于专业训练、职业习惯和对文献资料的敏感,我们也随时准备着与传统文献学者在漫游纸质书刊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发现的愉悦”[6]的感觉相遇,与某些令人愉悦、惊喜甚至厌恶、愤怒的“意外的发现”相遇。
如有学者即在浏览“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中的《河南民国日报·平沙》副刊时,无意间寻获一封“漫铎”(汪漫铎)写给巴金的信,从而对巴金自法国留学归国后的社会关系、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试验性的思考。[7]
但如果只是纯粹的文献整理、重刊,而不作研究、阐释,还有一个“史料首发权”[8]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尊重首次发掘、整理新文献的研究者的工作,凡引述这一新文献,须注明是何人发掘、整理之版本,或至少说明此一线索最早自何处见到,[9]然而,窃以为,作为一般性的学术规则、纪律,它可能较适用于互联网、数据库未诞生之前的学术生态,在其之后,就很难做此硬性要求了。
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学者可以借助同样的互联网、数据库资源,运用同样的检索方法、手段,获得这一文献的全文并予整理。

《数字人文导论》
虽然一些发掘、整理实践的完成时间较早,发表、出版也较早,因此从学术规范、伦理角度来说,应该尊重这些先行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先行研究既有被后之来者全部掌握的可能,且由于后起者作了同样的工作、重复了同样的程序、甚至可以利用来源更为广泛的互联网、数据库资源,所得结果将更为可观,而在其检得新文献后,又花了同样甚至更多的时间去校勘、整理、注释,甚至其间运用的文献学方法、手段更为彻底、充分、科学,因此使得其整理、研究成果更为精良、完善,我们又有何理由忽视?[10]显然这同样需要我们作出积极的评价。
其实不独辑佚,校勘、目录之学等其他文献学的分支如今也都遭遇着严峻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应该由互联网、数据库、数字工具负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其工作性质造成的。
以校勘而言,如胡适所说,“校勘学是机械的工作。只有极少数问题没有古本书可供比堪,故须用推理。绝大多数的校勘总是依据古本与原书所引的古书。”[11]因此,“两个学者分头勘同一部书,结果当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相同。”[12]但能否因此就说这两个学者的校本(甚且完成于不同的时间),必然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抄袭与被抄袭的关系?恐怕也不一定。

《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
因此,一种合理的态度或许是:我们既需要尊重先行的整理、研究成果,但同时也要准备着为后出转精之作鼓与呼,对这些最新发表的成果,作出与其贡献匹配的合理评价。
互联网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于对现代文学在当代的阅读、传播、接受等方面的研究。但与上述两种方法不同,更为专门,其中既包括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EM/CA)等实证研究方法,也有“互联网民族志”(netnography)等。[13]
前两者“在人机交互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14],后者亦称“数字研究的民族志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似更为密切。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网站、博客、微博等是其研究地点,而使用这些媒介的用户的行为、表达则是其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对象的在线访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互联网文本的文化研究,为我们了解新的媒介技术如何进入某一特定情境,人们如何将这些技术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工作、娱乐,其间身体体验和思想观念将会如何改变等问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描述和解释。
这一方法的核心仍然是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例如,信息科学研究者佩德罗·费罗拉(Pedro Ferreira)和克里斯蒂娜·赫克(Kristina HÖÖk)的论文《身体如何适应移动设备:来自瓦努阿图的启示》(Bodily Orientations around Mobile: Lessons Learnt in Vanuatu)[15]就展示了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的方式,一探美拉尼西亚群岛瓦努阿图居民如何接受、使用手机这一“新鲜”事物的“新鲜性”,“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西方实践,以及这些研究对象的活动。”[16]

《新数字人文导论》
贺麦晓(Michel Hockx )关于中国网络文学的研究,也部分地使用了互联网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17]葛涛编选的《网络鲁迅》《网络张爱玲》《网络王小波》《网络金庸》等资料集,及其所著《网络鲁迅研究》《互联网上的“作家迷”虚拟社区研究》等专书,亦皆显示出一定的开创性。
但毫无疑问,运用上举这些策略、方法,仍不能完全地解决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全部问题。除了基础设施、设备和作为用户的研究者个体的信息素养、“数字读写能力”等因素,都制约着我们利用网络、数据库及数字工具,以展开研究的专业技能、水平,无论是互联网资源,还是数据库,自身都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克服、解决,发展出相应的因应之道。
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到社会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影响,一种旨在超越信息检索的新的研究取向——“数字人文”——也逐渐进入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发展》

作者简介

作者近照
王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数字人文学科负责人,上海市“数字人文资源建设与研究”重点创新团队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索引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青年专家”,《中国数字人文》杂志主编。主要从事数字人文、中国文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注释:
[1] 牛犊:《读〈网络资源下的学术研究——以丁玲研究为例〉》,网址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275410100ci91.html,2020年4月12日检索。
[2] 有研究者曾简略地讨论了纸质文献之于文献整理、研究的局限性,并谓专业数据库在现代文学辑佚学者“那里早已悄然普及,”参金星:《于佛堂中言庙堂事——郭沫若佚文续考兼及民国报刊文献的数据化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 陈子善:《发现的愉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4] 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伪发掘”》,《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2日;倪文尖:《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致黄平》,《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吴宝林:《 历史感的缺失与“伪佚文”的辑佚——以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为例》,《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
[5] 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145页。
[6] 参陈子善:《发现的愉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陈子善、张德强:《钩沉辑佚,以小见大——陈子善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1辑,2019年3月。
[7] [日]坂井洋史:《巴金研究现状和前景——兼及文学史叙述的转型》,《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8] 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7-199页。
[9] 前揭书,第205-207页。
[10] 与谢泳的看法不同,有学者就强调了对网络文献必须实事求是、亲自阅读等七项引用原则,参见赵铭建、郑永果、傅德谦编著:《互联网资源检索与利用》(第2版),青岛: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145页。
[11] 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氏著《治学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12] 前揭书,第22页。
[13] [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9页。
[14] [英]萨拉·普赖斯、凯里·朱伊特、巴里·布朗:《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史晓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6页。
[15] Pedro Ferreira & Kristina HÖÖk. Bodily Orientations around Mobile: Lessons Learnt in Vanuatu,网址见:https://www.doc88.com/p-6601591625950.html,2020年4月14日检索。
[16] [英]萨拉·普赖斯、凯里·朱伊特、巴里·布朗:《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史晓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4-286页。
[17] 其专著《中国网络文学》(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尚未翻译出版,一个简要的介绍请参李婉容:《透视中国网络文学——谈贺麦晓(Michel Hockx)的新近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