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1974)是谁?如果说他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可能人们也会觉得不过如此。

但如果说,影响了二战之后四十多年的重大历史现象“冷战”一词,是在李普曼于1947年出版的一本叫《冷战》的小册子之后,成为美国报界和政界所共同采用的词汇,虽然李普曼不是冷战一词的发明者,但他绝对是“冷战”一词成为一种全球共识的最大推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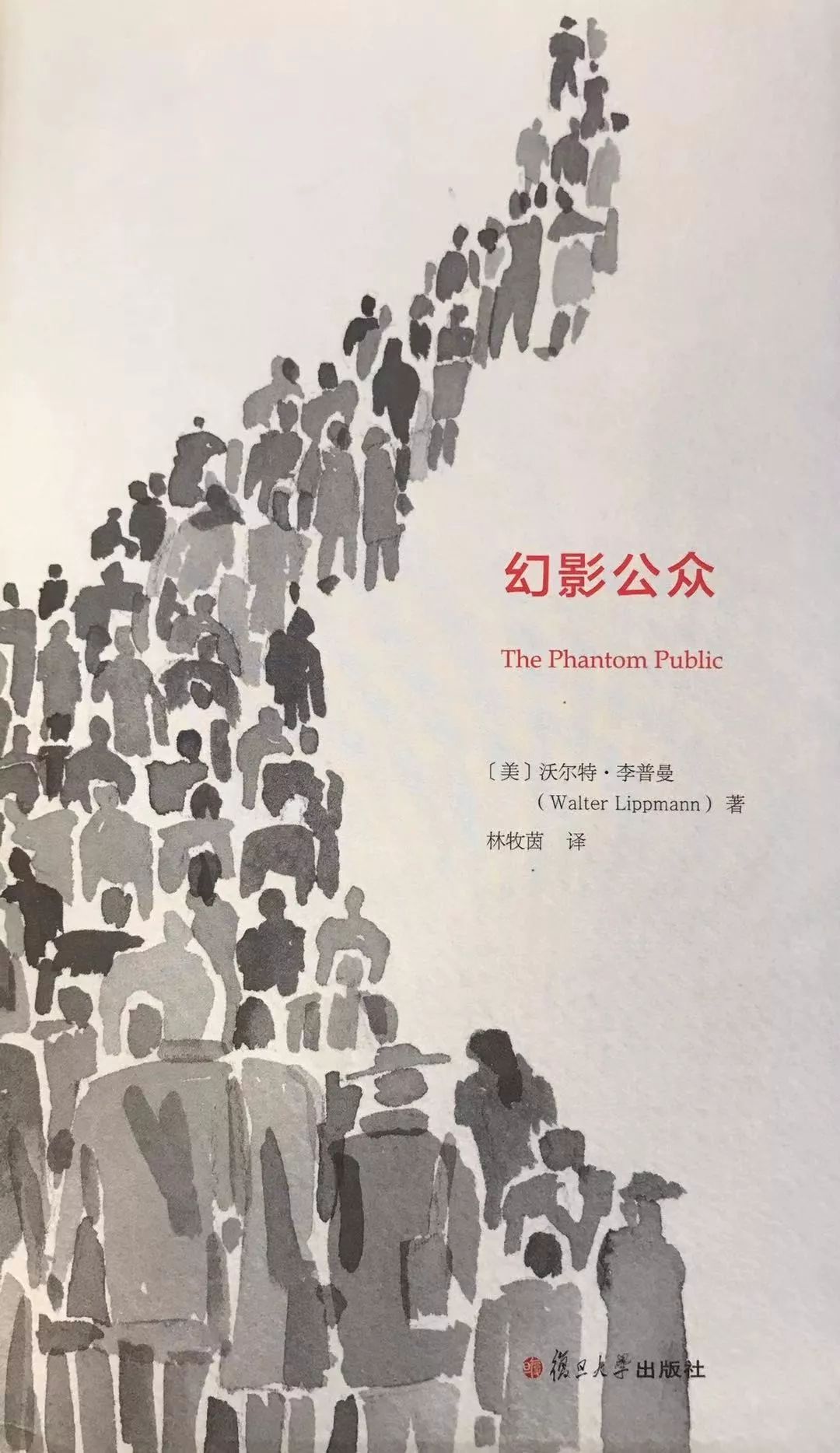
李普曼在75岁生日前被授予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也正是这样一位对美国非常重要的学者,却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中揭露出了美国民主的虚妄。
民众不是上帝,民主的地基也只是神话
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民众在政治活动中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大选中呈现出来的观点争锋以及民众对选举结果的左右。但针对这一点,李普曼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公众作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无法成功参与讨论,帮助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可以从外部做出判断,他们只能以支持某一直接利益相关方的形式参与进来。”

在《幻影公众》的开篇,李普曼就做了一个精妙的比喻“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
美国民主的神话就在于赋予了每一个普通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力,仿佛从大到国际政策、战争决定,小到医疗保险、税收增减的背后都是公民集体的意愿决定。

李普曼毫不留情地击碎了这个神话,首先作为普通公众,在当前纷繁复杂的政治格局之下,是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去做出理性的判断;就算能够获得足够信息,普通人也无法放弃自己生活中的琐碎事情,一心专注于政治;就算是人们可以一心专注政治,他们自身的水平也不足以支撑其做出有利的判断。
能不能靠教育来解决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问题?李普曼在书中也表达了对公民教育的失望。他提出了“代理者”与“旁观者”的划分,即普通公民大多都是政治的旁观者,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交由代理人去打理,这样自己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生活中的那些与自身更加息息相关的事情。

选举,就像是战争的升华,是革命的一种温和版本。但选举中少数服从多数的那种多数主义仿佛就是暴政的兄弟。李普曼指出,在美国公众舆论的主要作用,并不能直接对政治施加影响,但却是一个底限,公众舆论是反抗暴政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面对这一现状,虚妄的美国民主该怎么办?李普曼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他引用了笛卡尔的一句话“毕竟,我可能是错的;将铜币和玻璃当成黄金和钻石”。的确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谁都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解决路径。李普曼的方式就是区分出公民权和公共事务。

公民有权参与政治,但是一旦涉及到人数众多的公民的权力交锋时,问题必然变得摸糊,不再可能是针对于医疗制度、公路发展等具体情况,公民只能在大方向上选择与自己利益一致的代理人。将公民权让渡于代理人,由代理人实施公共事务。公民不能自己去处理公共事务,那样社会就会变得一团糟。但在这种区分之下,公民需要极大的发挥监督功能,提防着制度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及时的修正制度和更换代理人。
卢梭的“公意”和贡斯当的“自由”
其实李普曼所探讨的美国民主的问题,并不是他的独家发现。关于民主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在反复地批判。关于民主,知名度最高,最强力的鼓吹者可能就是卢梭了。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用一种精妙的论断,证明了民主的有效性。

卢梭理论的根基“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他提出了一个“公意”的概念,即人们将自己的自由和权力,转移给“公意”,然后绝对服从于“公意”。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意”实际上就是自己,服从自己就是自由。每个人这样做,就达到了整个社会的自由。
可以看出,卢梭的公意概念在社会契约论的体系下,实际上就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原始内核。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公意,由公意去指导社会的发展。但卢梭的理念,在后世不断被攻击,轻者指出其理论中的问题,比如公意是自身无法行动的,必须交由某一些具体的代理人来实施,他们并不是无私的完美的,而是有血有肉的自私的人,这样就相当将全民的权力让渡给少数的人;还有更重的指责是将卢梭的理论视为暴政和暴乱的元凶。

这些卢梭的批评者里面,有一位思想家,被后世称为自由主义的先驱——邦雅曼·贡斯当。在他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激荡李普曼的思想火花。贡斯当在其最著名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当中,对古希腊时期和18世纪欧洲的政治作了比较,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美国的民主并不是天生的,其实是脱胎于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政治。贡斯当一针见血的指出,古希腊时期的自由和民主,是有条件的——
第一、那时候国家很小,人们可以充分了解信息,同时政治决策也不多,无非就是国内的一些政策和对邻国的战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着公民的利益,他们可以直接发表意见;
第二、古希腊的城邦有着足够多的奴隶,在奴隶的辛劳工作保证下,公民才有参与民主政治的时间和精力。

这两点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李普曼对于美国民主的批评,美国国家庞大,人们无法了解信息,美国的政治决策也多,人们更无法深度参与,另外普通人都要忙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奴隶帮他们打理,他们就更没有时间去参与政治。
贡斯当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古代的自由——可以充分参与政治,但缺乏人身自由——和现代的自由——不太关注政治,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空间。在人类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事务越来越复杂的现代,人们更多的是退回自己的空间,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将政治事务教育专业人士打理。

本质上,从贡斯当到李普曼,都认同一点是公众是无法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而他们都将人们引向了一个更为丰富的价值观——多元论,也许这才是解决纷争的有效方法。
破除整体的迷信,用多元包容寻求平衡
李普曼在《幻影公众》里针对美国民主写到——
“我认为,迷惑的根源在于,企图描绘出一幅目标统一的社会统一体蓝图。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将社会想象成一个有机体,它只是一个思想、一个灵魂、一个目标,并不是男人、女人、孩子们的各种思想、灵魂、目标的集合。”
“不切合实际的拒绝承认社会由各种复杂关系组成,我们被迫接受各种版本的神话般社会概念的伟大学说,称之为社会society、国家nation、共同体community。”
“19世纪,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社会被人格化。每一个学说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主张将公众训练成为社会统一目标的代理人。事实上,真正的代理人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及其副手、社会改革者及其副手,然而他们却隐藏在幕后。”
“公众惯性地认为任何致力于民族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模式都应该得到支持,认为民族主义者的所思所为都是以民族国家发展为目标,这是爱国者的标签,认为改革者的初衷都是以人类更好的发展为目标。”
“人们不得不将灌输给他们的目标当成共同目标;如果接受,它将被强制执行;如果他看起来的确像是民族国家的目标,他将被作为制约一切的规则传承下去。”

正如歌德在诗中所说“这一奇迹终于得建,一种精神足以表达千种愿望。”
一体化的社会一元论,主张人们形成一个共同体,秉承同一个理念,达成同一个目标,消除了矛盾与纷争,在历史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发现这种论调的虚伪一面。

人们哪怕在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都很难达成一致。这世界上不止有一个真理,有佛教的也有基督教的,还有伊斯兰教的。强迫人们形成一个统一的的认知,不亚于用武力统一全球。想要解决问题,多元论可能比一元论更有效;寻求多方利益的平衡可能比彻底消除矛盾更现实。

而回到美国政治本身,既然美国民主是一种虚妄的假象,那么又怎么会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很多时候,人们往往被那些社会学的概念搞昏了头脑,把民主、自由、权力混为一谈。
民主作为美国的一种政治表现可能不够完美,但支持美国发展的并不是民主政治本身,而是隐藏其后的多元主义和对人权物权的尊重。多元主义的表现就是多种社会力量的制衡,以保证国家不会出现终极的暴政。而对人权物权的认可,是整个美国社会制度的核心,在这之上,才能开出美国梦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