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善作奇奇怪怪之文字,而此等文字多有深意。如《好了歌》,又如秦钟临死之前的鬼话,皆是如此。

《红楼梦长卷人物》
《红楼梦》第二回中有“正邪两赋”论,我们且来看文中的叙述: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版,2008,28—30页)
在“正邪两赋”论中,曹雪芹借北宋张载“气本体论”这一哲学基础,创出以气赋人理论,并借此将人群加以划分,继而通过这种划分,将情上升到哲思的层次。这就使得“正邪两赋”论既可作为哲思来进行解读,又有着很强的小说叙事功能。

《张载集》
这一过程的实现是极为巧妙的,而又颇为隐曲,读者若粗略读来则颇易忽视。

“正邪两赋”论的提出,乃是基于曹雪芹对历史人物的总结。其分类依据了儒家的评价标准,然而这只是表面的表达。小说中,在贾雨村的长篇大论之后有一段文字:
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此种论说无疑是一个大的翻转。

戴敦邦绘冷子兴
从正与邪所列人物而言,都是极有功绩的。这种功绩或被歌颂,或被批判,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成”与“不成”,因为结果的不同,从而成为“王侯”或“贼”,其根本却是建立在事功之上的。
小说中,“正邪两赋”论的提出是贾雨村通过“读书识事”,继而再去“致知格物”“悟道参玄”才得出的结论,其所下功夫自是不少。初始的贾雨村尚有几分书生意气,在经历了起而复败之后,这种意气已经所剩无几了。
冷子兴是一个依赖于世家大族的商人,当他将冷子兴视为“有作为大本领”之人来看,他的评价已经偏离了儒家的标准。在谈论“正邪两赋”之时,贾雨村的一句“正是这意”,使二人的表达与理解达成共识。而这种共识,才是曹雪芹借二人之口所表达的真实涵义。
如果就此对曹雪芹的历史观加以解读,我们就会发现曹雪芹有着更深一层涵义。曹雪芹是在借贾雨村之口,在儒家的评价标准之外,以自我的历史观去重新构建了一种评价。

《史记•孔子世家》
《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笔”与“削”,就成为撰史者的权力。如此境况之下,史书的书写中难免会有对“仁”的修补,或对“恶”的加强,以书写者的理想与需要作为雕刻史书之基础。
曹雪芹自然是深知这一道理,在他的创作观中,好人全好与坏人全坏的脸谱式书写是被批判的,“千部共出一套”的创作模式是被作为对立面的。
他更注意的并非是史传式的“事之真”,而是倾向于“理之真”。在这种历史观照下,历史人物的事功就会被消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就被突出出来,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

“正邪两赋”论中,无论是正,抑或是邪,实质上只是铺垫。他们均是为这段理论的主角“正邪两赋中人”服务的。

孙温绘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儒家入世,以“仁”为根本,以事功为要,强调的是人之于社会的关系,却未免有些忽略了人之于自我的内心慰藉。至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出,对人的桎梏更为加强。
然而任何时代都会有“异类”产生。如“正邪两赋中人”的陶潜、阮籍、嵇康,乃至红拂、崔莺。曹雪芹在列这个名单的时候,刻意将部分戏剧小说中人列入,从而与前二者形成明确分界。
当我们去解构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其中无论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还是“奉旨填词”的柳耆卿,更或者一生落拓的唐伯虎,他们都是无法从事功的角度来评价的。
正如贾雨村所说的,他们要么是“情痴情种”,要么是“逸士高人”,要么是“奇优名倡”,但他们不会成为“仁人君子”。他们既“聪明灵秀”,又“乖僻邪谬”。他们的“聪明灵秀”表现在他们的兴趣点上,他们的“乖僻邪谬”却是在人情世故之上。

电视剧《红楼梦》中贾雨村剧照
他们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人物,但也不会是大凶大恶之徒。他们关注自我,关注本真性情,追求的也不是人之与社会的事功。而正是由于这种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与不妥协,才会使得他们成为失败者。
在他们关注的领域内,他们是顶尖的天才,是居于“万万人之上”的。他们的生活是自我的、真实的、艺术的、审美的。他们只是不符合于主流的价值观,不符合于主流价值期待而已。
贾雨村说:“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至此,曹雪芹的目的已经明确,他就是要将贾宝玉列入“正邪两赋中人”,此中人的特性都是关注本真,关注自我的。而贾宝玉关注的是情。

正是为了表达情的重要性,曹雪芹才创作出“正邪两赋”这样独特的理论,以此来为贾宝玉的行为提供理论基础。

程乙本插图贾宝玉
在小说第一回中,有“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句。此句正是贾宝玉悟世的过程总结,“空”“色”之间的情就卓然独立,成为《红楼梦》的最主要表达对象。
在“木石前盟”神话中,曹雪芹就赋予了贾宝玉的本真性情“情不情”。《红楼梦大辞典》中对“情不情”的释义为:“宝玉对不知情者(无情者)也忠于情。”当神瑛侍者日日灌溉绛珠仙草之时,这种“情不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神瑛侍者下凡成为贾宝玉的时候,“情不情”又有了拓展。在小说第五回中,警幻仙姑谓之为“意淫”。无论是“情不情”还是“意淫”,都是有着特定对象的。
在小说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中,曹雪芹借两个婆子之口,将贾宝玉的日常行为做了简写:“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这正是“情不情”的表现。绛珠仙草、燕子、鱼、星星月亮,都是具有美好属性的事物,是美好的符号化表达。

《红楼梦图咏》之通灵宝石、绛珠仙草
至于意淫,也是有着特定对象。小说第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中,有一段贾宝玉的著名言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未出嫁的女子,少受世俗污染,保留了人的美好,是一颗“无价之宝珠”。而只有具有美好属性的人,才会是贾宝玉意淫的对象。
如此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作为贾宝玉“情”的付出对象的“色”,并非是佛教所言的事物存在方式,而是美好的事物。只有美好才是使神瑛侍者生出凡心、使贾宝玉所留恋的“色”。

桑田剪纸贾宝玉
换言之,对美好的向往、呵护、付出,才是曹雪芹认知中的情。在神瑛侍者凡间之旅的“悟”的过程中,他在体悟美好,享受美好。他付出以情,又在享受这种付出。因此他才能成为“正邪两赋中人”。
“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的贾宝玉,正是“天下古今第一情人”。他又是“正邪两赋中人”。如此的曲折表达,使得《红楼梦》不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本哲人的思考之书。

贾宝玉执着于情,故而他是“正邪两赋中人”。情的提出,是人性的舒张,这种舒张,是必须要放置于社会中去实践的。《红楼梦》的创作,也可视作曹雪芹的实践:他将自己的认知幻化为人格,变成小说中的人物,又以他所认知的社会规则,构建小说中的社会规则。他让小说中的人物游走于他所认知的社会规则之中,去经历、去推演,更是去追求。
叶朗先生在《“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一文中提及《红楼梦》的人生感悟集中在一点,那就是对人生(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2期)。而构建“有情之天下”大观园,正是曹雪芹关于人生价值的理想表达。大观园中集中了世间之美好,成为情的乐园,贾宝玉在其中恣肆着,留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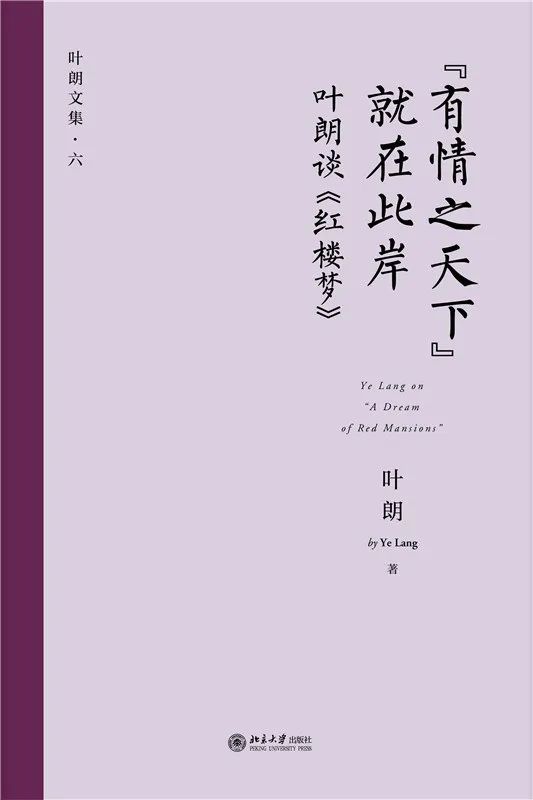
《“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叶朗谈红楼梦》
然而,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一个悲剧。大观园毕竟是在人间世的,美好也终归是毁灭了的,色终归是空的,“有情之天下”终归是不能存在的。这也就使得《红楼梦》的悲剧尤为震撼人心。曹雪芹的“他乡”与“故乡”之问,也就成为永恒的追问:无心安处,何处又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