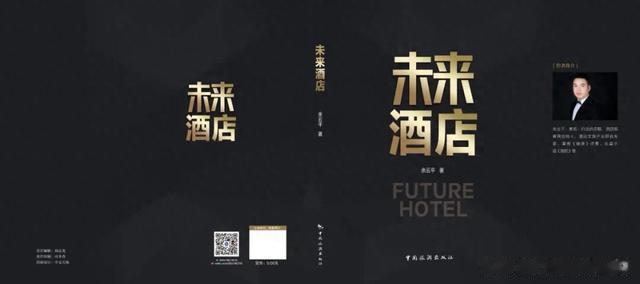
第一章:缘起-我的酒店启蒙
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走出家乡-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新疆。因为新疆地域辽阔,以小孩的力量是无法“翻越”如此的距离。我从小的认知是新疆就是祖国的全部。故而在整个孩童时期,甚至认为那个生活的小城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几万人口的小城规划整齐,横竖交错,高空看就是一个方正的圆圈坐落在河边。开车五分钟就能出城,随即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隔壁、河流、雪山。
我从小在想象着,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瓮里,这个瓮四面环山,密不透风。但眼睛看到的山是很遥远的,以至于在前十几年间从未踏足到山脚下。小时候父母总说“望山跑死马”。直到长大后坐上汽车、火车和飞机从那些山峦穿过与飞过,才感知那个瓮里是如此的狭小,但那山确实很雄伟,而山的那边更远大。以至于在后来时常回去的时候,那个瓮里已经容不下思绪。
第一次接触酒店是在2005年左右,因为在90年代末我所在的那个小县城的一个景点火了,并且火的一塌糊涂。那些年的旅游出行方式是旅游团为统治的时代,只要是个5A级景区,有一些特殊的人文景观资源,再加上一些电视报纸信息的宣传,可以让本来就不大又偏僻的县城很快就能拥挤起来。
这里的景区被挖掘之后,小城街道上开始出现最多的业态就是各种宾馆和饭店。当然,我可以毫不吝啬的说,这个景区就是新疆北部阿勒泰境内的喀纳斯景区。大约从2000年跨越新千年前后,这个小城因为喀纳斯景区而全国非常有名。确实如宣传的那样,喀纳斯的风貌景观是具有独特非常气质的。
被称为中国最像瑞士风光的一块地区,加上后来的“湖怪”出没故事的炒作,让这个景区愈发变的火热起来。结果是一个偏远的小城因为大自然馈赠的一个壮美风景而富裕起来。在这个以农业和牧业组成的边疆小城,本地人多了一个赖以生存的靠山,就是开酒店饭店哪怕开小餐饮店当游客司机,都能获得一个相对可靠的收益。
在我的记忆里,去酒店打工成了当时辍学青年的首要选择。因为自从我上初中开始,时常会发现身边的某个桌椅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同学的身影,再不久就会有这个消失同学的消息回头,然后大家八卦一阵便又消散不见。原来这个人不来上学了,去了某个酒店端盘子去了,在学业繁重的时候有时候这种消息着实会让人突然羡慕一番。
2005年还在高中的我在那个暑假第一次与酒店产生完全近距离接触,这次接触并不是去住在了某家酒店,而是我以暑假工的身份进入了小城的某家酒店当起了传菜生。此前有几次住酒店的经历,但对酒店的印象非常模糊,无非就是白色的床铺加个卫生间。而在那个暑假,我却要与酒店每天24小时接触,这是当时最大的感触之叹。
值得说明的是,那时候的小城酒店做的都是半年生意。每年最旺的季节从五一小长假开始再到十一长假之后结束。当地大多数的酒店选择在十一结束便关门歇业。这种现像犹如储备一夏的粮食而去冬眠的松鼠,夏季的繁忙与冬日街上不见一人的冷清显得如此滑稽。
那个夏季,我在酒店餐饮部每日因负责近二十多桌的上菜以及撤盘子以至于气恼不已。恼的是自己为什么要来受这个罪,却从来不思考如此大的酒店和待客量,老板为什么不舍得再招募一个传菜生。
我在后堂心里默骂着厨师:为何炒菜那么快,厨房四五个做菜的人,却仅有一个端盘子的传菜生,两条腿怎么可能跑的过来。那时候的客人大多是团队游客,吃饭方式也多是团餐。团餐的模式就是按人头计费,餐厅按客单价配几菜一汤,然后主食管够。团餐讲究的就是量大速度快,一波客人上来需要半小时内上齐所有的菜,半小时后再撤下所有的盘子碗筷,然后再收拾出来桌子继续准备迎接下一批客人...
当时一般的酒店客房可以卖到300元一晚,还是非常普通的酒店和房间。而我当时的薪水则是600元每月,几乎没有休息日。从来没有职场体验的我拼的就是那时候年轻,虽然每日工作14个小时,下班疲惫不堪,但睡一晚过后第二天精力就能得到完全恢复。那时候最大的快乐是躲在厨房偷吃花生米,当着厨师的面把大把的花生米塞进嘴里,直到胃里犯恶心才会停下咀嚼的嘴。
18岁的时候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最容易饿肚子的,但那个酒店刚开始员工餐里往往没有任何荤腥,因为这个问题以至于在一个月后,我被老板扫地出门。原因是在这家酒店的对面位置,有一个与这家酒店老板老死不相往来的竞争对手,这家准确的来说是个饭店,没有餐厅。因为地理位置相同,时常会抢起同一拨客人。
我有一个同样为暑假工的同学在那里上班,我们经常会在夜晚下班后聚在一起喝点啤酒吃花生米,喝的多了难免会吐槽一下员工餐吃的不好。这句话无意中被对方老板听到,成为对方老板吐槽我方老板的话柄。果然在不久之后这个话就通过一些方式传到我的老板耳朵里,以至于第二天老板气急败坏的对我说你泄露了我们的“机密”,这里“不能容你”。
就这样第一份“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世时间里就体验到了失业的滋味。我卷起铺盖蹲在马路边,假期中的学校宿舍肯定是回不去的,想想只能去投奔对面的同学,在他的宿舍将就了一晚。好在第三天就在2公里外的另一家酒店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从那时候起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是带着“愧疚”的心态,因为我“泄露”了老板的“机密”,以至于可能会给老板带来“损失”。后来我从曾经“同事”的嘴里了解到,这个老板对员工餐的吃饭标准是按照当月生意好坏来配的,起初还未到旅游旺季,客人不多,所以员工大多需要吃素。到旺季火热的时候,每天餐厅剩下的大量客人吃不完的荤腥是可以给员工补营养的。
这个老板虽然抠,但长得漂亮,貌似三十多岁的样子让18岁未尝人间烟火的我无数次在胡思乱想,我也很难想象在那个年纪为何会对大自己一轮的女人心怀想法,我甚至想象她对我如此严苛是不是对我的考验。但随着开学后,这些想法就烟消云散,思绪很快被繁重的作业所取代。在这些年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那里看看,如今或许她已经成为半老徐娘,但印象总存在于那个时期里,想想都觉得可笑。
酒店保安的工作相比端盘子就显得非常“清闲”了,这家酒店挂牌三星级,比之前那家稍微好一点,规模也大一点。酒店有180间客房,还有一个宴会厅和几个包厢。酒店大楼有八层,地下还有一层是司陪房。保安的职责就是守住停车场,每天将拉游客的各种车指挥按顺序停在停车场。酒店门前的空地就是停车场,因为没有围栏和大门,开放式的停车场需要晚上有人盯着,怕被人喝醉的人砸坏车玻璃或者偷东西。
晚上看车这项工作就成了做保安难熬的工作任务。那时候工作时间的安排是每人每上24小时班然后休息24小时。两班倒,每班两个人。这边的待遇和之前酒店传菜生是同样的薪资,但是员工餐要好一些。
想起当保安最大的乐趣是每天早上收停车费,第一次感受每天收钱的感觉。因为停车场没有栏杆没有计时收费的设备,整个场地全靠人守在出口,或者看到哪辆车要启动了马上跑过去把票递给司机。一辆车停一晚是十块钱,大车应该是十五元一辆。开放式的停车场总会有司机逃票,几乎每天都有司机强行开车走,对此我们也很无奈,对于这点酒店老板也是知晓的,但他似乎也不会在乎这点费用。
老板娘每天早上来到保安室收停车费,我们则按照车牌号登记表和票据合计每天收到的款项交给老板娘。在我们工作一两周后,保安室来了一个大学生暑假工,段位比我们高,毕竟人家是大学生,脑袋非常灵活,马上看出了赚钱的漏洞。他说:反正每天都有车“跑掉”,那么跑掉一辆还是三辆老板能知道吗?
在我们四人保安团里,除了我,还有俩人是职业保安,学历属于初中没毕业,但脑瓜子比我灵活,马上领悟到了大学生的“思想”。而我还在那一脸疑问:什么叫跑一辆还是三辆?难道我们每天要主动让三辆车跑掉?直到第二天,看了“大学生”的”操作“,我终于明白“跑掉”的意思。有句话叫做你不同流合污谁和你做朋友?
从第二天起,员工食堂再看不见我们吃饭的踪迹。早上交完账换完班,揣着两三张停车钱,就奔向早餐店。一碗豆腐脑一定要多放醋,再来两笼包子。晚上买上两瓶“夺命大乌苏”坐在酒店后面生活区的台阶上干喝。那时候突然觉得日子变的惬意起来,似乎认为这才是人追求的理想生活,第一次感觉到秋天开学是那么的可怕,厌学在那一霎间涌上心头,但很快就又被现实浇灭。
随着开学时间的临近,“大学生”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上交的停车费也越来越少。以至于某天老板娘看着交上来的十几张票,突然疑问:我看昨晚酒店都住满了,至少三十多辆车,怎么只收到十几辆的。不愧是大学生,马上掀开裤腿:‘老板娘你看,我腿上就是一个车强行开走蹭的,我被蹭完倒在一边,后面的车看到我这个保安倒下了一下子就跑了十几辆,等我缓过来已经来不及了’。这句话一出,老板娘立马指示经理过来给“大学生”放一天假去休息。
我和“初中生们”看的是惊立在现场,看着“大学生”瞬间将这个将死的局面瞬间扭转。
一个“初中生”拍着我肩膀说‘你一定要考上大学,不然连保安都干不好’。“初中生们”则暗自捶胸,恨自己当年没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从这天开始往后,接连十几天断续都有太多车“跑掉”的情况后,不常在保安室露面的老板估计也猜出了端倪,但苦于找不出证据,人家也不可能亲自去守停车场。这个老板见面给人一种大腹便便,其貌不扬的状态,我那时暗想,为啥老板都长这样?
找不到发泄口但是收拾你小员工还是有办法的。因为我们需要经常上夜班,自从“大学生”来了之后,我们是不可能一晚上安心睁着眼盯着停车场的。那么酒店大堂的沙发成了我们后半夜睡觉的卧室。在老家的小城,夏天夜晚温差还是较大的。因为白天很少有睡觉的习惯,晚上如果一直熬夜人再年轻也扛不住。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规则,我们就赶在后半夜睡上几个小时,早上在开早餐前赶紧起来将沙发恢复原样。我们每次将“起床”的这个时间定在凌晨六点钟,六点以后就陆续有人退房离开,而老板则习惯在七八点来到酒店。
在后来的几天里,老板就像故意提前到一样,我们后来才明白,他就是故意的,确实是专门抓我们的。当某一天六点前到的老板看到酒店大堂横七八卧的我们,马上叫醒值班经理做出指示,扣我们每人扣一百块钱工资。要知道那时候我们每月只有六百元薪水,一次扣掉一百还是非常心疼的。更要命的是一周被抓了两次,当月工资少了三分之一。这样导致我们后面不再敢睡觉,就算睡觉也要更加提前醒来。
那段时间我们似乎在和老板玩捉迷藏。当我们看到让再次提前来到的老板看到我们在保安室睁大眼睛盯着停车场时,一种胜利感油然而生。我们就像和老板斗气一样变本加利的继续吞下停车票。在开学的前日,我们去财务部领到不到三百块的月工资竟没有一丝不悦。我和“大学生”和“初中生”们告别后,各自转身离去回归到自己该去的地方。时至今日,当年的印象历历在目,时常会有一些愧色。
这段经历是我第一次和酒店近距离接触,而且周期如此之长,也是到今天为止唯一一次在酒店内工作的时光。或许也是此生唯一一段酒店生活工作的经历。我们感叹大自然的馈赠改变了很多面貌,也让我能有缘接触这个行业。
当时离开酒店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象过未来还能和酒店有什么瓜葛,顶多是希望在未来去往各地能住到自己喜欢的酒店里。而且我总会认为这段打工的经历也不值得回味,因为充满了不甘、嗜血、压榨和道德压力。
那时对于酒店的理解和认知就是看到那些来来去去慌慌张张的旅客。他们从各种大小旅游车上下来,急匆匆的奔向餐厅,大口朵颐着团餐,吃饱喝足后,又急匆匆而去。住店的客人也大都晚到,拿着旗子的各种导游一般先从车上下来,大声招呼着。这种画面在那个假期是百见不鲜,像极了我在小学时期,要入少先队了,老师举着队旗,让我们一一列队站好,接受训话。又或者犹如家养的宠物,我时常喜欢训练它,对它吆三喝四的,军训的科目都会用起来。
那时的旅行团没有分一定是老年团还是青年团,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毕竟在互联网时代初级,移动互联网还未普及的当时,独自出行自驾游这些还是时髦产物。
记得暑假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兴奋的当晚很晚才睡。第二天便花了二百元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手机品牌我记不住了,有彩信功能,可以打电话发短信。手机的到手的第一个月,第一次接触手机将爱不释手展现的淋漓尽致。拿出电话本给每个人打了电话,煲电话粥经常到晚上,躺在床上听到对方的声音竟然是如此的兴奋,全然不顾其实和打电话的人大多数的距离都不超过十公里,完全可以线下见面。
唯一让这个行为停下的是高昂的电话费账单,按照分钟计费的年代,怎么经得住熬夜煲电话。从第二个月开始,我不敢再主动打电话,接电话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因为发短信也是收费的,所以发短信的数量也变的节约起来。这个举动让我想起当时各种电视广告,400电话或者其他电话方式盛行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拿起手机,拨打了城中最大的一家酒店的热线,已经忘记说什么了,也许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家酒店旗下还有订机票的业务,他家号码就是400开头,后来才知道这家酒店不简单,以至于什么背景现在也已经遗忘了。
十一长假是这个小城最后的疯狂,当地酒店的价格突破了一年的最高峰。也许大自然的礼物总是让人向往,又或者要充分利用这来之不易的假期。所以在明知拥挤的假期,各地人群依然疯狂涌入这座不大的城市。所有的酒店睡满了人,所有的餐馆坐满了人,甚至晚上路边一些车里也睡着没有预订到酒店的人。那个暑假第一次知道了“旅游黄金周”这个词,也知晓了为何在这个季节里,会有平时数倍人流的旅客来到这里。
这些天里,这个小城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地方,各种神情心态的人都有:忙碌的员工,笑意遮不住脸的餐饮酒店老板们,还有那些小商小贩也因此都能沾上些光。而那些焦急等待客人的司机;那些找不到游客拿着旗子大声喊叫的导游;那些风尘仆仆在车上昏睡的旅客,那些看着高价的酒店和餐饮价格皱起眉头的消费客。但来的人似乎都不怎么吝啬,唯有碰到离谱的价格才会质疑,毕竟大家出来玩也不想以此破坏了心情。
宰客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一条河里的普通鱼经过包装渲染就变成了稀有物种,所谓的“高山冷水鱼”、“湖怪进化”而来等各种名目便成了各个餐厅不能说的公开秘密。总会有冤大头买单,只是碰到离谱的就会变成行政机关不得不出面干预的事件。本地人听了也会觉得有些诧异,对于这类失去信义的店本地人是绝对不会去的,因为这种印象已经深深的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只有不明所以的游客还会反复光临,但这种现象逐年减少,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商家也知道短利的危害,从而逐步学会从良。
在酒店泊车的那两个月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第一次知道了小费文化。因为保安一部分的职责是要帮助来客搬运行李,这里指的主要是团队的行李。一般客人下车后,会集中在大堂办理入住手续,而我们推着行李车将数十件的行李全部推到大堂,然后根据不同客人的房间送到楼层。
完成这项任务后,就等在门口等待领队或导游给小费,从一开始的欣喜到变成后来的理所应当,碰到不给小费的团队领队,有时候会在背后指点几句。等到“大学生”来到以后,碰到不给小费的车辆,他会主动跑到领队面前去要,时常惊得领队嗔怪不已。那时候经常能遇到港台客人,这波客人相对会比较大方,给小费是最主动的群体,偶尔能收获几张外币。
十一长假的结束也意味着一年的忙碌彻底结束,就像一场嘈杂热闹的盛宴结束,灯光熄灭,人员散场。人们看着满目破碎,回家先睡个几天几夜,回来再数口袋今年赚了多少钱。这里有高兴的,也有不甘的,不甘的是觉得钱来的太容易,早知道如此好赚应该将价格卖的再高一点,这样就可以赚的更多。但往往钱赚的太容易,就会出现一些德不压财的现像。冬季闲来无事的这群人开始大吃大喝,外出旅游挥霍,重复着夏天游客来这里的相同节目。甚至打牌赌博也成了常态。而我们提着行李,攥着手里屈指可数的几张票,回到学校继续过着更为忙碌的日子。
那个假期确实有些长,但却是打开了我对职业、对工作、对酒店、对旅游行业的启蒙。我经常在那时候思考,是不是大自然四季分明的安排让忙碌的人可以有半年的休息。夏季赚钱,冬季花,等钱快花完的时候,就又到了春暖花开开始迎接游客。这里除了酒店旅游业,当地还有一些主要产业是农牧业,农牧业也是半年农忙,半年闲忙。
春季播种秋季收获,这就预示着一年的结束。再来光临这块土地就得等到来年冰雪融化,春暖柳树发芽。小时候见的最多的还是哈萨克族牧民的赶场,那里的牧场分为冬牧场和夏牧场。春天和秋天就是赶场的时节。冰雪融化后,我们就看到路上、戈壁上、田野间成群结队的牛羊,后面跟着驮满生活物资的骆驼,牧民骑在马上拉着骆驼控制着整个群体。这些往往就是一个牧民家庭的全部,骆驼驮着的是房子(毡房),瓶瓶罐罐,自古以来逐水草而居的习惯依然在现代上演,这本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春季转场的低调相比,秋季的转场往往更为壮观。正如出征胜利凯旋回来的军队,膘肥马壮,牧民的口哨声不绝于耳。这就是自然给人世间形成的力量,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氛围和感觉。
我总是拿今天兴起的帐篷、露营、天幕等设备和当时赶场的牧民比。每每到周末,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我总会带上家人和装备,寻找一处宽阔青绿的草地搭上帐篷或者天幕,放置出躺椅,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各种饮料和小吃放在防潮毯或者折叠桌上,享受这一刻的祥和。看着公园草地搭满的帐篷,此时的脑海总会闪现那些牧民的迁移。那些骆驼背上的帐篷、干粮,还有席地而坐喝水的姿势,是不是都在预示着今天生活方式的演变本就是重重,只是目的变了,行为却没有多少变化,他们是一种生活,我们如此也是一种生活,只是生活的背后多了一层忙碌的影子。
在结束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假期,我第一次踏足家乡那个景区的时候,确实被风景震撼了。但与内地来的游客相比,我还是稍显沉静的,毕竟从小的生活环境还是稀释了一些对于本地美景的审美。而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基本都会忘记旅途上的疲劳和不愉快,虽然在这里享受了高价的普通服务,但看到如此震撼美景也就释怀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短视频功能的传播,人们信息来源基本还是靠电视、电脑和报纸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踏足新疆,或者第一次出到如此远的地方,难免有一些惊叹。约莫十几年后,我又一次去了这个景区,如今的商业化氛围越来越浓烈,各种酒店餐厅林立。景区门口的摆渡车络绎不绝,流水线式的景区观光流程,却让我对整个体验过程有了一些厌恶。
这些年走过了大大小小上百个景区,除了风景内容不同外,观光的模式和体验几乎出奇的一致。这背后是国内景区特殊体制形成的规则,越高等级的景区,基本都是国有属性,并且在当时完全属于行政管理方式在运行。拿家乡的这个5A级景区举例,景区管委会就是一个处级单位,和一个县的配置相同,除了没有户籍人口,其他公检法等机构部门齐全,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景区体制。
在我们这个小城进入到十一月,街上几乎就见不到外地车辆了。天气也逐渐冷了起来,随着天气逐渐变冷,雪也开始降下。那时期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冰雪游的概念,如今看来可是浪费了如此好的冰雪资源。
唯有我们自己在孩童时期视雪如宝,滑冰、滑雪、滑爬犁都是一种自发式的娱雪活动。然而上了中学之后视雪为毒物,它时常因为下的过量过厚而导致回家的路被雪阻断,大雪封路在我小时候是常见的事情,大雪过后往往夹杂着寒风,风吹雪会让任何路的痕迹都消失不见,人冒着风雪推着车走也是常态。
时至今日,距离曾经已经近二十年,我们逐步发现各地才开始发掘冰雪的价值。而我的家乡当地政府也开始在冰雪上下文章,从宣传到地方投入,逐步开发利用起这些优质的资源,企图延续夏季旅游的热潮,从而拉长整个旅游季节的收获期。尤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让冰雪游概念开始在全国普及。
犹如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开幕让国人掀起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冰雪旅游的普及让这个热潮传遍祖国各地,如今在我的家乡冰雪游建设已经凸显效果,喀纳斯和禾木景区现代滑雪场的开放以及马路除雪设备的逐步投用,让冬季冰雪游从概念成为现实。冬季游人的增加让大雪封路成为历史,虽然偶尔发生的雪崩和大雪封路事件都变成这里必然的点缀,但这些突发状况短时间内都能得到完全恢复。
如今冰雪的价值也在逐步放大,冰雪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稀缺性。中国有一半土地冬季是降雪的,但能形成天然滑雪的地方屈指可数。这些地区要么就是高山峻岭,人类无法征服,要么雪量小或者气温不均衡。而仅有的高优质的冰雪资源便成了这些地方不可忽略的财富,中国也仅有东北少数地方和新疆北部地方拥有这样天然的冰雪资源。
正如二十年的旅游是个轮回,夏季南方的游客趋之若鹜的来这里避世、避暑,观赏这惊世之景。而这里的人则在南方客人身上赚到了钱,在冬季的时候,南下避寒,南方的人再在这群人身上把钱赚回来。
如今,这种现象正在改变,一部分南方的客人在冬季开始奔赴一场冰雪之旅。无数游客冒着寒冷来到阿勒泰体验季节气候落差带来的感受。以至于这里的人们结束了冬季窝冬或者南下避寒的举动,进而在夏季旅游热潮之后留在当地,继续开门营业, 等待具有更大消费力的冬季客人们。此举让我突然想到就在前段时间回到家乡的时候,路过了很多戈壁上、山脚下整齐划一的新建民房。
友人告诉我这是牧民的安置点,他们不再依靠骆驼背着自己的家来回往返于各地寻找牧场,如今几乎全部实现了四季稳定居住。而我问:牛羊怎么办?友人回答:夏季依旧可以去夏牧场放牧,冬季可以回来圈养或者在就近的牧场放。但不用全家颠沛流离,一个家庭出去一两人就可,可以围绕家的周围来实现移动,这样就有了一个根。
我突然在想,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千年形成的习惯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而我望向天空中的鸟,依旧还在遵循着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它们的轨迹,南来北往的飞着,只是如今越来越难看到它们的身影。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只有数万人口的小城,却因有着天然美景的原因而热闹起来,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感受体验这场大自然馈赠的视觉美味。如果说把景区作为一个终点站,那么串联人到景区之间就形成了多种的产业链和职业。这里的产业链最重的则是酒店,成为承载人出行路上的载体和栖息地。
那时的酒店不是人出行的目的地,而是景区所需要的配套。酒店是旅程路上的一个点,一个休息站。是完成往返于景区观景路上必要休憩的地方,故而它因为此种功能而存在。这也是景区酒店的价值,也是当时这个周期内大部分酒店的价值,是观光游产业里最为重要的一环。除了酒店,旅游这个产业链还形成了像餐饮、旅行社、特产零售、旅游车、以及导游、讲解员、司机等这样的产业和职业。
想起导游这个职业,我思绪突然又回到在酒店做暑假工的日子,想起那些摇旗扯嗓吆喝的导游们,是不是和赶场的牧民相似。有区别的是这些牧民是骑在马上,手里拿着挥舞的鞭子,嘴里时不时呼喊着,鞭子在空中响起一声声清脆的犀利,远听有些动听,近听似乎有一些颤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