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编辑:nirvana
1853年春,太平军北伐,曾一度兵锋直指京畿,震动朝野。但这场声势浩大的远征,并没有停在北京城下,而是倒在了连镇——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地方。
连镇,只是河北景县与东光之间的一座边镇,横跨运河,平原之中不起眼的一点。
可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太平军在这里坚守了十个月,挖壕扎营,建木城、凿地道,与清军反复拉锯,最终全军覆没。
连镇之战,不是一次决定天下的大决战,却几乎耗尽了北伐军最后的气力与希望。
这场战斗,是怎样发生的?连镇为何成为太平军的归宿?援军为何未至?清军又是如何一点点围死这支疲惫孤军的?
今天就让我们仔细来说一说这一场太平军北伐的最为关键的一战——连镇血战。
壹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1851年,很快从广西一路北上,横扫南中国。
两年后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建立政权。
接下来的布局,洪秀全与杨秀清一边巩固江南,一边谋求北上,力图直捣北京,以图速战速决,一举倾覆清廷。
1853年夏,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奉命率两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挥师北上。
北伐军队从苏皖入豫,经山西,转河北,所到之处风驰电掣,官军节节败退,一度打到天津南,惊动咸丰帝,震慑京畿。
然而北伐虽猛,却是孤军。
粮草不继,援军不至,清廷反扑又狠。

尤其在直隶境内,水网遭清廷破坏而决堤,北伐军受阻于汪洋,无法进取,只能转守为退,绕道西撤。
天寒地冻、兵疲粮竭,局势由盛转衰。
1854年5月,突围阜城之后,林凤祥与李开芳率残部一路佯攻迷敌,最终选定运河北岸的连镇为据守之地。
为什么是连镇?这个不是偶然。

首先连镇这个地方地处直隶东南角,紧靠山东,水路通达,河上有桥,镇子分为东西两岸,隔河相望。
这对习惯水战的南方士兵而言,是天然的防线;而对依赖骑兵的清军来说,却处处掣肘。
更重要的是,连镇周边富庶,有粮有畜,可以撑得起一场长期对峙。
太平军动手很快,他们用征来的木料和船,连夜搭起浮桥,把东连镇和西连镇连起来,变成一个整体。
周围几个村庄也被占下,设了五个小营,像五把钉子钉在外面当警戒。
林凤祥守西镇,李开芳守东镇,两人分工明确,互通有无。
几天之内,这座小镇就被打造成一座坚固的前线堡垒。
清军追兵很快赶到。

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西凌阿、托明阿先后集结,采取分岸围攻的策略,意图合围太平军。
一场围与反围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第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5月15日。
清军东西两线夹攻,火力猛烈,鼓噪震天。
但太平军早已布防完备,火炮齐发,密集如雨,将清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大员伊勒东阿都被重伤。
首战告捷,太平军士气大振,乘胜夺取西岸数个村庄,将防线向外推进一步。
然而,战局从不止步于一场胜利。

5月19日,清将胜保率部赶到,与僧格林沁会合,兵力翻倍,对连镇形成三面合围。
到了5月25日,第二次总攻来势更猛。
这天的战场正逢风起沙扬,战场上烟尘弥漫,太平军拼死抵抗,再次击退敌军,守住阵地。
就在这时,援军的消息传来——天京派出的增援部队已至山东临清。
这是一线希望。
林凤祥与李开芳立即商议迎援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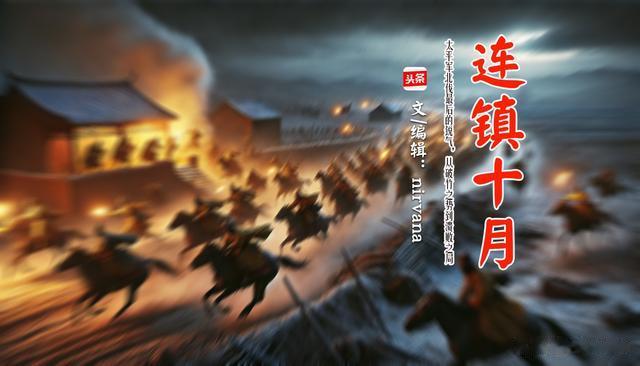
5月28日,李开芳亲率悍勇之卒千人、战马千匹,突围而出,东进临清。
他一路急行,穿过吴桥、德州,直逼鲁地,但途中得知噩耗:援军已被清军击溃,北伐支援彻底失败。
李开芳犹豫再三,不忍放弃连镇的兄弟,又无力独自返身,于是占据高唐州,妄图以攻代守,另寻破局。
但清军早已布控,胜保、德勒克色楞紧追不舍,高唐很快被围。
从这一刻起,北伐军被彻底分割,连镇与高唐互不联络,孤军奋战。
贰
我们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都知道,林凤祥是太平天国非常厉害的将领。
他从广西一路打到金陵,从天京又一路北上杀进直隶,打了无数恶仗,摔不倒,打不散。
他是实打实的太平军猛将,和李开芳、罗大纲并称“太平三虎”。
李秀成就说过他们,像他们这样的主将,战场上是能独当一面的,冲锋陷阵是一把好手,指挥调度也绝不含糊。
这一次,他扛起了全村最后的希望。
孙子兵法有云: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连镇这个地方,你看地图,完全是平原,但林凤祥愣是把这里变成了一座铜墙铁壁的堡垒。
他在镇里重新布防,砍树搭木栅,用土筑墙,把整座镇子围得严严实实。

墙外他还命人挖了深沟陷坑,甚至还打通了几条地道,从城中一直通到外面,白天他就固守,到晚上了,太平军还跑出来偷营,打得清军防不胜防。
清军根本没想到,一支孤军竟然能筑得出这样的阵地。
清朝官员姚宪之在《粤匪南北滋扰纪略》里说得很清楚:“城内粮食甚足,缘城复立木栅,悉用土壅,周挖沟陷坑,又挖地窟,贼皆潜居,并有地道直通城外。”
你看这描写,完全是一座地上地下配合得紧密有序的工事网络——太平军不是在等死,是准备死守待援。
僧格林沁越打越伤心,气得直跺脚,在奏折里亲口承认:“逆匪所占村镇,壁垒甚坚,我兵步队备尝艰辛……伤亡较多,以致临敌不免退缩。”
换句话说,他手下的兵都被打怕了。

尤其是他倚重的蒙古马队,冲锋凶是凶,可一进连镇外围陷坑、一道又一道的木栅栏就没辙了。
林凤祥把南方水乡的打法搬到北方平原,用机关和地势,生生让草原骑兵无法前进半步。
但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好歹僧格林沁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他想起了水淹七军的招数来了。
他飞信山东巡抚,请人从上游调水。

德州四女寺那边立刻开闸引河水,打算灌淹连镇。
为此清军甚至征集了数万民夫,修堤挖渠,硬生生想用水把连镇给“泡”掉。
但林凤祥没有被吓住。
他继续坚持主动出击的策略。
六月二十到二十一日,他派出马步兵偷袭清军骑队,清军死伤不少,巡捕营的常山也中枪身亡。虽然太平军这边也伤了两百多人,但战斗意志丝毫不减。
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清军副都统达洪阿率兵突袭太平军正在挖的新沟。
林凤祥反应极快,命令部队立刻反击,一场激战后,清军死伤三十余人,守备哈魁当场战死,达洪阿也被打成重伤,几天后吐血而亡。
从这点来看,林凤祥确实不愧是高手。而且他这人不上大话,也不搞虚招,但他对战机的判断极准,打起仗来又狠又稳。
他不是靠蛮劲,而是靠经验、胆识和决断力在撑。
清军吃了几次亏后,立刻又从北京调来了援军。

圆明园守军、固安防兵,加起来上千人,通通开往连镇增援僧格林沁。
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林凤祥还是继续采取固守+夜袭骚扰的战术继续折磨清军。
僧格林沁后来在奏折里承认:“连镇之贼负固死拒,两月以来,我兵屡次攻扑,百计诱引,奈该逆死守不出,我兵徒多伤亡。”
我们从军事角度看,这一阶段,林凤祥打得是极其精彩的。
他以一己之力,把僧格林沁、胜保、达洪阿三员清军大将拖在连镇,清廷连续调兵换将,耗费巨大兵力。
而这些兵如果不是困在连镇,原本都可以南下围攻天京。
所以说,林凤祥守连镇,不仅仅是为了求生,更是在尽最大努力,为太平天国全局赢时间、减压力。
叁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连镇里的天是越来越低,水是越来越高。
七月中旬开始,南边的陈庄和小村子都被淹了,战争的天平也开始悄然倾斜。。。
此时的林凤祥的人马只能泡着水、撑着筏子往连镇里退。
当然,他们不是没试图反攻,7月22日那天夜里,风雨交加,林凤祥带人划着筏子,摸黑突袭清军的庆洪营。
只是这时的清军已经摸准了太平军的战法,夜晚防守非常严密,一场激战下来,太平军损失惨重。
作为这次战役第一次出现转机,清军当然是把战果吹得天花乱坠,说“浮水漂出太平军尸首百余”,真假不好说,但这一仗确实是战役的一个转折点。
自此以后,林凤祥的军队渐渐不再出击了。
小股偷营也越来越谨慎。不是太平军不想打,而是打不起了。
每打一仗,都是一身伤、一堆死人,换不来补给,也换不来希望。
那时候,太平军剩下的大约还有六千人,里头还有一千个病号。
现在搞成了最可怕的不是敌军,而是肚子。

运河水一涨,东连镇也被淹了,米粮都泡了汤。士兵们从吃米饭变成啃黑豆,再后来,连黑豆都快吃完了,只能硬撑着嚼高粱壳。
到了九月,军中已经断粮,士气一落千丈,于是,有人想跑,也有人想投降。
这时候的林凤祥,还是没动。
他不是没看懂局势,而是还抱着一点点希望。
他记得李开芳走时说过,如果援军能回来,会放火弹为号。
这是他的一个执念。
然而,清军居然抓住了林凤祥的执念,原来,这段时间投降的人数增多,有知道内幕的投降太平军,为了邀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清军。
清军大喜,在十二月九日夜里,清军假扮太平军,学着样子点燃火弹,还派叛徒冒充援军跑来通风报信。
对于这跟救命稻草,林凤祥等了太久了,于是他没有多加思索便信了,派兵出迎,结果可想而知,出门就中了清军的埋伏,一通连环炮下来,太平军被炸得死伤一大片。

这一夜,可以说是林凤祥的心理崩口。他终于意识到——等不来了,援军是真的不会来了。
但他没有认输。他还是在苦撑,可是这时候的太平军,早已经是强弩之末。
清军越打越猛,林凤祥却再也拉不出一支能冲锋的队伍了。
连僧格林沁都看出来了,在奏折里说:“太平军已无前日之勇,虽困守巢穴,凶气大减。”
于是,针对太平军的“心理战”开始了:贴告示、开条件,“投降免死”、“有功赏戴”,诱降政策一路铺开。
一开始,林凤祥还严惩逃兵。
谁敢跑,被抓回来就是人头落地。
但到后来,他自己也撑不住了。他看到太多弟兄实在熬不过了,不是怕死,是饿疯了。
他也明白,再杀也没用,兵心早就散了。
他开始改口,拿出仅剩的银子发给那些还想逃的人,说:“你们走吧,别跟我一块死。”

他这一刀两断,既是放人一条生路,也是一种自责。
他不是一个昏聩的将领,他知道局势已尽。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倔强,才拖到这步田地。
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宁可拖着,也要拖垮敌人,给天京多撑几天。
但这回,现实没有眷顾他的信念。
到了来年一月,太平军已经开始大量投降,叛逃者超过千人,被清军编为“义勇”,反过来攻打昔日的袍泽兄弟。

2月8日,连镇的木城终于被焚毁。几天后,清军调集“义勇”和正规军,对东、西连镇发起总攻。
太平军奋力反抗,战得极苦。
在西连镇的肉搏战中,两军鏖战六小时,太平军的三座营垒相继被烧毁,防线岌岌可危。
偏偏这时候,军需官报来一封信——“圣粮馆报粮绝,无粮可发”。
那一刻,林凤祥终于明白,一切真的到头了。
他下令撤出西连镇,转守东连镇,把最后的兵马集中起来准备死战。他还在坚持,但这已经不是争胜负,而是挣最后一口气。
这是最后的阵地,也是最后的希望。
肆不过清军没有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很快,浮桥被拆,西连镇沿河的高地全被筑起炮台,一门门火炮咬牙切齿地盯着河对岸的东连镇。
水路被封,陆路有重兵压阵,连天都似乎收紧了包围圈。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清军放下了“收降”的脸面。
他们不再招安、不再许诺,只剩下屠刀和冷血。
先是将萧凤山、钟有年等91名投降者就地“正法”,接着又一批一批地杀光了六百多名叛降者。
那些曾投敌求生的,可耻,也可悲。他们绝大多数最终也没逃出“活着离开连镇”的命。
东连镇里,还剩不到两千人。
还好,这两千人都是硬骨头,没一个软的。
林凤祥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退。他也不装什么“等援军”的梦了,干脆把所有人都叫起来,重新筑城、修垒、备战——哪怕就是打一仗少一仗,也要打到底。
他们把木头一层一层地垒成“木城”,再用泥土堵实,打得很快,也很稳。
谁都清楚,这不是什么“堡垒”,而是他们准备为之殉身的一尺土、一口气。
林凤祥没有慌,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慌。
连僧格林沁都承认:“太平军虽已困守一隅,毫无生机,但他们战守从容,无有溃乱。”
太平军粮食没有了?那就先杀骡马,煮皮箱、刀鞘,熬马骨喝汤;再不行,就拔草根、刮榆树皮,挖野菜;清兵若有落单被擒的,甚至……会被“分食”。
这是人吃人的战争,是一群穷得只剩意志的战士,靠牙齿和信念死死咬住一寸阵地。

在2月25日的激战中,东连镇的太平军竟还能反手出击,打死打伤清军六七十人。
这不是一场战术意义上的胜利,而是他们在向敌人喊话:“我们还活着!”
但活着越来越难。
到了3月7日,僧格林沁把所有能调动的人马都拉来了:西凌阿、瑞麟、庆褀、绵洵、玉明……六路清军和一大批“义勇”围成一个死圈,炮声、火箭、火弹接连不断。
林凤祥他们没法突围,只能死守。
最后的城垒被火焚毁,木头烧成灰,血肉烧成灰。
连镇已经烧成一团人间炼狱。
最终的战斗维持了六个小时,太平军的人一批一批倒下,还有人投河而死,不愿被敌人砍倒。
清军攻入时,东连镇几乎已经没人站着了。
林凤祥还活着。也还在撑。
他本来想逃一次,甚至剃了长发准备突围。但两次负伤,让他连走路都做不到。

他和三十余名将士一起,退入一个早就挖好的地道。那是他们留给“最后一刻”的藏身之处。那地道蜿蜒数里,结构复杂、暗门遍布,不熟悉的人根本找不到。
清军血洗连镇三日,一直找不到他。直到叛徒施绍恒带人查到地洞,他们才在污泥里把林凤祥拖了出来。僧格林沁在奏折里写道:
“林逆藏身极深地穴之中,污泥黑暗,伤重,服毒未死,现已抬至大营医解,拟解京正法。”
这位在武昌冲破城墙、在南京第一登城的猛将,终究没死在战场上,而是被绑上了去北京的囚车。

林凤祥被凌迟照
他的结局,是被凌迟处死。但在北上路上,他没有一声求饶。
他死时31岁。
而连镇,连同那一批太平天国最骁勇的北伐将士,也随着这场浩劫一同归于尘土。
伍惨烈的连镇之战说完后,我们再用一个章节来说说另一名太平军北伐将领——李开芳。
1854年春,连镇被围不久,李开芳就看出了形势的凶险。
他带着手下仅剩的六百多骑兵,硬闯清军封锁线,往南突围,想赶去临清接应援军。
结果途中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

他只好暂时占据山东高唐州这座偏僻小城,就地防守,继续打旗帜上写着的四个字:北伐清廷。
到了高唐,他没有死守,而是主动出击。
夜里突袭,白天挖地道、翻墙打游击,几次打得清军大乱,还一度直接打到钦差胜保的大营后门,把胜保吓得几天不敢出门,连奏折都缩在帐里写。
李开芳人不多,却打得清军不敢硬碰,只能围困。
但局势越来越糟。
1855年正月,林凤祥在连镇被擒,援军无望,连镇失守,李开芳成了真正的孤军。
他知道拖下去就是等死,干脆决定突围南归,回天京去。

他选的突围点是个小村子——冯官屯。
清军早已设下重围,僧格林沁亲自领兵追堵,把他困在村里。
李开芳带兵在村中挖壕沟、修地道、设埋伏,还用鸟枪打狙击。清军靠近就中枪,伤亡惨重,不敢贸然进攻。
僧格林沁故技重施,改用水攻,调运河水灌进冯官屯。
大水一来,地道被淹、火药泡烂,粮食也发霉了,连埋好的地雷都被冲出来。
李开芳眼看局势不妙,决定设一计诈降突围。
他先派心腹黄近文带着一百多士兵假装成难民投降,在外边接应自己。
然后等到风大沙起、天昏地暗的一天,写了一封诈降信,让清军派小船来接他“投诚”。
但僧格林沁早就识破了这套,布下重兵埋伏。

李开芳一上岸,就被包围擒获,连同八十多个将士一起,被押往北京。
押送途中,李开芳绝食、不言,始终不肯低头。
到了北京,他接受了清廷审讯,留下了两份供词,说自己能劝南京太平军投降,还提到广西人一旦有人降,其他人也会跟着。
这些话真假难辨,可能是他真想求生,也可能是清廷编造出来做宣传的。
无论真相如何,清廷没有放过他。

1855年五月初五,北京菜市口,李开芳和七位将领被公开处决。传说,在行刑时,将领黄懿端突然飞起一脚,踢死两名刽子手,踢伤两人,场面一度大乱。李开芳昂首怒视,大喊:
“自出天京,所向无敌!清妖不堪一击,灭亡就在眼前!”
接着,是残酷的凌迟之刑。
他没喊一声、没流一滴泪,眼神冷峻,像块铁。血洒长街,英雄就义。
关于李开芳投降与否的争议李开芳是战死,还是投降?是力竭被擒,还是诈降未成?这一点,至今史料仍存争议。
一种较早、广泛流传的说法,见于清人姚宪之的《粤匪纪略》:李开芳在冯官屯突围失败后,主动派人投降,亲自带领88人缴械出营,被清军围捕之后,声称愿劝说金陵将领一同归降。
他被送往北京后,更留下了所谓“又供”,内容详述了自己如何可以策反太平天国将领、攻破南京的计划。
这一版本中,李开芳被描绘为在生死边缘选择了妥协,甚至出卖故旧,试图保命。
如果单从清廷档案、奏折看,这套叙述逻辑完整,语气严密,似乎证据确凿。
但问题在于,这一切是否可信?
另一种说法,出现在较多的民间记载、太平天国同情者笔下。比如《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耕余联谈》《冯官屯守备纪实》等记载了另一条路线:
李开芳原本打算诈降突围,先遣先锋混入清军布下内应,自己乘风沙掩护、带兵突围,结果计划被识破,全军被俘。
他本人在被解往北京途中拒食绝水,表现出强烈的求死意志。
更有传说,在刑场上他怒目高呼,部将黄懿端踢死刽子手,引发场面混乱,李开芳则以“昂首怒视,寸磔不屈”殉国。
两种记载孰真孰假,至今难以定论。
支持“诈降失败说”的学者主要把证据集中在三点:
第一、清廷有故意抹黑、夸大战果的习惯,李开芳“又供”内容过于“巧妙配合”清军需要,反倒像是加工过的宣传品。
第二、李开芳曾长期不食,被“抬着去京”,说明其求生意志极低,不像一个真心求降的人。
第三、在整个北伐过程中,李开芳战功显赫、性格刚烈,面对重兵围困仍多次突围作战,从性格和过往判断,不大可能临终时主动求降、投敌求荣。
但支持“投降说”的论者也认为:
“诈降失败”同样可能是太平军战后美化的说辞,为了保全英雄形象而故意弱化其求生之举。
供词内容复杂详尽,非仓促捏造者能拟,或许李开芳真的在被围绝境中做了求生选择,只是清廷最终还是没有饶他。
我们无法轻易判断哪个版本是绝对真实的。但可以确定的是——
李开芳的故事,走到最后,已经很难用“忠”或“叛”来简单评判。
他确实动过求生的念头,也确实在绝境中试图“诈降”突围;他说过“愿说南京伙党来降”那样的话,也许只是诱敌之计,也许是疲惫之中的一点动摇。
但他最终没有活下来。是他自己放弃了求生,还是敌人根本就不给他活路,这一点,至今也无从确证。
历史的记录总是零碎而模糊,尤其是对一个失败者来说,留在纸上的,往往是敌人笔下的版本。
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死时没有戴清军的顶戴,也没穿敌人的衣裳。
他没有变成清廷的一员,也没有领到功名利禄。
他是以一个太平军统帅的身份、一个失败者的姿态,走上刑场的。
或许他不是完人,或许他曾在绝望中犹疑过。
但他最后的结局,不属于背叛者,也不属于逃兵。他属于一位死在理想尽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