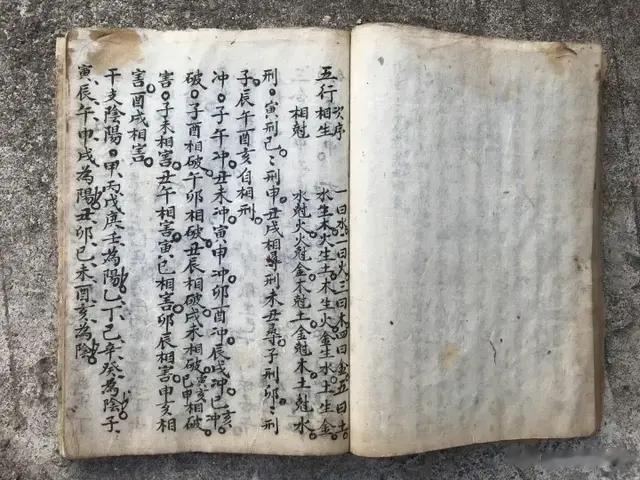随着黄维怒火的消失,整个房间内又静了下来,杨伯涛这才又小声的问:“覃军长,重刚是怎么回事,共产党审问他了?”
覃道善摇了摇头,以极低的声音说道:“不清楚,我们不是一路,我也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回事?这里只见到黄司令官、吴副司令官,没见到胡军长,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不过,我听第11师的散兵说,他们是用坦克车撞……”

覃道善没敢再说下去,杨伯涛的脸色,已经变白了,他能想象得到,第11师最后集中了第12兵团所有的战车,猛地冲向解放军阵地时的情景,更能想象得到解放军战士如何用血肉之躯,打国民党军战车的,把炸药捆在肉身之上,冲向坦克,抱着燃烧的芦苇、玉米秸秆,冲向坦克,甚至拿起简单的铁锹,击打着坦克车的装甲……在战车的横冲直撞之下,多少解放军战士被辗压得血肉模糊,他们这样对待指挥官王元直,是不为过的。
杨伯涛不愿意再问下去了,他抱起膀子,如同一只落败的斗鸡一样,缩上了脖子,内心里翻腾着,共产党,是不会饶恕自己这样的人的,自己的双手上,沾满了他们的鲜血,是要受到审判的,是要受到严厉的制裁的。他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吃下那把安眠药,自己为什么不朝着自己的额头开上一枪,自己为什么没有冻死在水中。
坐在杨伯涛身边的王岳,似乎也没有了刚才的热情,他嘴角动了动,自言自语地说:“劝降,劝降,他们派杨松青来,就是劝降来的。我们,当初不也是这样干的吗?”
谁也没有想到,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尹钟岳又呕吐起来,一下子把中午吃的东西,全给吐了出来,屋子里立即充满了一股辛酸恶臭之气,其他几个人,也忍不住吐了起来。
这个尹钟岳,是第18军的老人,年龄是数第一的,他是湖南洞口人,出生于浙江宁波,但他却不是黄埔出身。尹钟岳肄业于浙江武备学堂,在北伐之时,就加入了陈诚的部队。被俘时,任第18军118师师长。

就在众人的呕吐声里,大门被打开了,一股恶臭之气,令进来的人也跟着干呕了几声。
“我们抗议,你们口口声声说优待俘虏,就是这样优待的吗?满屋狼藉,也不收拾一下?”覃道善用手抹了一下嘴上的秽物,大声说道。
“卑鄙,卑鄙,给我们吃了什么东西?要毒死我们吗?要杀要剐,能不能来个痛快点的,搞这些下三滥的东西干什么?”尹钟岳捂着胸口,痛苦地叫嚣着。
“有本事,我们战场上见,真刀真枪地再干一场!”一直站在黄维身后的韦镇福同样高叫着。
又是那个解放军干部,大声命令着:“都给我住嘴!有什么事,一个一个说。”
梁岱极有经验地举起右手来,说道:“报告,同志,能不能先让他们到院子里坐坐,让我来收拾一下房间。”
“对,我要洗脸,我要洗衣服。”覃道善也早已站了起来,指着自己吐了一身的破旧军装。
“我,要求看医生,看医生,你们不是要实行人道主义吗?不是要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吗?我,病了,重病,是吃了你们提供的食物之后,中毒了。”尹钟岳一脸痛苦的样子,说话时,又猛烈地咳嗽了几声,吐出一口鲜血来。
一身“凛然正气”坐在会客厅正中的黄维,声音不大,却很“威严”地说道:“这,就是贵军的优待战俘政策?就是贵军口口声声所宣传的优良传统?就是你们要实施的罪恶的放毒计划吗?自我宣传,自我宣传。尊敬的干部同志,请问,你们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吗?脏!”
黄维的话,又立即引起了门口站着的几名干部和解放军战士的愤怒,一个战士大叫着:“闭上你罪恶的嘴巴,你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你才是最脏的人!”
另一个战士大叫着:“黄维,你才是放毒的罪魁祸首!人民会审判你的,就你这种人,活剥了你,都不亏!”
一个年龄稍大点的干部,也就是在门口管登记的那位,急忙把那个年轻的干部拉到了一旁,耳语了几句。杨伯涛心想,那个年轻的王干事,应当是比杨松青级别低,但却比其他人级别高的干部,杨松青走后,应该是他当家的。果然,那个年轻的王干事虽说还有一脸的不情愿,但还是喊叫着:“好了,你们几个,回到岗位上去。小牛,你们两个,带着尹钟岳,到野战医院去给他看病。小李,带他们排队出来,站到院子里,上厕所的,一个一个地来。梁岱、文文修,你们两个负责,打扫一下屋内的卫生。李干事,你到梁大娘那儿,借把刷子过来,让他们先清理一下衣服上的秽物。”
很快,他们便安静了下来,两个战士扶着尹钟岳出去了,杨伯涛想,肯定是到上午来时看见的那所简陋的医院去了。于是,看了众人一眼,便抬腿向院子里走去,身后,其他人陆续走了出来。

夕阳西下,染红了半边天,红彤彤的,透着亮色,把人的面孔照得发红。正襟危坐在院子里的黄维,抬起双手,轻轻地撸了一下稀疏的山羊胡须,叹了口气,说道:“要下大雪了,光亭兄,黄维无能,不能再为你们做些什么了,你们,一定要顶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