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朝碑铭的故事:为何会有一人两志?竟是王安石不满文豪曾巩大作而退稿
在中国古代,墓志铭一般都是在墓主死后,由死者家属支付一笔钱,在石碑上刻下纪念的文字,也就是俗称的“润笔费”。但是,也有一种很少见的情形,也就是一个人同时拥有两块碑文,那就是死者请求别人两次书写自己的碑文,为什么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宋朝的王安石了。

王益墓志铭的写作历程及矛盾。古代名人的墓志铭,一般也会请德高望重之人来写,曾巩是著名的大文豪,王安石之父王益的墓志铭,一直都认为是由他所著。王益病逝准备下葬时,他拜托曾巩替他写一篇碑文,以作纪念。曾巩也说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和安史是朋友,所以知道的最详细的事情。将死之时,派人带着安史的话和书信来求碑,于是碑成。”这一事实,原本是无可争议的,但两块碑文的发现,却使这一事实有了很大的逆转。王安石之父王益、兄弟王安仁二人之墓志书已被发掘。据考,王益的墓碑为孙侔所作,而不是曾巩所作。此处有个问题,曾巩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王益墓中所出的碑文的著者孙侔,目前尚不为人所知。事实上,孙侔的名气在北宋还是很大的,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更多地认可了孙侔的功绩。有一封给孙侔的信件,直截了当地对孙侔说明,其父墓志虽系曾巩所作,但有两个缺陷:一是所谓的“须至别作”,也就是一些细节不对。二是由于交流不畅而造成“事有缺略”。因为对曾巩所写的碑文不满,所以在他的书信中提到想要改一改。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因为对曾巩所写很是不满意,所以就让他的朋友孙侔再写一封,被孙侔拒绝之后,他就换了一个借口,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孙侔最终接受了他的请求,再写了一块碑文,免得他忘记了自己的父亲。

其实在王益的墓碑上,至于为什么会被他坚定地“退稿”,曾巩也说过,他是根据他的记叙文来创作的,那就需要仔细研究一下了。宋代文人在撰写高官墓志时,往往着重于其在仕宦生涯中的功绩、品性、品德等方面的表现,以记叙高官的身世为主要内容。虽然内容有缩写、句式和用词上的变化,但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在总体上保持统一的基础上,曾巩对王益先生墓志书《先大父述》作了一些增加、删除、修改,有可能引起了他的不满。首先是修改的内容,第一,王安石曾言:“临江为判官者,虽有违法乱纪,但在公事上,则以论理论之。”这是说和临江军主交战所取得的成果。至于是否如此,他并未提及。第二,是关于王益处理韶州牢狱纠纷的情况。曾巩着重指出:“少居于江南,虽然是个小州,但在监狱中,却是最大的难题。公因以其才干而多过,便以平定。"这一点他并没有提到。第三,对王益七子的名字进行了补充,并对他提出的丧事进行了说明。第四,添加了一位好朋友王安石的题记程序。这些话,都是曾巩自己写的,补充了一些。第四点说写碑铭的缘由,是一种通用的碑刻书写方式。其次是曾巩删省掉的五个重要的地方。一是漏掉了“任职数个月,无不惶恐,而有法度”一事,这是王益在建安郡守之位时,是对他治理才能的一种肯定。二是没有提及王益文与张咏的关系。三是对王益 “三十载,吏民称其为公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有所忽略,那是他在新淦县任职。四是对其所使用的“判官滩”一词的由来进行了探讨。五是忽略了王益在担任韶州总督期间,曾经将胡瑗所著的《政范》作为韶州的治所等一系列重大的成绩和影响。

曾巩所删去的部分,其一为王益与宋初著名官员张咏的交游之实,其二到五则为王安石在其父仕途上所作的记叙。曾巩在讲述王益的“忠义孝友”故事时,又对王安石所提资料进行了修改,体现了其创作思想。王安石所提供的资料主要集中在王益的“孝友”这一层面上,而关于“忠义”这一层面上的细节却没有太多的记载。曾巩将其生平经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家庭中的私人领域,二是在仕途中的公共领域,在官途上的公开领域,表现出了他的果敢果断,英勇不屈,而在处理私人领域的家庭问题时,则收敛内敛,委曲顺承,这就是他在各种环境下的表现。这个墓志铭逻辑清晰,表达的意思也比王安石提供的素材要详细得多,应该不会惹得王安石一家人的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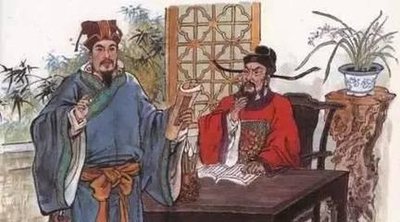
综上所述,曾巩在王益墓志的写作中,大体还是遵循了王安石《先大夫述》的有关内容。另外,还添加了一些家庭背景和官职,这一点,死者家属是不会质疑的。曾巩也对王安石所提供的材料进行了修改,并遗漏了更多关于王益在官场上的影响,而这可能就是王安石致孙侔的回函中所说的“事有缺略”和“须至别作”之处。而王益墓志的发掘,则为我们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提供了契机。

孙侔撰写的若干问题。王益墓中的碑文,因风蚀和破损,已不能完全解读,故而未能一睹真容,颇感遗憾。通过对已发表的文献和拓本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墓志的书写方法,是按照年代来记述的。墓碑的序言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王益一家人寻碑的经过进行了简单的回顾:“由侍郎寻碑,赐安国,安世,安礼,安祖,安祖,安葬于府南。”第二部分,首先对其官职和职务进行了概括,然后对他五次任职期间的成就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相比于曾巩对王益在官场上的影响进行了删除,孙侔则是根据王安石所说的写的,“州亦惮焉”,“县大奸臣,虽远,但政局清明”,“后悉听计从”,“小人能欺,政闻中州”,“少人思之,后必以公道治国”,“少人自有公道”,“王益在朝堂上的地位,自有权势”,这些都是关于王益在朝中的影响,一笔带过。第三,概括王益的优良品质,抒发其过早离世的悲恸。第四部分,介绍了王益的生平和结婚生子。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益墓志序和曾巩的碑铭最大的不同在于,王益在官场上的影响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这应该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事有缺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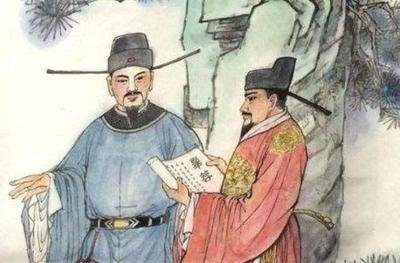
王安石在“须至别作”方面所重视的内容,可以从两个墓志中的铭文部分进行比较和剖析。墓志铭,由撰者本人提炼出来的,材料大多依据家属提供的材料。曾巩撰的王益墓上的碑铭主要是为了表示对王益的惋惜,也是为了突出王益的母亲,以及他的子嗣,都是优秀的,并没有提及他在官场上的功劳。孙侔为王益写的墓碑上写着:“死了!君子之年,谁不修行?人之将死,其所能及之一州也。德在其境,其所居之处,其所居也。君来日方长,神焉尔留。百姓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坟墓。”孙侔在题诗中,采用了适宜于表达感情的诗句,不仅为他的过早去世而感到惋惜,同时也赞扬了王益的优良品格,并赞扬了他的政事上的影响力。将这两个墓志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确认王安石所说的“须至别作”就是王益的墓志中的一段。在王安石的文中,他的父亲王益,尽管“死而无才”,但是他在仕途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值得称赞的,能够体现他的“为国为民”的志向。然而,曾巩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前言中忽略了王益在官场上的影响,而且在最后一句话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这让身为丧子的王安石很是不满。唯有了解了这一事实,我们才能明白王安石为什么放弃了曾巩的文章,而再次聘请孙侔来书写他的父碑。如果曾巩如此看重王益的墓碑,那么,他的这些志铭,到底是什么意思?纵观曾巩生前所著36方男子墓志,除王益外,其余诸人墓志铭无不是从墓主的才干、修养、品行、家世等各方面总结而出,无一不是如此。所以,王益之墓志,决非曾巩之“笔”所为。事实上,曾巩在写完王益的墓志后,还附上了一份《祭王都官文》,在这篇祭文中,至少要传达了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他从一开始就说到“他去了,忽而死了,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句话来看,王益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为官的才能;第二,从“对祖先公道,诚挚厚道”到“从其私心,委婉迂回”,在个人层面上概括了王益的“信”、“孝”、“亲”等卓越的个人特质;第三,从“钟山雄伟,只有一条大江”到最后,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自己语言上的匮乏,无法形容王益的卓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示对王益逝去的悲痛。这段话很有感情,也很符合墓志序文的意思。或许,因为曾巩所写的这段悼词,很有可能是采用了“互见”的方式,这也符合学者们对他“以自己的笔迹写墓志”的看法。但是,曾巩的这个相当认真的想法,最后竟被王安石以一种近乎“退稿”的形式抛弃,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墓主人死后,葬家人另聘他人为其题写墓志,这在宋朝,甚至在中国古史上都属少见。王益的“一人二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通常人们都以为,墓志碑铭是由丧葬家族委托别人写成的,他们除了向死者提供遗书等信息以及支付酬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参与的可能。其实,在作者写完之后,死者的家人会将作者留下的名字、埋葬的时间和地点等重要的资料都填满,并且进行仔细的检查,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会进行一些修正,直到满意。很少有人能确定,最后被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到底是不是作者自己的文字。因此,可以说,虽然亡者家属对刻石文本的书写的参与程度不尽相同,但是对最后的墓志文本的控制却始终是一种趋势。另外,与隋唐时期的情况相比较,宋朝时期的“一人二志”还有很大的不同。隋唐时期的“一人二志”都是碑文,都是被亡者家人承认的墓志,可以看出,在北宋时期,“一人二志”,前者是被抛弃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宋朝时期的“一人二志”,是撰者“退稿”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