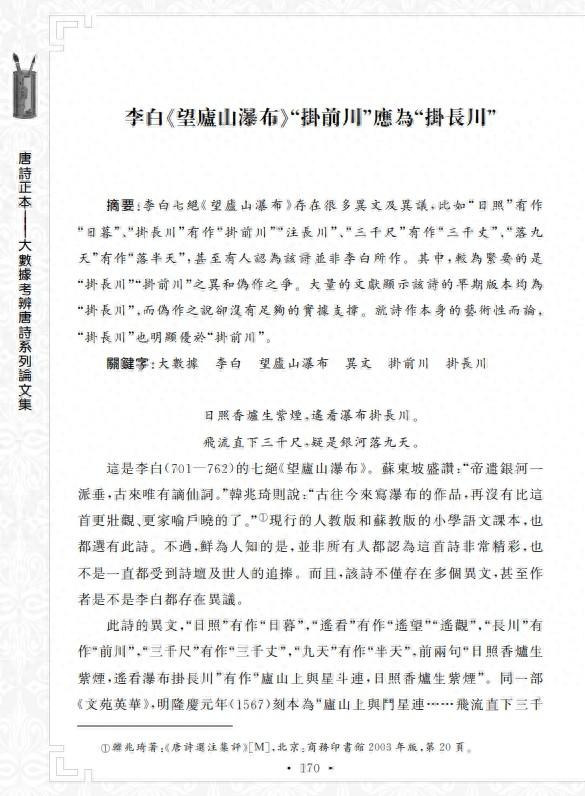
【按】本文載於拙著《唐詩正本——大數據考辨唐詩系列論文集》(澳門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引用或轉載請注明出處。
摘要:李白七絕《望廬山瀑布》存在很多異文及異議,比如“日照”有作“日暮”、“掛長川”有作“掛前川”“注長川”、“三千尺”有作“三千丈”、“落九天”有作“落半天”,甚至有人認為該詩並非李白所作。其中,較為緊要的是“掛長川”“掛前川”之異和偽作之爭。大量的文獻顯示該詩的早期版本均為“掛長川”,而偽作之說卻沒有足夠的實據支撐。就詩作本身的藝術性而論,“掛長川”也明顯優於“掛前川”。
關鍵字:大數據 李白 望廬山瀑布 異文 掛前川 掛長川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這是李白(701—762)的七絕《望廬山瀑布》。蘇東坡盛讚:“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韓兆琦則說:“古往今來寫瀑布的作品,再沒有比這首更壯觀、更家喻戶曉的了。”現行的人教版和蘇教版的小學語文課本,也都選有此詩。不過,鮮為人知的是,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首詩非常精彩,也不是一直都受到詩壇及世人的追捧。而且,該詩不僅存在多個異文,甚至作者是不是李白都存在異議。
此詩的異文,“日照”有作“日暮”,“遙看”有作“遙望”“遙觀”,“長川”有作“前川”,“三千尺”有作“三千丈”,“九天”有作“半天”,前兩句“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有作“廬山上與星斗連,日照香爐生紫煙”。同一部《文苑英華》,明隆慶元年(1567)刻本為“廬山上與斗星連……飛流直下三千丈……”,清文淵閣四庫寫本(下文簡稱“四庫本”)為“廬山上與星斗連……飛流直下三千尺……”。《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的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明修本、四部叢刊明刻本、四庫本和明萬曆年間刻本也有兩處不同。
本次考證,筆者共檢索到了載有七絕《望廬山瀑布》全詩的48種文獻的52個版本(有4種文獻為兩個版本)。以文獻成書時間劃分,宋代20種、明代13種、清代13種、民國1種、現代1種;以版本刊行時間劃分,宋代5個、明代17個、清代28個、民國1個,現代1個。
一、《望廬山瀑布》是不是偽作?
所謂“偽作”,指的是該詩非為李白所作,而是別人假託李白之名而寫的。在所有文獻中,《望廬山瀑布》均在李白的名下,但署名“李白”並非一定是李白的作品。《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搥碎黃鶴樓》和《贈懷素草書歌》就被疑為假託李白的偽作。不過,這種質疑早在數百年前就已出現,而《望廬山瀑布》被指偽作卻是近幾年的事情。
孫尚勇在《古典文學知識》2016年第6期發表了題為《七絕<望廬山瀑布>是李白作品嗎》的論文。該文認為,七絕《望廬山瀑布》可能“不是李白的作品,而是晚唐五代或宋初人根據李白的五言古體改寫的。”此所謂“五言古體”指的是李白另一首詩題同為《望廬山瀑布》的五言古體詩,因關係甚大,茲全錄如下——
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 欻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裡。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潈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還得洗塵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孫尚勇認為《望廬山瀑布》為偽作的理由有四:一,七絕《望廬山瀑布》因襲五古以及李白他作的地方過多。二,李白同時代的文人、唐人李詩抄本、現存各種唐人的唐詩選本和唐人詩文皆未曾提及七絕《望廬山瀑布》。三,七絕內容本身存疑,即“日照香爐”不可能“生紫煙”。四,七絕與五古的風格不相類。
不可否認,兩首《望廬山瀑布》的相似之處確實很多。“三千尺”與“三百丈”,“銀河”與“河漢”,“九天”與“雲天”,寫的都是香爐峰,而且還都是瀑布。在有的版本中,五古《望廬山瀑布》中的“初驚河漢落”為“初驚銀河落”,也就是說兩首詩中都有“銀河”。七絕最後三字若為“落半天”,又與五古的“半灑雲天裡”相似。出現這樣情況,確實不合常理。但李白生性不羈,不喜為矩所縛,他寫的格律詩也大都違拗,先後寫兩首類似的詩也不是沒有可能。
另有兩個因素:一,這兩首詩孰先孰後並無定論。在很多詩選中,這兩首詩共用一個詩題,五古在前,七絕在後,但這有可能是按照詩體的先後排列的,即“五古”早於“七絕”,並不意味著《望廬山瀑布》的五古一定早於七絕面世。如果僅憑相似度,既可以懷疑七絕因襲了五古,也可以懷疑五古因襲了七絕。張立華就認為,五古可能“抄襲”了七絕。況且,兩首《望廬山瀑布》排在一起的時候,也有七絕在前、五古在後的,比如《竹莊詩話》。二,兩首詩的異文都不少,而有些異文直接關係到相似度。比如“掛流三百丈”中的“三百丈”有作“三千丈”、“三千匹”的,“飛流直下三千尺”中的“三千尺”也有作“三千丈”的。如果是“三千尺”對“三千匹”,相似度就會大大降低,但通行的版本偏偏是互文的“三千尺”和“三百丈”,這或許是一種巧合。而通行本中的“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裡”,在唐人抄寫的敦煌殘卷中為“舟人莫敢窺,羽客遙相指”。如果敦煌寫本是正版,那麼“銀河”與“河漢”、“半天”與“半灑雲天”這兩處相似就不復存在。
孫尚勇的第二條理由也很難成立,因為符合這一條件的唐詩很多。流存至今的“唐人選唐詩”只有10種,包括敦煌殘卷在內,體量都很小,很多經典詩作都沒有出現或未被提及。比如李白的《靜夜思》,現在被認為是最為膾炙人口的唐詩之一,但最早也只是出現在宋代的文獻《李太白文集》和《樂府詩集》中。這些今人眼中的經典詩作之所以沒有入選唐代的典籍,除容量因素,可能也與時代的審美趣味有關。也就是說,唐人可能不太欣賞《靜夜思》《望廬山瀑布》等詩作。實際上,自宋以來,對《望廬山瀑布》的評價,一直都存在兩種聲音——蘇東坡(1037—1101)認為“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對李詩大加讚賞。而葛立方(?—1164)卻說“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為可喜也。”立方先生明知東坡激賞《望廬山瀑布》,卻還要發表不同的意見,可知他是多麼的“不敢苟同”。在葛之後,劉須溪(1232—1297)也認為“銀河猶未免俗”。而有這種感覺的人,也非止葛立方、劉須溪。從歷代詩選等典籍的收錄情況來看,不僅唐人不太認可《望廬山瀑布》,後世也有很多詩選家不太喜歡這首詩。檢索結果顯示,雖然《文苑英華》《萬首唐人絕句》《唐音統簽》《全唐詩》等很多詩選收錄了《望廬山瀑布》 ,但沒有收錄該詩的選集也很多,比如《千家詩》《古今詩刪》《唐詩選》《唐詩歸》《唐詩鏡》《唐詩別裁》《唐詩三百首》等等。出自《萬首唐人絕句》的《唐人萬首絕句選》,選了李白的七絕《望廬山五老峰》,也沒有收入七絕《望廬山瀑布》。只是到了現代,《望廬山瀑布》才成為各種唐詩選集的常客。關於兩首《望廬山瀑布》的優劣,意見也不一樣。蘇東坡顯然認為七絕好于五古,但胡仔(1110—1170)卻認為五古“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唐人典籍中沒有收錄或提及七絕《望廬山瀑布》,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審美取向,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詩歌品味,唐人不喜歡七絕《望廬山瀑布》,很多詩選家不選《靜夜思》等詩,都不難理解。但,唐人不選或未提七絕《望廬山瀑布》,不等於這首詩當時不存在——這是關鍵。
第三個理由:“日照香爐”會不會“生紫煙”?萬花飛濺,水霧蒸騰,陽光之下,光線折射,產生“彩虹”效應,這是非常正常也很常見的物理現象。但孫尚勇認為“彩虹”是“五顏六色”的,不可能生出“紫煙”。的確,彩虹有七種顏色,赤橙黃綠青藍紫,但這些顏色中最搶眼的卻是紫色,而且人們最願意看到的也是紫色,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紫”象徵著祥瑞。梁簡文帝詩曰“金風飄紫煙”,人們期待“紫氣東來”,是也。王禕(1322—1373)在《開先寺觀瀑布記》中稱:“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峰上,諸峰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人們眼中只有紫色、筆下只寫紫色,委實正常得很。不管日光下的紫靄是“斂”或“生”,都說明“紫煙升騰”這種狀態是存在的。再者,如何遣詞與詩作真偽也沒有直接的關係。
至於第四個理由,即七絕與五古風格不相類,就更不足以認定真偽了。孫尚勇認為,“五古略見稚拙,有欣喜的天仙之氣,末句‘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充分表達了作者出世游仙的願望,是李白早年作品不斷表露的思想。七絕則太過純熟,意指不明,看不出表達了什麼明確的感情。”的確,五古中的“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及敦煌殘卷中的“舟人莫敢窺,羽客遙相指”都帶有明顯的道家避世之意。此外,李白另一首以廬山瀑布為題材的七絕《望廬山五老峰》中的“吾將此地巢雲松”也是如此。而七絕《望廬山瀑布》中,卻沒有這樣的意旨。如果一味地講求思維的一貫性,這似乎是個問題。但若換個角度,比如追求新穎性或差異性,“不一樣”反而正好。試想:李白已經在兩首描寫廬山瀑布的詩作中表達了避世遊仙的思想,第三首還這麼寫,不膩嗎?面對“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壯觀場面,直抒自己所感受到的視覺震撼,也在情理之中。
總而言之,孫尚勇的四個理由都很牽強,斷言七絕《望廬山瀑布》為偽作的依據嚴重不足。
二、“日照”還是“日暮”?
在絕大多數版本中,七絕《望廬山瀑布》的前兩句均為“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但在《文苑英華》中,前兩句卻為“廬山上與星斗連,日照香爐生紫煙。”另有《李太白文集》《李翰林全集》《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等幾個版本把這樣的兩句作為異文處理。孫桂平撰文認為,這兩個版本均出自李白之手,“廬山上與星斗連,日照香爐生紫煙”為原作,“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為改稿,但只是推測,並無實據。“廬山上與星斗連”是夜晚之景,“日照香爐生紫煙”為白天之象,時空穿越如此之快之大,不是正常的觀感。若取“日照”,必舍“星斗”。

關於“日照”,既有異解,也有異文。一般的理解,“日照”的意思就是“日光照射”。但苗埒發表文章說:“去年遊廬山,才知日照原來也是峰名,這詩是寫暮色蒼茫中,遙遙相對的日照、香爐二峰峰頂仿佛如紫煙繚繞,這才更襯托出末二句的瀑布形象,注家注為日光照射,真是隔靴搔癢,‘不識廬山真面目’了。”此說令人耳目一新。但遍考古籍文獻,都沒有廬山存在“日照峰”的記載。雖然現在確有日照峰,但很可能是後人根據李白詩而命名的。以今之地理解古之詩文,謬矣。
胡仔(1110—1170)《苕溪漁隱叢話》:“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暮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胡仔這段筆記中的“日暮”二字,雖為僅見,卻不容忽視。

看到“日暮”二字,筆者首先想到了本詩在《文苑英華》中的第一句——“廬山上與星斗連”——這描寫的不就是“日暮”時分的景象嗎?
另請注意上文先後所引王禕和苗埒的文字。王禕在《開先寺觀瀑布記》中寫道:“日初出……”他所描寫的是“紅日東升”時的瀑布。而苗埒文中有這麼一句:“這詩是寫暮色蒼茫中……”他所描寫的是“日落西山”時的瀑布。前者是如實記述,後者是作者想像。為什麼要把李白描寫的情景設定在“暮色蒼茫”之中呢?苗埒沒有解釋。但遊覽經驗告訴我們,日出或日落前後是觀看瀑布的最佳時段,因為這個時段的光線最容易發生折射,也最容易產生如夢似幻的絢麗景象。王勃《滕王閣序》所謂“煙光凝而暮山紫”,也與“日暮香爐生紫煙”非常相似。所以,單就文本而論,“日暮”應該優於“日照”。
本次考證檢索到了《漁隱叢話》的4個版本,其中只有明嘉靖七年(1528)抄本為“日照”,明抄本(9行17字)、清乾隆五年至六年海鹽楊佑啟耘經樓依宋板重刊本、四庫本均為“日暮”。四庫常常按照通行的版本竄改文字,但此次卻選擇了不常見的“日暮”,值得注意。
在周凱(1779—1837)《廈門志》中,也有“日暮香爐生紫煙”之句,未知其來何自。在筆者檢索到的52個版本中,除《漁隱叢話》外,七絕《望廬山瀑布》的首句(《文苑英華》中為第二句)均為“日照香爐生紫煙”。所以,就版本來說,“日照”是無可撼動的。可能正是這個原因,魏慶之(1240年前後在世)《詩人玉屑》在轉錄《苕溪漁隱叢話》那段話時,把“日暮”改成了“日照”。竊以為,不加注釋地改動原作,並不可取。當然,原作是否為“日暮”,亦需進一步考證。
三、“前川”應為“長川”
“長川”和“前川”是七絕《望廬山瀑布》中最緊要的一處異文。在52個載有本詩的版本中,除《文苑英華》的兩個版本無此句外,“長川”為31處(包括“長川,一作前川”),“前川”為19處(包括“前川,一作長川”)。宋敏求(1019—1079)《李太白文集》,姚鉉(968—1020)《唐文粹》,祝穆(?—1255)《方輿勝覽》,陳舜俞(1026—1076)《廬山記》,不知撰者《錦繡萬花谷》,這5個宋本全部為“長川”。《山堂肆考》明刻本為“長川”,四庫本為“前川”,竄改的軌跡明顯。“長川”的版本不僅更多,而且較古。

古代書法家的墨蹟亦可作證,比如祝允明(1461—1527)和陳繼儒(1558—1639)書寫的《望廬山瀑布》中均為“長川”。
就版本而論,“長川”應為原版。那麼,從意境來看,“長川”和“前川”孰優孰劣呢?

我們先來看看現在通行的“前川”。古籍文獻中,選評者都沒有對“掛前川”作出具體的解釋。而現代的版本中,卻不乏詳細的注解。但令人吃驚的是,各種版本對“掛前川”的解釋五花八門。
“前川,是指瀑布下面形成的河流。瀑布水大勢猛,匯成的河流也奔騰澎湃,真是‘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這是《唐詩選析》的解釋。前半句說“川”是“瀑布下面形成的河流”,後半句又稱其為“掛流三百丈”,既然是“掛”著的,怎麼又在“下面”呢?前後自相矛盾,實在非常明顯。
“掛前川:瀑布下流成河,好像掛在前面河床的上空。”《新選唐詩三百首》的這個解釋與《唐詩選析》類似,除存在同樣的問題外,“河床”一詞也莫明其妙——毬卷雪迸的瀑布下面,必然是深潭激流,肯定見不到河床;面對驚心動魄的場面,觀者也不應該想到河床。據《大明一統名勝志·南康府志勝》載:“廬山之南,瀑布以十數,皆待積雨方見。惟開先之瀑不窮,掛流三四百丈,望之如懸索,水所注處,石悉成井,深不可測。”也就是說,此瀑的下面是激流沖鑿而成的井潭,而不是河流,亦非“河床”。
“前川:指香爐峰前的水流。”《古代山水詩一百首》也把“前川”解釋為山下的水流。瀑布之壯觀在於大量的山泉從高處傾瀉而下,變成水流之後還有什麼“壯觀”可言?即使是站在近前,觀瀑的視線也應該是自上而下集中於水流瀉落的過程; 若是從遠處“遙看”,更是如此。再者,瀑布下的水流當然是在山峰的前面,如此這般,“前川”之“前”豈不是個廢字?
《唐詩一百首》:“前川,山前的河面上。”《唐詩今譯》:“川是河流。掛前川,指瀑布掛在眼前,看去有如一條大川。”《絕句三百首》:“掛前川,從峰頂直掛到山前的水面。”這三條注釋中的“川”都是掛著的,這比前面的幾條靠譜。但“水面”給人以平靜的感覺,也不會是“毬卷雪迸”的樣子。關於“前”字,一個解釋為“眼前”,兩個解釋為“山前”,這三種解釋中的“前”都是無效的表達,因為瀑布當然是在“眼前”和“山前”之間,這是不言而喻的。
《唐詩鑒賞辭典》:“掛前川,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是一條巨大的白練高掛於山川之間。”《絕句三百首注譯》:“掛前川,瀑布從峰頂一瀉而下,好似巨幅白練懸掛在山前。”這兩種解釋都把瀑布比喻成“白練”。所謂“練”,本義為柔軟而潔白的絲織品。常見的“練”是長條狀的,但不會太長,也不會太寬。毛澤東詩曰“誰持彩練當空舞”,句中之“練”即為此意。兩種解釋在“白練”的前面分別加上了“巨大”和“巨幅”,顯然是想形容瀑布的宏偉壯觀,但“巨”與“練”存在內在的衝突。換句話說,“練”本身就是不會“巨”的,如果“巨”就不是“練”了。雖然香爐峰瀑布也不是很寬,《大明一統名勝志·南康府志勝》也是用“懸索”來比喻的,但如此寫實的詞語肯定不在喜歡誇張的太白辭典裡面。尤其不能忽略的是,詩的下句是“疑是銀河落九天”——試想一下:“白練”與“銀河”匹配嗎?徐凝詩曰“千古猶疑白練飛”,東坡譏之“不為徐凝洗惡詩”。“惡”從何來?“白練”就是一個既俗套又失准的詞語。
綜觀各種版本對“掛前川”的解釋,實在不是一個“亂”字所能了得。那麼,為什麼會如此混亂、甚至自相矛盾呢?這固然與釋者的視角及水準分不開,但恐怕也與片語本身的不合理有關。在筆者看來,句中的“前”不僅是無效之字,而且會擾亂讀者的理解。對於“百煉成字,千煉成句”的律絕詩來說,這樣的字是不應該出現的。但若是“掛長川”,上述問題就不復存在。
長川,長長的河流也。閆伯理(唐人,生卒年不詳)《黃鶴樓記》有“極長川之浩浩,見眾山之累累”之句。“遙看瀑布掛長川”,就是說遠遠望去,瀑布就像是掛著的長河一樣。這樣的意思很明顯,應該不會產生歧義。與無效的“前”字不同,“長”字強化了“川”的長度,而且為後兩句中的“三千尺”和“銀河”作了鋪墊。從“長川”到“三千尺”再到“銀河”,文字就像瀑布一樣順流直下,一氣如注。豪邁奔放、想像豐富、清新飄逸、意境奇崛——這才是“詩仙”的風格!這才像是太白的手筆!
52種版本中,“掛前川”最早出現於《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的兩個版本。其中四部叢刊明刻本的異文小注,“廬山上與星斗連”中的“與”誤為“舉”,明顯的“魯魚”之訛。但,“長”與“前”並不形似,不知此本是不是異變之源。
另外,《漁隱叢話》明抄本為“注長川”。此中的“注”字,顯然是“掛”的形訛。
四、“九天”還是“半天”?
本詩最後兩個字,52個版本中,48個版本為“九天”(其中5個版本為“九,一作半”),只有《唐詩品彙》《唐詩拾遺》《重選唐音大成》等3個版本為“半天”。《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的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明修本、四部叢刊明刻本、四庫本為“半天”,明萬曆年間刻本則為“九天”。同一版本的《廬山記》則是既有“九天”,也有“半天”。

“疑是銀河落九天”的意思是好像銀河從九天之外落了下來,“疑是銀河落半天”的意思是好像銀河從半天空落了下來,都能說得通。但太白喜歡誇張,涉及數量一般都是極言其大,比如“白髮三千丈”“天台四萬八千丈”等等,本詩也有“三千丈”或“三千尺”之說。依照這樣的語言風格及其“想落天外”的思維特徵,顯然應該是“九天”,而不是“半天”。傳說中天有九層,“九天”或“九霄”,都是指天的最外邊。屈原《九歌·少司命》:“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慧星。”毛澤東《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也有“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之句。
《廬山記》卷二摘錄了七絕《望廬山瀑布》的後兩句,卷四則收錄了全詩。卷二中的最後一句為“疑是銀河落半天”,卷四中的最後一句為“疑是銀河落九天”。或許,這就是“半天”和“九天”之亂的源頭。
五、另外幾處異文或異議
本詩第三句的最後三個字,52個版本中,《文苑英華》明刻本、《漁隱叢話》明嘉靖七年(1528)抄本、《記纂淵海》、《唐詩絕句類選》為“三千丈”,《李翰林全集》《唐詩紀》《唐詩所》則為“尺,一作丈。”其他版本則均為“三千尺”。筆者以為,“三千尺”和“三千丈”均非寫實,都有誇張的成分。雖然《大明一統名勝志·南康府志勝》稱此處瀑布“掛流三四百丈”,可能也是約摸的數字,抑或也是出自前人詩句。五古《望廬山瀑布》中的“三百丈”有作“三千匹”, 此中“匹”字倒是新穎別致。一來,“布”與“匹”很搭配; 二來,“匹”有“寬”的感覺,用來形容瀑布,既形象,又勢足。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古代組編選的《唐詩選注》,本詩第二句為“遙望瀑布掛前川”,句中的“望”字不知依據何本。筆者猜測,《唐詩選注》的編者換“看”為“望”可能與詩題《望廬山瀑布》中的“望”有關。雖然“望”與“看”同義,亦都可作平聲,也不能隨便改動。
說到詩題,也有多種。52個版本中,《望廬山瀑布水》有17個,早期版本多為此題;《望廬山瀑布》有16個,近期的版本多為此題。另外還有《望廬山香爐峰瀑布》《望廬山瀑布泉》《游廬山瀑布水》《觀廬山瀑布》《廬山瀑布》《望廬山》,《方輿勝覽》引用詩目錄中的題目為《開先瀑布》,還有一些文獻省略了詩題。這些題目,有繁簡之分,無實質之別。
“疑是銀河落九天”中的“疑”字之義,也有爭議。有人解為“懷疑”“疑心”,有人解為“好像”“似乎”。《靜夜思》“疑是地上霜”中的“疑”字,也存在這樣的爭議。筆者認為,這兩首詩中的“疑”字均應理解為“好像”,但“疑是銀河落九天”中的“疑”釋為“疑心”也未嘗不可。如何理解詩中的字句,原本就沒有標準答案。況且這兩種解釋,對詩意的影響不大。
王承丹認為,“遙看瀑布掛前川”之“川”應為“山”。他產生這樣的想法,就是源於各種文獻對“掛前川”解釋的混亂。他認為,之所以目前較為通行的釋義語義難通、於理不符,就是因為“山”訛為了“川”。該文列舉了三個方面的依據:(一)李白集中因字形相近而產生的混用現象比比皆是;(二)古籍中有“山”、“川”致誤的例子;(三)很多文獻證明香爐峰瀑布是掛在山前的。但上述理由的證明力都很弱,不足以立論。“掛前川”確有弊病,但錯不在“川”而在“前”。 文獻及版本大數據表明“掛前川”原本是“掛長川”。在七絕《望廬山瀑布》中,“長川”是一處彰顯太白卓絕想像力以及“詩仙”之氣的精彩之筆——它不僅擺脫了“白練”“懸索”之類的窠臼及平庸,而且為後兩句的“三千尺”及“銀河”作好了鋪墊。如果“長川”換成“前山”,全詩就大為減色。
六、作者之異
本詩的作者也存在不同的說法。
《陝西通志》之“鎮安縣”有載:“雲蓋寺,在縣西四十里營兒寨。相傳唐大中初,妙達禪師重請勅修前後九樓十八殿,僧舍以千計,潄玉招涼亭遺址猶存。有瀑布泉自懸崖瀉出,若飛練之狀。唐賈島詩:‘日照香爐生紫煙,遙觀白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明正統間,僧清潭、無礙師徒繼修,尚書劉璣撰碑。(縣誌)”
這段記載中的詩句與李白《望廬山瀑布》有兩字迥異,即“看瀑”為“觀白”,但這首詩的作者不是李白,而是賈島;描寫的瀑布不在廬山,而是在陝西鎮安縣雲蓋寺旁邊的懸崖上;所謂“香爐”不是廬山的香爐峰,而是雲蓋寺裡焚香的香爐。
這段記載出自鎮安縣誌。因為“孤證”,難以取信。不過,這倒是為李白非本詩作者的“偽作”之說提供了一個佐證。
七、結語
七絕《望廬山瀑布》雖然存在很多的異文和異議,但大都無關緊要,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個問題,即:該詩是不是偽作,“前川”與“長川”之異。前者是著作權問題,後者是詩本體問題。本文認為,李白寫兩首題材相同且高度相似的詩作確實不合常理,但斷定其中任何一首為偽作都缺乏有力的證據。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可以存疑,但不能輕率地下結論。而無論是從版本學角度,還是從藝術性來看,“前川”都應該讓位於“長川”。恢復原本的“長川”,不僅可以結束解釋違拗且混亂的局面,而且能讓這首經典詩作重新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韓兆琦著:《唐詩選注集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0頁。
[2]張立華撰:《詩仙李白為何‘抄襲’自己》[N],上海:《解放日報》2016年5月10日。
[3](宋)胡仔撰:《苕溪漁隱叢話》[O],四庫本,後集卷4第3頁。
[4](明)王禕撰:《王忠文公文集》[O],明嘉靖甲申年(1524)刻本,卷8第34頁。
[5]孫桂平撰:《李白<望廬山瀑布>(其二)異文問題思考》[J],廈門:《集美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2期。
[6]苗埒撰:《日照何能生紫煙》[J],《唐代文學》1982年第1期。
[7](清)周凱等纂:《廈門志》[O],清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卷9第68頁。
[8](宋)魏慶之編:《詩人玉屑》[O],朝鮮正統四年(1439)刊本,卷14第5頁。
[9]張燕瑾著:《唐詩選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頁。
[10]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新選唐詩三百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頁。
[11](明)曹學佺撰:《大明一統名勝志·南康府志勝》[O],明崇禎初刻本影印,卷4第6頁。
[12]金啟華、臧維熙編:《古代山水詩一百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 頁。
[13]社編:《唐詩一百首》[M],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1頁。
[14]徐放譯:《唐詩今譯》[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頁。
[15]葛傑、倉陽卿選注:《絕句三百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頁。
[16]馬茂元等:《唐詩鑒賞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第330頁。
[17]陳昊等注譯:《絕句三百首注譯》[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頁。
[18]王承丹撰:《“遙看瀑布掛前川”之“川”應為“山”》[J],廈門:《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