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梨白,一枚历史和写作萌新爱好者,欢迎关注哦,本文为原创,盗文必究!
书接上回!
这篇小文等于是《苏轼的朋友:有人是江湖寂寞人,有人是世间一知己》的第二篇。
上个周,咱们在说到苏轼朋友的时候,首先说了黄庭坚,是因为他和苏轼最好吗?不是,单纯就是梨白我很喜欢黄庭坚,哈哈哈哈。
上篇文章咱们也留下了谜题,谁是苏轼世间一知己呢?

很多小伙伴可能要说苏辙,因为苏轼真得是不止一次向弟弟苏辙“表白”,毫不遮掩对于弟弟的爱,这在普遍内敛含蓄的古代比较少见。
比如什么“我生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等等,都是苏轼对于弟弟苏辙的爱。

但是今天苏轼的这位世间一知己并不是苏辙,而是苏轼的一位忘年交、好朋友。上个周咱们提到黄庭坚和苏轼“神交”做笔友十多年才见面,足见苏轼的魅力,可今天这位更狠,他这一生可能也就和苏轼见了两次面,却成为了最懂彼此的人。
这人是谁呢?不卖关子了,他就是北宋官员、著名画家、诗人文同。
苏轼有一首诗词《於潜僧绿筠轩》,
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
这首诗苏轼借用竹子的高洁、风骨来比喻君子的气节和品德,表达了他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和赞美,竹子在古代文人中一直备受追捧。

这里歪个楼,这首诗有几个版本,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搜一下。
言归正传,小伙伴们可能不懂怎么说到文同又说起竹子了呢?因为文同非常热衷于描绘家乡四川的竹子,想要过苏辙在《墨竹赋》中与竹为伴,比邻而居的生活。
朝与竹乎为游,莫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
《墨竹赋》正是苏辙赞扬被文同画竹子的技艺高超的一篇赋文。
文同画竹子在整个北宋都是很有名的,有“竹痴”的称号,他的作品《墨竹图》现在在中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保藏,是清宫旧藏。

文同画竹子最大的特点是就是利用毛笔撇出竹叶,以浓淡墨区分竹叶子的正反面,“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再加上落笔时虚实结合,让竹子有了灵动之感,给人富有生命力的感觉。
苏轼的偶像白居易也喜欢竹子,并且对认为画竹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植物之中竹最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苏轼觉得文同的主子画的很好,不光画出了竹子的神韵,还画出了竹子的神态。
什么神态呢?竹君子的神态,苏轼的《墨君堂记》也是一篇评论文同竹子的文章,表示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如果文同不是端正无双,品性高洁的君子也不会将竹子身上的“君子”性描绘地淋漓尽致。

苏轼关于论述和与文同讨论竹子的文章又很多,除了对文同的人品,画技有所讨论外,还理智地论述了画家在画自然事物的时候怎么处理被画对象的“形”和“理”的问题。
苏轼认为一味赋予被画对象超脱本身和自然属性的意义是不可取的,还是要依托于被画对象本身,通过描绘对象的形,让见到画的人自然而然体会到描绘对象本身的气质。
这段确实有点拗口,简而言之就是不能脱离实际,不该通过不切实际或者夸张的手法来表达事物本身的气质,应该从画身上能感受到它在自然世界中的气质。
总之,苏轼觉得文同画的竹子就是这样,“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形理俱全。

关于文同的竹子,苏轼还真是“千求万求”过,因此也留下了不少“求画”的诗词和有趣场面。
《宋史》记载,对于自己画的竹子,文同没觉得多宝贵,但是求上门来讨画的人却是越来越多,还有人拿着丝绸来求画,气得文同将丝绸扔了出去,还言要把这些丝绸做成袜子踩在脚底下。
不愧是文同,要是真收了人家的丝绸,可能就画不出有“君”气质的竹子了。
最后,文同不厌其烦,就号召求画的人去找苏轼,“吾墨竹一拍,近在彭城”,还将此事告诉了苏轼,还诙谐地加了句,“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苏轼回信文同,表示给那些人画竹子也成,但是“当绢二百五十匹”,读到信的文同也是哭笑不得。
这事儿还真让两人之间互相“扯皮”良久,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这里咱们就不多说了。
别人求画,文同就笑着让他们去找苏轼,却不曾想苏轼也有“耍赖皮”找他要画的时候。
苏轼说,我在别人那里看到了阿兄的主子,但我只有一幅。我可以给你作记写赞,任你驱使,但你能不能多给我几张呢,我现在就派人去找你拿。

如果你敷衍我或者糊弄我,我就出去到处乱花,说你画的,然后拿着之前的约定去索赔二百五十匹绢。
不得不说,这里咱们的北宋国民男神苏轼都有一种小孩撒娇的意思了。
上篇文章我们一直看到的事黄庭坚对于苏轼的崇拜,在文同这里,苏轼成了文同的小迷弟。
事实也却是如此,苏轼一直以文同的从弟自居,但据考证两个人一个老家在眉山,一个老家在绵竹,没有啥亲戚关系,所以最有可能的是苏轼真的太喜欢文同,所以想要“攀”这层亲戚关系。
那么,文同除了人品过硬,竹子画得妙,还有什么地方是吸引苏轼的呢?
《再祭文与可文》(文同字与可)就记载了苏轼和文同的初次见面,这是苏轼在文同死后写的一篇祭文。
这里咱们就要说一下文同和苏轼的年龄了,严格意义上讲两个人并不是同一辈的人,文同要比苏轼大十八岁,比苏轼、苏辙的父亲只小九岁,在古代那是可以“生”出一个和苏轼年龄相当的人。
即便如此,两个人还是成为了忘年交,苏轼说第一次见文同就是一表人才,“广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
曾经有人考证过,两个人见面应该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元年,文同给父亲服丧完回京,图几个陕西。

彼时苏轼因为制科考试百年第一被安排在陕西的凤翔做官,两个人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见面了,文同四十七岁,苏轼二十九岁,虽然有年龄差,两个人却一见如故。
文同对于这次见面也有记录,说“子平一见初动心”。
看吧,文人表达其互相欣赏时也是不吝啬使用“大开大合”词语的,这么看文同和苏轼都是性情中人。
这里也说一下,“子平”就是苏轼,之所以用了这两字是因为变法派和保守派轮流执政,各有起伏,变法派占先锋的时候弄了个“元祐党籍”和“元祐党禁”,苏轼是其中被打击的灵魂人物,所以对苏轼的作品是有忌讳的。
彼时后人正在编纂文同的作品集《丹渊集》,就把“子瞻”改为了子平。

好了,我们再说回文同。
文同这个人很有人格魅力,我们看他的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文湖州。
不瞒大家说,光看见这个号梨白就已经“笑哈哈”了,文同一定是一个豁达、开朗的人,不然不会画出灵动的竹子,也不会被同样豁达、乐观的苏轼所喜欢、敬重。
学问已经是“百年”第一的苏轼对文同的诗、词、画、草书赞不绝口,称为“四绝”。这里也说一下,《宋史》还记载文同写得一手好飞白,笔画中丝丝露白,“文湖州”的号大家应该也能理解了吧。
《宋史》记载,文同是汉代文翁的后裔,所以四川当地人以“石室”称其家。

歪个楼“科普”文翁,名党,字仲翁,公学始祖,庐江舒人,西汉循吏。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
文同是宋仁宗皇祐元年的进士,和苏轼不同的是,文同一直在地方做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文翁的原因,王安石称其为“循吏”。
循吏就是关注民生,能做出政绩的好官、清官。
文彦博这个人之前咱们也写过,和欧阳修不太对付,两人同科,但是前者是那年的状元,官至宰相。

文彦博在成都做太守的时候,对文同觉得十分惊奇,还写信给他说,“与可兄襟怀坦荡,风韵洒落,有如晴云秋月,一尘不染”,宋朝文人之间的钦慕和交往就是这般神奇和简单,被某个人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就要告诉他。
不光是文彦博、王安石,就连一向古板的司马光也是非常敬重文同,所以苏轼成为文同的小弟一点不夸张,讲到这儿,梨白都想“看看”光风霁月的文同了。
上面咱们说了苏轼和文同的第一次见面,下面来说说第二次见面,这中间的许多年或者是两人交往的许多年,其实更多的就是靠着书信往来,“见字如面”。

苏轼的起伏人生梨白在这里不多加赘述了,咱们之前已经写过很多次了,他自己也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其实还有杭州、徐州、密州、湖州、黄州、惠州。。。
相比于苏轼的快人快语,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文同在政治上态度一向严谨,始终都保持着中立的态度。
这里的中立态度不是左右逢源,而是不卑不亢,就真的如竹君子一般。
但即便如此,自神宗变法后,宋朝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劣,在朝的大臣也因为变法而被分裂最后演变为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变法攻击彼此。

在这般环境之下,文同也不能幸免,因为宗室袭封的事情被褫夺官职,出京到陵州任职。
出京之前,文同和苏轼都是在京城的,文同也知道了苏轼要去杭州做通判。
大家都知道后来苏轼的乌台诗案就是因为和谁都称兄道弟,和谁都诗文往来,和谁都管不住嘴推心置腹。
如果是别人也就算了,他可是从欧阳修手中接过文坛大旗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对朝堂、政局,都是有影响的。

苏辙就曾告诫过兄长苏轼一定不能乱说话,就是说也要想想对方的意图,苏轼表示这个确实是自己的缺点,但说话就是嘴快于大脑。
文同其实也发现了苏轼这个问题,他将苏轼看作小弟,估计半个儿子也是能看的,也不止一次从中劝导、写诗词敲打他谨言慎行。
两人第二次在京城相处的时间里,只要是节假日文同就会邀约苏轼研究学问,写字作画,为的就是转移天真烂漫的苏轼的注意力,别让人出去“胡说八道”,也不要过多关注朝局。
文同在离京的时候再次叮嘱苏轼“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不得不说文同太了解苏轼了,对于乌台诗案的导火索《资治通鉴长编异文》中就曾经记载,《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巡察浙江的时候,去找苏轼讨诗,而讨的这些诗词就成为了之后苏轼贬低、妄言新法的证据。
当然这个说法待考证,之前咱们也写过,感兴趣的小伙伴到梨白首页搜索“沈括”,这几天梨白还会写一篇有关“沈括”的小文。
出了京城,两人相隔万里,文同依旧像一个护着小鸡崽苏轼的“老母鸡”不厌其烦地劝诫“小弟”不要出去乱说话,管住自己的嘴,比如“愿君见听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伤”。

苏轼估计看了就一笑,事后就忘光了,谁让男生天真烂漫呢。
文同在“教育”小弟,小弟却只想念大哥,什么“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往。一日不见,使人思之。”
这要不是知道是写给文同的,最后一句还以为是写给久去未归的情人的,关键是,这还是文同刚出京。
在熙宁八年的时候,苏轼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做官,修葺了一个台,起名“超然台”,写了一篇《超然台记》给文同,向大哥求诗。
第二年,文同回信了,写了一篇《超然台赋》,用词也是明亮、大胆,毫不吝啬地表达对苏轼的思念,就现在看来,有的词儿也挺“大胆”,我真的只能用大胆形容,比如“俯九州而下窥有一美人兮在东方,去日久兮不能忘。。。”

不得不说天真烂漫的“苏美人”也是魅力非凡,文同和苏轼之间还真是又来又来,一个“一日不见,使人思之”,一个“有一美人兮在东方,去日久兮不能忘”。
就在苏轼和文同第一次见面后,文同在京城应该也拜会了“同乡”的苏洵和苏辙,苏洵对这位四川同乡小老弟也是称赞不已,苏辙也有机会认识了文同,且将这对情谊升华。
熙宁十年的时候,文同的儿子和苏辙的长女议婚,对此苏轼觉得“极为喜庆”,是“喜事!喜事!”,更是在那之后和文同书信时开始跟着苏辙称呼文同“亲家翁”。
苏轼人没到,却把儿子苏迈调配到了南京听从叔父安排,为两家的亲事驱使。

《宋史》记载,宋神宗元丰二年,文同赴任湖州,他到陈州宛丘驿,忽然留住不走了,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停止了呼吸。
临死之前,文同还是想要见苏轼一面的,但彼时苏轼在徐州,且宋朝的官员任职期内是不能随意离开的。
苏轼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三天三夜没有睡着,只是默默地做到天亮,巧合地是,结束徐州任期后,苏轼知湖州。
后来在湖州曝书会上见到文同生前画的竹子时,苏轼悲痛不已,泣不成声,直言感受了曹操曾经得知桥玄死讯时的“车过腹痛”之痛,由此我们也能感受到苏轼对于文同的深厚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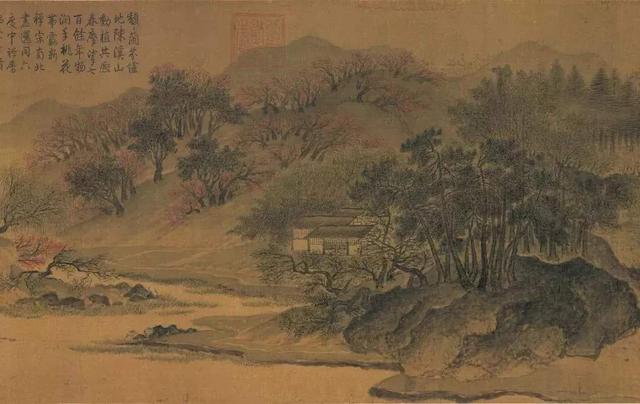
文同死后,家贫,无力发丧,苏轼致信舒州的李常,希望其能出手帮助,这里的李常应该就是黄庭坚的舅舅。
之后苏轼在湖州乌台诗案发,在被贬去黄州的路上,和弟弟苏辙在陈州相聚,帮忙料理文同的丧事,看到文同留下的书法时有时一阵悲痛。
苏轼在离开陈州要去黄州时还留下了“君已思归梦巴峡”,有对好友的怀念,也有对渺茫前途的迷惘。

在这之后,苏轼又写了很多思念文同的诗词,不知道在起起伏伏,“伏”大于“起”的人生中,苏轼有没有一天突然想到文同对他的劝诫。
不过那都不重要,斯人已逝。。。。。。
(文中所有图片来自网络,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万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