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8年春天,汉中盆地的冰雪,尚未消融。蜀军却已燃起北伐的烽烟。五丈原上,诸葛亮望着,蜿蜒北上的军伍,手中羽扇,不自觉地收紧。——这支,承载着先帝遗志的军队,即将面对,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

街亭的黄土坡之上,参军马谡手持宝剑伫立在那里。这位得到丞相亲自传授“依山扎营”这一密令的年轻将领,此刻正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远方,以及那正在升腾而起的烟尘。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将两万精锐部队带上南山,并且坚信“居高临下,必定能够破敌”,不过他却完全没有顾及到王平苦苦劝诫的水源之要害所在。当张郃的铁骑截断汲水通道的时候,蜀军喉咙之中,那如同火烧一般的焦渴之感,比魏军的箭雨更加让人感到绝望。

不过翻开《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袁子》所记载的细节,着实令人心惊。诸葛亮在汉中“蓄力八年”筹备的粮草,竟在第一次北伐之时,便已呈现出捉襟见肘之态。祁山道上的运粮队,需穿越三百里险峻栈道,而且每十石粮食运抵前线,民夫就要吃掉八石。当赵云在箕谷佯攻的偏师,因断粮而溃退时,整个蜀汉的后勤系统,其实早已千疮百孔。

陈寿笔锋如刀:"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退欲跨陵边疆。"可当四十六岁的诸葛亮含泪处决马谡时,他或许比谁都清楚,这场溃败不仅是军事失误的苦果汉中军械库的竹简记载着残酷现实:北伐前打造的三千张弩机,因巴蜀冶铁技术落后,有近半弩臂存在裂纹当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时,诸葛亮拒绝的真正顾虑,或许正是这支军队经不起任何意外消耗。

细雨迷蒙之下,位于成都武担山下的地方,督粮官李严正跪在丞相府的门前请求治罪。这位曾经与诸葛亮一同接受托孤重任的大臣,此刻因为暴雨将粮道冲毁,心中惶恐,不敢直接面对那可能到来的质问。蜀汉政权内部原本就存在的派系裂痕,随着北伐所面临的压力逐渐显露出来;益州本土的士族对待粮草征调这件事持消极态度,而荆州集团的将领又接连遭受损失。当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下“民穷兵疲”这几个字的时候,北伐大业竟然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历史的长河慢慢把真相那清晰的轮廓给冲淡了。不过等我们再次回顾这场对三国局势有着深远影响的战役时,或许得好好反思一下:要是汉中地区的粮仓储备很充足,马谡还会不会坚决地在山坡上扎营呢?要是蜀道的运输一直都很通畅,诸葛亮是不是就能毫无顾忌地全力实施他的战略计划呢?在街亭的山坡上,那支部队因为缺水最后都渴死了,这就成了压垮蜀汉国力的最后一根很容易断的稻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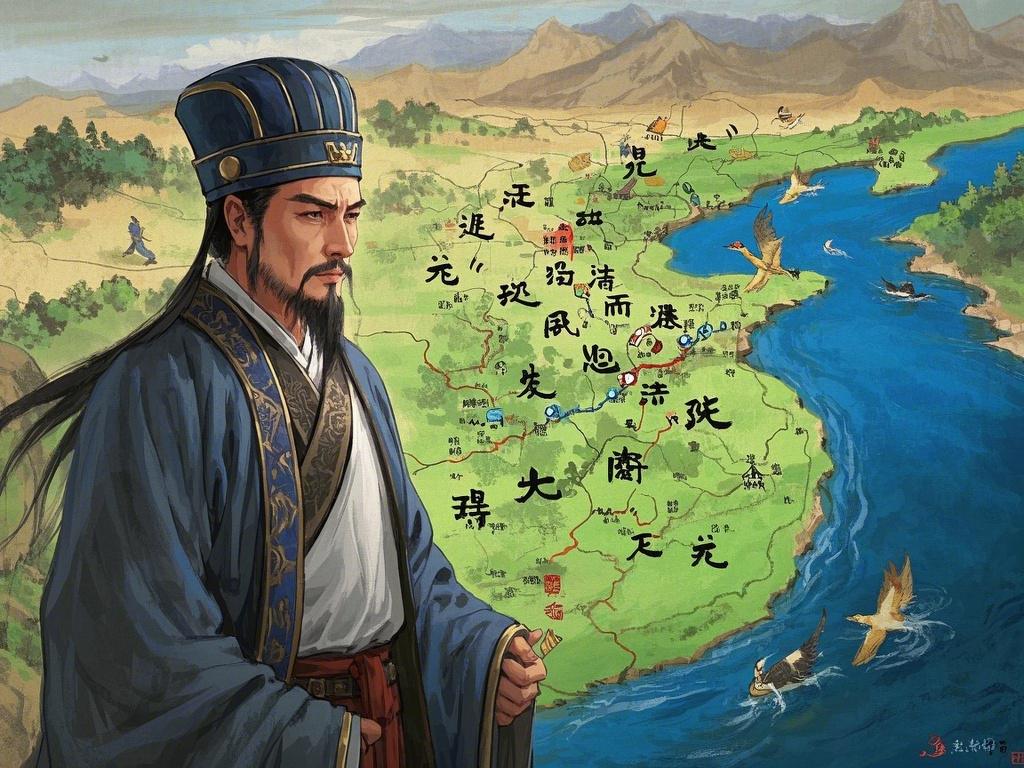
站在定军山武侯墓前,在松涛声里,似乎依旧回荡着《隆中对》那激昂的气息。读者诸君不妨好好思量一番:倘若您把控着蜀汉,到底是要一直持续地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去进行北伐,以此来报答先帝呢,还是暂时停下脚步,让百姓休养生息,静静地等待天时的降临呢?历史虽没有假设之事,但每一个抉择都值得后人深深地去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