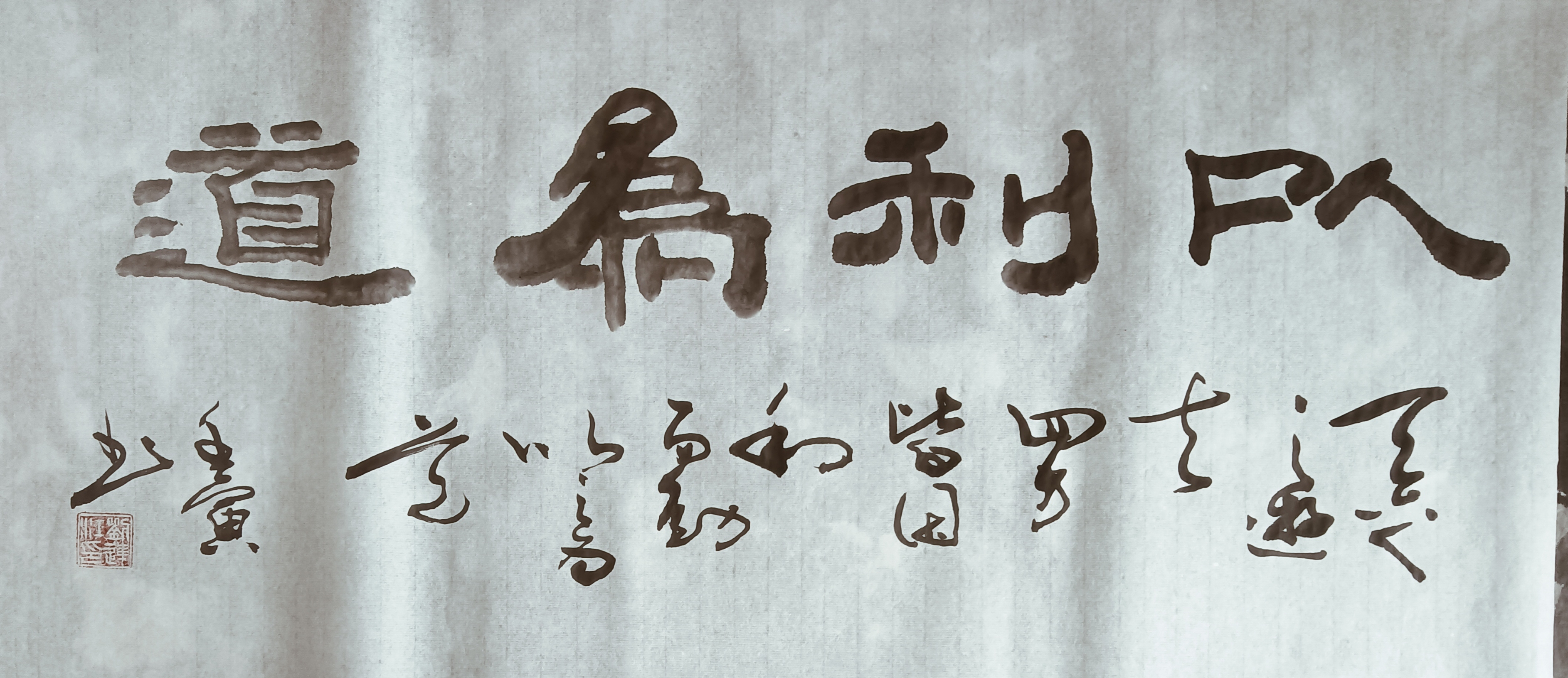
地球史中所有生命无不以努力保证生存延续要素的要求和更多的要求为主旨;无不以生活资源的占有和更多地占有为目的。生命进化史中所有生活习惯的改善、生存方式的改变、甚至生理基因的突变,无不因利而动,利益之道,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学,经济发展无不引导着生命领域所有之嬗变,或者说生命无不因经济环境变化而变化。
习俗包括家庭和社会时尚,不论是因地还是因时而易,都是一种表象,其实质都是经济环境的量变而致。比如对应到当下社会我们耳熟能详的啃老特色的家庭,其之所以产生并且如此广泛普遍的存在,映射的还是因为纯粹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当下社会压力下太过脆弱和弱不禁风,才演变出来的“六个钱包”供养“小夫妻”打拼天下的事实。这与所谓的“80后”“90后”的个人道德修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啃老是表象,之所以啃老是因为残酷的经济压力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经济环境决定经济行为,经济行为决定消费模式,消费模式决定着社会时尚。人类历史中被动构筑的所有社会组织都是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其中固然有此间乐不思蜀的卫道派的作为,更有人性禁锢的事实,你比如说“禁人欲,存天理”的家族理学社会“几家欢乐几家愁”,其中人性压抑的受害者不论是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大于“特权嗜欲”享乐派的。并不是作者空口无凭的信口开河,这是特权机制中特有的现象,就像沪深股市中赚赔钱效应一样的必然,万马千军的散户们大多都是开着夏利车进场,最后拄着拐蹒跚而出。脑满肠肥的庄家却赚的盆满钵满。这与智商无关,因为资源占有不可同日而语,那就是起跑线不一样,既然起跑线都不一样,那乌龟赛跑能胜过兔子也就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
20世纪意大利著名法学家马尔蒂诺曾针对对古罗马埃特鲁斯时代之变革论述了他的如下观点:“习俗”实际是公元前10世纪罗马在埃特鲁斯时代所引进的最现代和文明的习惯,这些“习俗”被引用的目的就在于有效限制家长权一任己意的残暴运作,而这些移风易俗的变革能通过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时尚流行,并且最终得到监察官的认可。罗马远古家庭源自父系团体,最初是建立在畜牧业和粗放耕作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之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罗马可耕地的扩大和开始向更发达的集约型农业经济的转变,父系团体这一古老野蛮的生活生产方式开始瓦解,并从中不断分离出具有同样主权性质的自主性组织,即自有法(习俗)家庭。可见不论是群婚制的原始部落,还是自有法家庭---应该是是家族,类似于大宅门里的家族,巴金笔下的家。-----当然也包括现代文明意义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和这种家庭与时俱进的衍生、嬗变和推陈出新的未来的新时尚家庭,都无非是个体经济条件改变的被动应变而已。换言之,你有什么样的个人属性范畴之内的经济能力,就有着怎样的社会组织。
我们中学时代政治经济学启蒙的第一课,应该就是所谓的“社会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以我们自身的社会阅历去验证它不成立的谬误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社会底层或社会运行被动者而言,它无疑是正确的。公元前10世纪以来,随着埃特鲁斯时代的推动,亚平宁北部社会不论是可耕地供给规模和参与生产的人员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限制父系团体特权的独断专行,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嬗变,就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了。它与感性的道德评判无关紧要,与激情燃烧的国恨家仇情绪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有者利益再分配才是一剑封喉的命脉所在。要做大蛋糕的首要之义,不是组织生产蛋糕的社会资源,而是在可预期的未来时间段里,如何分配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