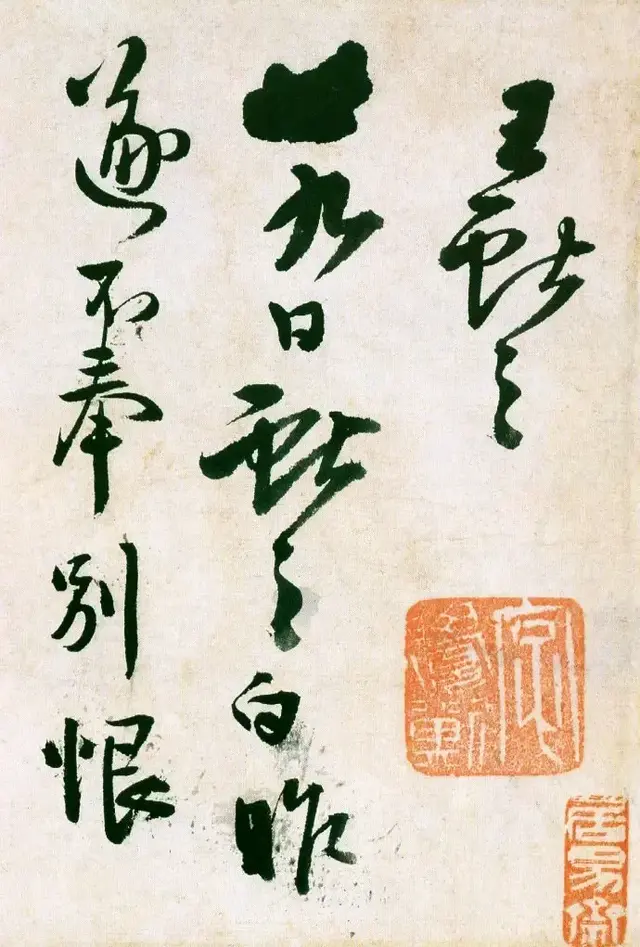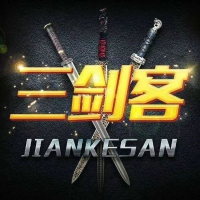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若有侵权请联系修改或删除。

前些日,第一次走进狮泉河烈日陵园,来到孔繁森同志的墓碑前,这位我很小就常听长辈提起的人物,如今跨越时空面对,许多关于记忆中的西藏泉水般涌上心头。久久无法平静......
我的父母长年在日喀则地区工作,父亲在部队,后来母亲也从老家随调到了西藏,我则留在老家跟着外婆外公生活,成为了一名留守儿童。
自打两岁起,每年放暑假时我都会来到父母身边,多数是在其他叔辈的帮助下进藏,也有一次是走的无人陪伴儿童通道。
在我童年记忆中,九十年代的日喀则城市建设较内地是比较原始落后的,整个市区仅有一条主干道是水泥铺装的路面,大街上汽车更是少之又少,偶有车辆经过时顺带激起的漫天黄沙总会迷得人睁不开眼睛。内地与西藏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遇到冬季大雪封山导致信件滞留,就只能卡着字数发电报报平安,迫不得已的长途电话还要去邮电局排队等候。
在我出生那年,正好遇到接连的暴雪,父亲说他所在点位唯一通往外界的道路积雪堆积成雪墙比车顶还要高,等他休假回来时,我早已经满月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这里的天蓝得像染过的一样,河水清澈随时能见到畅游的鱼群,山很高帽子都要望掉,云很低仿佛踮踮脚触手可摸,每次雨过天晴后去林卡里采蘑菇,总能给人意外惊喜,院子后面那片青稞地,采新鲜青稞放在嘴里嚼起来也总是那么甘甜咧人......
这些景象在内地无法感受,而在孩童眼中,就是游乐的天堂。
那时候地区各县乡间几乎没有路,大多都是牛车马车压出来的车行道,砂石地、搓板路、稀泥潭......还有积满碎石的河道,下雨天常常伴有泥石流的危险,陷车、推车、拖车都是家常便饭。
父亲经常会乘着那辆上了年纪的老北京吉普下乡,每次出门前驾驶员都要站在发动机舱前鼓足力气、瞪大眼睛、抡圆膀子,呼呲嘿呲用摇把摇上半天,直到发动机传来“哐哐哐”的声音才能启动,行驶途中父亲也常打趣的说,除了喇叭不响、哪里都在响。
周边县乡大多在人迹罕至、海拔又高的地方,而那时的我真是“又菜又爱玩”,总想跟着父亲去见见世面,但结果却是走一路、晕一路、吐一路,到头来只记得翻江倒海的胃和天旋地转的我,却仍不忘嘴硬的说着“我还要来”,回头想想实在可怜又可笑。
有一次,从岗巴回程的路上,汽车陷在帕里草原的泥潭里动弹不得,在牧民和牦牛的帮助下又推又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脱困,而那会儿我却因为高原反应只能无精打采蹲在一旁,救援成功后藏族同胞那憨厚质朴的笑容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只是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到过更加艰苦的仲巴、吉隆和萨迦,总归是有点遗憾的......

但酥油茶香的糌粑、酸甜可口的奶渣、扎什伦布寺后山回荡着“嘛呢嘛呢叭咪吽”的转经路、乃堆拉山口漫山遍野的红景天、谢通门途中深夜突发漫过车门的泥石流、南木林远看成树近看林的行道树,还有仁布附近百丈悬崖的峡谷和汹涌湍急的雅鲁藏布江等等,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难以抹却的回忆。
当地人总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八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来形容这里的艰苦。一进入高原的雨季,父亲经常和战友们一起数个昼夜连轴转扑在一线抗洪抢险,甚至有一次刚回到宿舍连口热饭都没顾上吃又得奔赴下一个战场。
在那个条件极其有限的年代,我也在耳濡目染下见证了许多守边、救灾的英雄故事,他们中有的昨天还抱过嘤嘤学语的我,转瞬之间就永远长眠在了雪域高原。
在许多人眼中,西藏可能是一个符号,也可能是一个神秘而向往的地方,但我心里早已当作了“第二故乡”。有一次进藏时母亲问我,西藏美不美,还是小学生的我想了想说,西藏应该是不美中的大美。用母亲的话来讲,无论这些童年的经历是喜悦美满还是悲伤痛苦,都已足够成为我一辈子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路成长伴随这些“财富”和对部队的向往,高中毕业后我毅然报考了军校,分配时我又主动提出要去西藏工作,但在与父母家人的多次沟通后还是折中选择了内地部队。
本以为和西藏的缘分将告一段落,没曾想因为工作的原因后来又多次进藏,而每次上高原时,母亲都会反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后来,我有幸来到了人们常说的“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
踏寻着父辈的脚步沿着边界线行程万里,见证过达坂上圣洁透亮的雪山白,班公错透彻心扉的冰川蓝,一路格桑花开的高原红,这里有难以言说的孤独寂寥,也有义无反顾的牺牲奉献,尽管有的山脉终年雪积千尺,但凛冽冰冻却掩盖不住的边关战士的铮铮誓言,和那深深融入骨子里的满腔热血。

他们之中,有的稚气未脱初上高原,趴在运输车后厢板上一边晕吐一边默默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有的白净腼腆不输须眉,父母老小千里之外相依相盼,还有的拖儿带口举家进藏,但似乎有一种执念和淳朴,也许早就跨过了大江大河,高过了千山之巅,更超越了花田月下的浪漫,让我被这清澈纯粹的藏地情多次动容。
前几日,老连队一名退役士兵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日喀则工作了,我既为他感到欣慰又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情感。同样,在父辈的后代中,还有一些儿时的玩伴,如今被亲切的称作“藏二代”,他们接过父辈的火炬默默的在藏区扎根奉献,继续谱写着这一代人的使命。
尽管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藏区变化也是日新月异,人们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明显有了质的改变,但较内地仍然是相对艰苦的,哪怕是在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长期坚守对身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依旧不可逆转,但挡不住一代又一代像孔繁森这样的老西藏人如洪流般前赴后继,割不断跨越岁月跨越山海的情感纽带。军人、警察、大学生、援藏工作者......
明知西藏苦,偏向西藏行。
因为他们的存在,这里的一切便愈发有了新的生机,他们不需要认识,也不需要知道,在他们心中早已把青春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
三十多年过去,我也从襁褓中的婴儿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二宝出生刚满月,我又收拾行囊再上高原。光阴在变,心态在变,依旧不变的是,父亲这个角色的高原逆行。
西藏,让我内心深处始终葆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站在夕阳洒落的红柳滩上,听着手机里循环播放的《向往神鹰》,我的藏地情结仍在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