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23日,延安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刊载了一组特殊的杂文——《野百合花》。这组杂文刊载后,一时间在延安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大量的群众就像是赶庙会一样到壁报上看这组文章。甚至就连毛主席本人,都连夜打着油灯去专门看了一眼。
因为这组杂文在延安乃至全国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坏了!这组杂文的作者,名叫王实味。

王实味的家庭出身比较困难,所以虽然他的才华很好,可是却总是无法顺利的完成学业。1923年,王实味考入欧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今天还在,不过已经更名为河南大学。从这学校的名字其实就能看出个大概,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赴欧赴美留学生的。
所以王实味青年时期接受的其实是西式教育,这一点很重要,一会要考。在欧美预备学校就读一年后,王实味因为经济窘迫被迫肄业。随后王实味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河南省有证据的邮务生,半工半读,月薪甚至能够达到30块银元,这样的薪资在当时可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了。

王实味接受的西式教育,讲究人权和平等,可是在邮政局的实际工作中,恰恰就是洋人不尊重他这样的中国人。王实味最终不堪其辱,直接辞职走人。1925年,王实味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就是这个时候王实味开始初步的接触文化领域,发表一些作品。
王实味进入北大后和胡风分到了同一个班,他受胡风的影响其实很深。而胡风这个人,怎么讲呢,他其实多少也有点问题,虽然信仰是坚定的,可是思想却有很多文人的毛病,解放后的各种运动中,他因为自己思想上的问题也吃了亏,而王实味后来的问题和胡风几乎是一样的,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6年,王实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为不顾党组织的劝阻,“发了疯般的追求”李芬,被开除党籍。王实味脱离组织后就去了南京,不久后和李芬同期入党的刘莹前往南京投奔王实味,王实味也就此得知了李芬牺牲的消息,唏嘘不已,然后转头就和刘莹结婚了。
王实味为了养活刘莹和后来出生的孩子,只能前往上海从事翻译著作的工作,这份工作收入不错,但是王实味脾气比较桀骜,和编辑发生了冲突,最终丢了饭碗。之后王实味又去了开封当英文教员,这个时候已经是抗战前夕了,王实味在学堂内频频抨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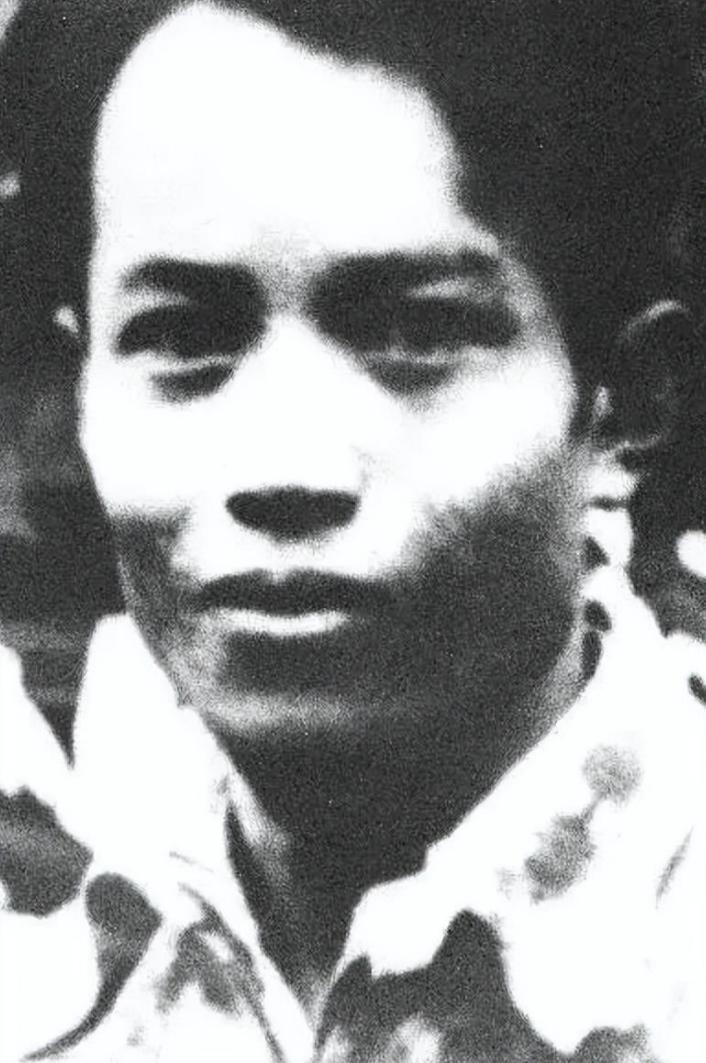
于是在1937年,被重新吸纳入党。卢沟桥事变后,王实味直接去了延安,去了自己心中的“梦想之地”...
“自找的麻烦”王实味在来到延安后,他的翻译水平立刻就派上了用场,党组织将其安排到出版局任研究员,主要工作就是翻译一些马恩列著作。王实味要是就这么老老实实的走下去,那么他未来的前途绝对是不可限量的,但是王实味偏偏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他青年时期接受的西式教育,让他将“人权”这一命题放在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上,所以他对当时延安的一些情况是很不能理解的。《野百合花》这组杂文,表面上是王实味用于纪念自己曾经爱过的那个女人,李芬。

但是实际上,《野百合花》绝不仅仅只是情情爱爱那么简单。王实味在这组杂文中,将延安的节假日晚会形容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又直言与“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极为不和谐。
延安干部的某些待遇上的差别,也被王实味形容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也形容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想想也知道,王实味的这种看法是很无理取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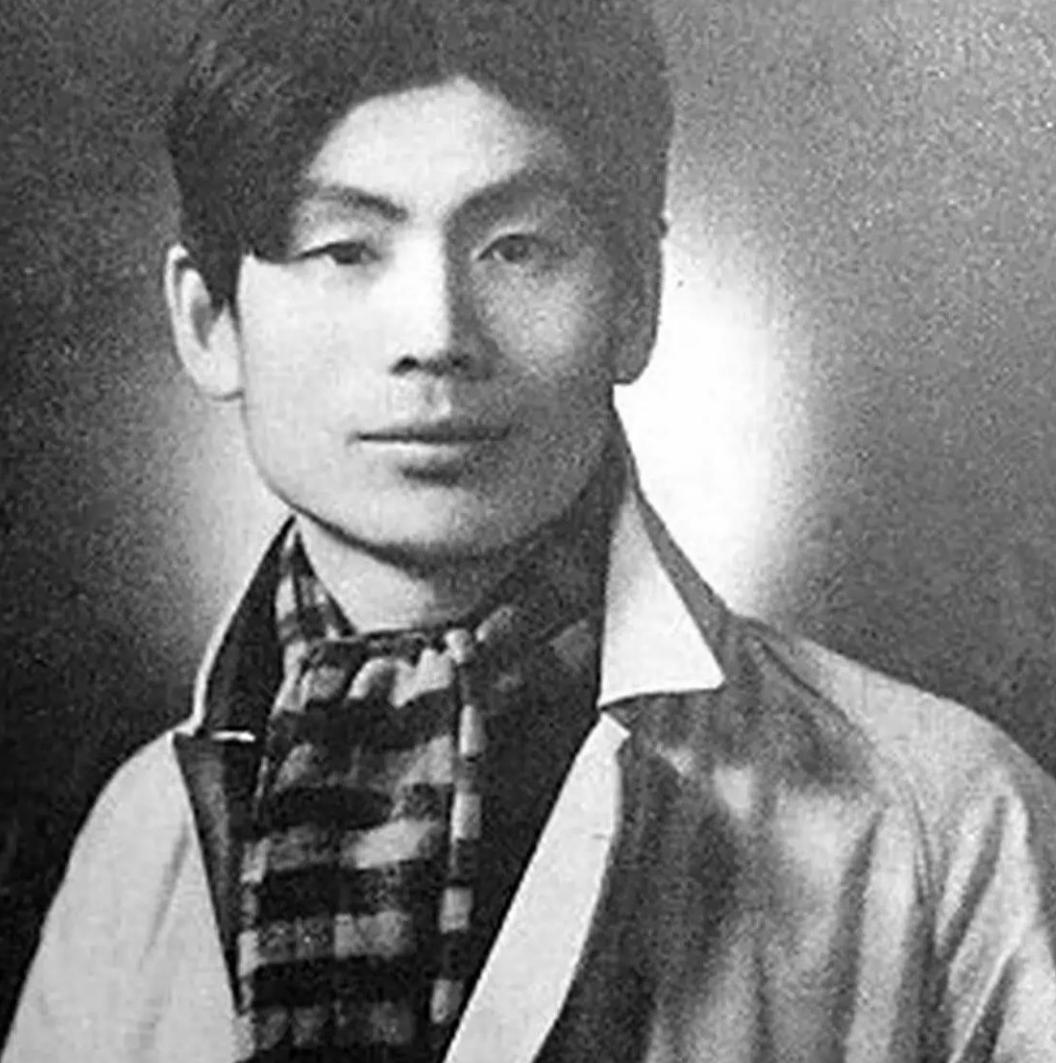
如果延安不办假日晚会,难道要每天都开追悼会吗?某些有糖尿病的老干部,你不给他打胰岛素,你不给他吃点好的,那难道你要看着他去死吗?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难道就说明所有干部都官僚主义?朱老总和毛主席自己也下地干活,难道他王实味眼瞎了看不见?
王实味的文章,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他们很快就将《野百合花》大量刊载在国统区,很多进步青年和老共产党员看过后产生了幻灭感,对延安的攻击日趋激烈...

我们以前评价过潘汉年,认为潘汉年的行为上是必然存在问题的,但是处理方式却不适当。王实味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要说王实味没有问题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他有问题,而且是有大问题,只是他的问题是个人思想上的问题,扭转过来就好了,并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立场问题!
那么是谁将这个问题扩大化了呢?

其实正是当时主持整风运动的康生,是康生将王实味的问题定为“托派问题”。因为王实味当年在北大的同学王文元,他就是托派。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托派问题的话,其实是不至于让王实味去死的。因为毛主席对托派问题的看法,和斯大林有着较大的不同,毛主席认为中国的托派和苏联的托派是不同的。
所以毛主席必然不会因为王实味是托派就杀他,更何况王实味压根就不是托派。他在北大肄业后长期脱离组织,王文元是托派他压根就不知道。所以这个指控,他一直都是不认的。这也使得王实味长期存在“抗拒改造”的行为,因此他就一直被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那时李克农进行了“抢救运动”,但是出于主客观条件,并未“抢救”王实味。他在1947年转移期间,被康生口头命令处决。直到一年后,毛主席才得知这个消息,怒不可遏,拍着桌子怒斥陕甘宁政府主席林伯渠:“你们还我王实味!”
参考资料:
《王实味:野百合花招来的杀身之祸》 于继增
《李克农与王实味案》 杨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