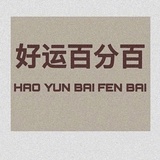美国介入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法律“依据”及其发展
今年7月25日,美国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无异议的方式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此法的主要目的是要修改2020年经由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而生效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简称《台北法案》)。此次修改的核心内容,是要在《台北法案》第二节a款中增加最后一段即第十段,具体内容为: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然而,此决议并没有涉及到台湾及其人民在联合国或任何相关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没提出任何有关台湾主权的声明。美国反对任何在没有台湾人民同意下,试图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
《台湾国际团结法案》通过质疑和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意在为帮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增强理据。由于《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是以修正《台北法案》的形式进行的,目前已通过了众议院相关程序,后续通过参议院审议及美国总统签署等程序“几无悬疑”,从而将会成为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一份正式质疑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生效法律。此法案与美国国会业已通过的其他相关法案及决议一起,无疑会推动美国国务院等行政部门加大其帮助扩展台湾“国际空间”的支持力度。同时,相较于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相关决议和生效法案,《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也标志着美国在推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法理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因而值得大陆高度关注、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应对预案。
一、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介入台湾“国际空间”的相关法案及决议
认真、全面梳理美国国会相关决议和法案会发现,在支持和帮助台湾扩展其国际空间问题上,美国国会以通过决议、法案等形式,为其介入台湾“国际空间”事务提供了相应的国内舆论和法律依据。总体而言,美国国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和法案等主要包括如下三类:
(一)决议
美国国会所通过的相关决议,大部分涉及到的是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活动,当然也有部分涉及到是台湾“加入”联合国。这类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通常只是政治立场的表达,其目的在于制造舆论,为后续相关立法制造和提供“民意”基础。此类决议又包括两类:国会通过的和没有通过的。没有通过的决议多数仅停留在提出阶段,没有付诸表决等后续程序。自1998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支持台湾参与WHO的决议共3份,分别是:1998年10月10日众议院通过的H.Con.Res.334决议,1999年4月12日参议院通过的S.Res.26决议,和2000年10月19日参众两院通过的H.Con.Res.390决议。没有通过的决议占大多数。
而从决议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些决议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91年-1997年为第一个阶段,1998年-2000年为第二个阶段,2001年-2008年为第三个阶段,2009年-2016年为第四个阶段。各阶段所涉内容具体特点如下:
在第一阶段,美国国会在所通过的决议中关注的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1991年,美国国会首次操作台湾参与WHO,为台湾扩大国际空间“鸣锣开道”。该年所提决议标题为“表达国会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立场”。在实质内容上,则表述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要求台湾及其2000万人民应当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拥有代表,同时国会还认为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1992年决议与1993年决议在标题及内容上都与1991年相类似。自1994年“台湾政策评估报告”的通过, 1995年的决议在内容上稍有变化,此时美国国会在内容上没有重点阐述台湾的代表权问题,而是以“台湾政策评估报告”为“肇始”,认为台湾应该“充分参与”联合国,包括获得联合国的席位。此外,决议中还宣称美国政府应立即鼓励联合国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研究台湾加入该组织及其有关机构的问题。同年的另外一份决议在内容上与前述决议相似。到1997年,其“理论基础”开始发生变化,增加台湾于1993年提出的“平行代表权”的相关内容,并表示美国政府应立即鼓励联合国采取行动,考虑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情况,采取全面解决办法,在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中“接纳”台湾。
自1998年开始,美国国会的关注重点开始有了变化,从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转向支持台湾参与WHO活动。1998年2月12日,美国国会首次采用了“关于台湾参与WHO”作为决议名称,内容也从此前从一般性地论述台湾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必要性”调整为专门只论述台湾参与WHO的“必要性”,也即聚焦的重点从综合性的主题变为单一性的主题。与此同时,在推动台湾参与WHO的具体策略上,美国也从此前的推动“加入”转变为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与WHO的活动”。例如,在同年10月10日众议院通过的H.Con.Res.334决议中,决议内容已经不再讨论台湾在WHO的代表权问题,而是将目光转向台湾如何“适当且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在此阶段(即第二阶段),美国国会共通过了三份相关决议,除前述1998年10月10日通过的H.Con.Res.334决议外,另外两份分别是1999年4月12日参议院通过的S.Res.26决议和2000年10月19日参众两院通过的H.Con.Res.390决议。就这三份决议的共同点来看,其内容与美国国会1999年12月7日通过的第106-137号生效法案基本相同,均强调“台湾及其人民应该适当且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三份决议的不同点在于,1998年10月10日众议院通过的H.Con.Res.334决议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在世界卫生组织中采取一些举措,让台湾以符合该组织要求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参与。1999年4月12日参议院通过的S.Res.26决议指示国务卿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国务卿为履行1994年“台湾政策评估报告”中所作的“承诺”而采取的措施,强调美国应当更加积极支持台湾加入“接受非国家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并寻找在国际组织中“倾听台湾声音”的途径。2000年10月19日参众两院通过的H.Con.Res.390决议与前两份决议的不同之处在于,该决议引进1999年第106-137号法案的“指示”,并“批评”国务卿在该报告中未能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没有遵循1994年“台湾政策评估报告”的“精神”。
第三阶段,美国态度和立场再次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回转”到了第一阶段的立场,即再次强调为台湾谋求“完全和平等的会员资格”;但与此一阶段不同的是,美国在此阶段为台湾谋求的会员资格是有限的,即基本局限于WHO等特定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而非联合国的会员资格。美国国会不再“延续”第二阶段所谋求的台湾“应当适当且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而是谋求台湾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享有完全和平等的会员资格”。自2001年8月2日H.Res.221决议的提出,直到台湾于2009年受邀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观察员之前,美国国会在多个决议上声明台湾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享有完全和平等的会员资格”。在2005年的H.Con.Res.154决议中,更是直接将标题命名为“表达国会认为台湾应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获得完全和平等的会员资格”。在内容上,表示美国应带头“谴责”台湾被排除在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之外的行为。
第四个阶段,美国国会立场再次调整,决议不再专门阐述台湾参与WHO的问题,而只简单提及了台湾应当具有联合国的会员资格。
通过前述介绍可以看出,美国国会在介入和推动台湾“国际空间”的问题时,每个阶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美国国会对台政策会随着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的相应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在前面三个阶段,台湾开始提出和主张“重返联合国”,并践行激进的“台独”主张。美国国会在此三个阶段所通过的系列决议,正与台湾“台独分子”的相关行为“相呼应”。而到了第四个阶段,随着马英九放弃“重返”或“加入”联合国的主张,转而谋求“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活动”,两岸关系出现了明显缓和,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在相应决议中也随之缓和,没有“重复”前述三个阶段的相关内容。
(二)有效法案
第二类是有效的法案。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并经由美国总统签署生效的类似法案共有6份,但此6份法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聚焦于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6份法案分别是:1999年12月7日通过的第106-137号公法、2001年5月28日通过的第107-10号公法、2002年4月4日通过的第107-158号公法、2003年5月29日通过的第108-28号公法、2004年6月14日通过的第108-235号公法,第6份则是2022年5月13日通过的第117-124号公法。
在这6份法案中,第一份法案是在李登辉在任期间作出的,中间四份是在陈水扁在任期间作出的,最后一份则是蔡英文上台之后作出的。马英九在任期间,美国国会并未通过类似法案。无论是李登辉、陈水扁还是蔡英文,都是推动“台独”运动的“关键性”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有效法案与第一类决议是有类似之处的。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和法案不断向台湾释放支持“台独”的信号。这些通过的法案与决议,与台湾当局的行动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从法案的标题和具体内容等来看,其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6份法案的标题“大同小异”,关注议题高度聚焦。从标题来看,美国干涉台湾参与WHO的行为具有“承接性”。除第107-158号公法之外,前三个法案均命名为:关于台湾参与WHO的法案(Concer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4的法案标题命名为:处理台湾参与WHO的问题。而在2022年最新通过的法案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示国务卿制定一项战略,以恢复台湾在WHO的观察员地位。法案标题的“小异”也可以反映出美国在加大对台参与WHO的支持力度。
其次,从具体内容来看,各法案的内容总体上都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论证台湾参加WHO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二部分则表达美国支持台湾参加WHO的“坚定”态度及国务卿应当采取的措施。当然,6份法案具体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前5份法案均强调台湾应当“适当且有意义地参与WHO”,最后一份法案则直接指向了恢复台湾观察员身份问题;前五份法案在第一部分都提及到了美国国会1994年通过的“台湾政策评估报告”,通过援引该报告来为美国支持台湾参与WHO提供充分的“政策依据”,第六份法案则未提及。
最后,从法案发展演变角度来看,后述法案大多只是在前述法案的基础上对台湾参加WHO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理论”或政策上的适当扩充。例如,第三份法案对第二份法案即第107-10号法案的修正就很简单,一是将布什总统在其致参议员姆科斯基(Murkowski)的信中的一个“要点”增加了进来,此“要点”是:美国应该寻找机会让台湾在国际组织中发出声音,以便为国际组织作出贡献;二是增加了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Tommy Thompson)有关将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言论。
相较于前5份法案的这种“小修小补”,第六份法案的逻辑特别值得关注:在该法案中,美国国会认为,在美国历届政府、国会以及有类似想法的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支持下,台湾于2009年收到了WHO邀请,从而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显然,在美国国会的理解中,台湾能够在2009年收到WHO邀请函,这应“归功”于其对台湾持续不断的支持,并认为台湾此后能够连续8年收到邀请,收到邀请就理应成为“惯例”。可惜的是,随着蔡英文上台后拒不认同“九二共识”,此“惯例”不灵了:自2017年起台湾就没再收到WHO的类似邀请函。美国国会把大陆在马英九在任期间所释放的善意(即允许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活动)“归功”于自身的支持,这真的是“贪天之功”,逻辑上完全颠倒黑白。
(三)《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之所以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单独归结为一类,是因为此法案与前述两类法律工具并不相同,尤其是与第二类中的生效法案存在重大差异。前述两类法律工具关注重点是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议题,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以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为攻击靶点,试图通过曲解第2758号决议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换言之,推动台湾参与WHO活动仅仅只是《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意图达到的目的之一,但并非唯一目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台湾无阻碍地参与包括联合国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与第二类中的生效法案的重大差异在于:第二类生效法案只是美国介入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单纯国内法律工具,《台湾国际团结法案》通过曲解第2758号决议而使之具有国际“正当性”与“合法性”,是把国际工具国内化了。因此,相较于第二类中的生效法案,无论是从“正当性”、“合法性”还是从动员国际舆论等诸多角度来看,《台湾国际团结法案》都具有前者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而这也意味着,《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与第二类中的生效法案叠加之后,美国介入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法律工具种类更丰富了,从此前单纯的国内法律工具发展到国内法律工具和国际法律工具兼备的新阶段。而从主题内容来看,也从专门只针对台湾参与WHO这一单一性议题发展为能推动台湾参与任意国际组织这样的“综合性”议题。
当然,从“溯源”角度看,尽管《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对第2758号决议进行了曲解,从美国国会角度来看,此种曲解却并非自《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始。美国国会对第2758号决议的质疑也早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至1993年,在该年,美国国会在所通过的决议中声称联大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彻底解决因中国“分裂”而产生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并主张台湾应当在联合国应当拥有席位。当然,美国国会当时只是试探性地抛出对第2758号决议的质疑。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的正式推出,则意味着美国开始正式“名正言顺”地攻击第2578号决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二、美国介入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特点及未来发展动向
(一)特点
结合美国国会前述法案、决议等可以看出,其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1)决议及法案在内容上具有“承接性”;(2)美国介入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力度在不断增加。
在操弄和推进台湾参与WHO等相关国际组织的国家中,美国无疑是最主动和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一方面,自1991年起,美国就率先通过其国内法来为自身“拓展”在台湾参与WHO议题上的可操作空间;另一方面,以1994年“台湾政策评估报告”为“肇始”,美国就不断推动国内立法“操作”台湾参与WHO、加入联合国等议题。而在此过程中,其法律工具箱也变得更“丰富”,既有国内法律工具,又有国际法律工具,既有综合性法律工具又有单一性法律工具。美国在通过其法律工具箱不断“介入”到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它也是心思“缜密”的国家,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国会陆续发布的决议(Resolution)、起草程序中的提案(Bill)及既有生效的法律(Act)中得到印证。而就这三者的关系而言,决议为前导,起到舆论铺垫等作用;提案是立法的“先声”和尝试,通过反复、多次地提出类似提案,为后续法案的起草和通过提供内容、技术等相应基础;生效法律则是最终追求目的。
此外,前述三类工具在内容上还呈现出“承接”的关系:美国国会后续通过的法案及决议,往往会援引先前的法案或决议中提及的内容,前后通过的决议或法案具有某种“滚动性”。以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推动台湾参与WHO的六份生效法案为例:后一份法案多以前一份法案的内容为基础,只是在后一份法案中增加了前一份法案通过后新发展的相关内容。
(二)未来发展趋势
从美国国会近两年行动看,美国国会在推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有如下新动态:
第一,提案呈密集排列趋势,且通过率较高。自2018年以来,美国国会大多以提案的方式发布有关推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议题,且通过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在国会内部,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美国干涉台湾参与WHO的议题凝聚了“共识”,对美国介入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意见也渐趋统一。一旦这些提案(Bill)通过成为法律效力最高的法案(Act),美国国务院就有了行动的压力。
第二,提案更加具有针对性、层次性,往往“直切主题”。以推动台湾参与WHO为例,提案基本上是围绕着三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台湾对世界卫生作出的“贡献”;二是认为台湾面临来自大陆的“施压”;三是指示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报告其为台湾重获观察员地位的努力。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内容似乎没有什么“新意”,基本上是对前述提案内容的“重复”与“补充”。实际上这些提案会形成巨大的舆论效果,为台湾参与WHO制造“实质突破”的机会。总体上,美国国会将多角度、多层次地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空间”,通过为台湾谋取“国际空间”而制造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和形象。而此种形象又能反过来“印证”美国国会前述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歪曲和曲解。
三、应对建议
对于美国国会在推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的前述诸多举措,大陆有必要高度重视,严肃应对。而从应对角度看,由于美国国会引发的挑战既涉及到国际法层面尤其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也涉及到美国国会国内立法程序方面,大陆就有必要考虑同时从多个角度入手,积极谋划相关应对措施:
(一)在国际层面加强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解释、宣传和适用
《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剑指”对象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对此决议的歪曲和曲解来为美国扩大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介入范围和力度提供“合法依据”。
总体来看,大陆在解释和适用第2758号决议上仍然有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1)未能充分认识到第2758号决议的于我有利性。无论从第2758号决议的具体措辞看,还是从第2758号决议的起草过程和辩论过程看,第2758号决议与“两个代表权”、“一中一台”等类似解释完全不兼容,是驳斥“两个代表权”、“一中一台”等类似提案的有力工具。但在实践中,在应对美国等提出的有关“两个代表权”等类似说法的时候,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却很少援引第2758号决议来予以驳斥;(2)在国际层面对第2758号决议的解释和说理不充分。一方面,对于美国官方和民间有关第2758号决议的曲解,大陆很少及时组织反击和驳斥,另一方面,在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每年在给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台湾问题立场的信函中,尽管都提到了第2758号决议,但对此决议的正面阐释是不充分的,错过了在国际层面正面阐释决议的正确含义的机会;(3)对第2758号决议的适用场景评估不足。由于第2758号决议的解释于我有利,在适用场景上,其既可以适用于联合国各机构,也可以适用于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等,但从我国对其适用的既有实践来看,目前对此决议的适用是极为有限的,其适用场景和潜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
要克服前述不足,我国有必要从如下两方面予以改进:(1)要重视对第2758号决议的正面宣传和传播,及时反驳和抵制美国对第2758号决议的曲解,防范其解释扩大影响。一方面,我国有必要在国际层面多宣传对第2758号决议的正确解释,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多在英文重要学术刊物等发表有关第2758号决议的解释与适用的论文,同时,还可以考虑召开围绕决议解释的国际学术会议,多渠道对第2758号决议的正确解释进行宣传和普及;(2)要重视在联合国各机构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对第2758号决议的解释和适用。第2758号决议是联合国系统内有关台湾国际地位的唯一有效决议,其既可以在联合国各机构内适用,也可以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系统内适用。在适用的过程中,我们要改变既有的不重视对此决议进行充分阐释的实践,充分利用此决议的起草过程、各国围绕此决议草案的辩论发言记录等资料,重视解释过程的完整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克服目前的解释太过简单和粗略的不足。
(二)要介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过程,加大对美国国务院相关行为的预期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国会相关“立法”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源头”。国会通过了相关决议或法案,美国国务院等行政部门就有义务去执行。美国国务院等行政部门在具体执行中尽管有一定的酌处权,却会受到美国国会的监督和制约。在这个意义上,要影响美国的对台政策,我们首当其冲就要在美国国会“立法”的过程中积极介入。一方面,我国驻美大使馆有必要与美国国会进行适当沟通,可以多考虑机会争取到美国国会演讲,向国会议员传递两岸关系的正确认知,另一方面,还可以多寻找机会与积极推动相关“立法”的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接触,积极对其进行游说,争取将相关“立法”遏制在萌芽状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在美国国会的立场不会更改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未来将加大对台湾参与WHO的游说力度。为此,我们不仅应当密切关注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及决议,还要时刻关注美国国务院的行动,防止更多的国家被其舆论导向而走远走偏,加入“错误阵营”。应该对美国国务院每年的类似行动有预期。只要美国国会的相关法案没有更改,基于执行法案并向美国国会报告执行法案情况的需要,美国国务院每年都会采取行动,呼吁并推动台湾参与WHO的活动。这个态势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需要对此有相应认知,并提前采取相应预防行动。
(三)修改或制定必要的国内立法,用国内法反制美国国内法
通过前述研究可以看出,美国的每一步行动都有明确的“法律”得以支持。无论是法案还是决议,其发展变化都是环环相扣、有迹可循的,美国国会擅长通过援引先前通过的法案或决议为自己最新的法案或决议奠定坚实的“立法基础”。而相比美国而言,我国国内相关立法是有相应不足的,例如,《反分裂国家法》等规定内容过于简单,可操作性比较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此类介入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行为缺乏明确规定等。因此,一方面,在有明确的国内立法依据的情形下,我国要积极适用相关法律规定来对美国的相关举措予以反制,另一方面,在既有立法存在不足的情形下,还有必要及时启动修改法律规定的程序,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为自身反制行动提供坚实的国内法律依据。
作者最新文章
国际TOP
- 1 197比102!韩国法案判决结果出炉
- 2 中国就是不给台阶,特朗普摊牌了,美国玩不下去了,向中国摇白旗
- 3 特朗普大仇得报!扎克伯格被罚款300亿美元,美国商界瞠目结舌
- 4 王毅外长董军防长首次配合,中方的安排有深意,对邻国极为重视
- 5 美国拒付会费,世卫组织宣布因预算缺口裁员重组
- 6 不到24小时,东盟欧盟集体让步,中国换了打法,对美文化霸权动刀
- 7 华盛顿大门已敞开,只等中方登门,特朗普以总统名义,立下保证书
- 8 激烈交锋,中乌粮食交易清零,基辅提高召见等级,中方回了2句话
- 9 美国人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90艘中国船开往美国,该来的躲不过
- 10 25对59,莎拉集团翻盘,律师称老杜无罪,马科斯家族叛徒出现
国际最新文章
- 1 中国不跪!站队中国的国家已出现,美财长下令:对华谈判暂时搁置
- 2 特朗普长子办超级富豪俱乐部,入会费50万美元还供不应求
- 3 韩国转卖中国稀土给美国,中方果断出手,“二级制裁”不是开玩笑
- 4 美国开始撤军!原来特朗普早就把话说透
- 5 离大谱!马德里赛因断电休赛1天世界第4炮轰:没法洗澡+被困赛场
- 6 美国要求希腊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
- 7 特朗普对华改口,欧洲老朋友提醒中国:切莫相信,美国还没被打疼
- 8 威廉和哈里的前管家,对未来的国王,剥夺他弟弟头衔发表了看法
- 9 53票赞成46票反对!投票结果出炉,特朗普一夜收到3大“噩耗”?
- 10 德国防长呼吁乌克兰拒绝美国的和平方案,称这无异于投降
热门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