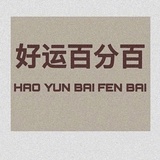联合公报认定为条约?实践中很难!
在希腊诉土耳其“爱琴海大陆架案”中,涉及到希腊和土耳其于1975年5月31日发布的联合公报是否构成条约、从而为国际法院提供管辖权依据的问题。该公报是在双方总理在该日会谈结束后直接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双方总理均未在该公报上签字。该公报中提到了彼此间争端的解决问题,原文是这样写的:
在会晤期间,两国总理有机会审议了两国关系目前状况的各种问题。他们决定(decided,法文原文为ont décidé),这些问题应(should be resolved,法文原文为doivent être résolus)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至于爱琴海大陆架问题,则应由海牙国际法院解决。他们确定了两国政府代表即将举行的会议所依据的总方针。
希腊认为联合公报可以构成一项协定。为了达到此效果,希腊认为,“公报除了包括习惯形式、友谊声明、主要原则的阐述外,在有充分必要的时候,其也可以包含条约性质的条款”。希腊律师还强调,联合公报是在国际实践中获得充分地位的现代仪式。希腊特别强调了前述句子中所使用的“决定”和“应”的措辞,认为这两个措辞标志着两国总理达成了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进行解决的共同承诺,两国总理在公报中达成的此“协定”就不再仅仅是承允彼此进行协商了。希腊进一步强调,两国总理达成的前述“协定”意味着,为将相关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目的,两国就有必要履行前述承诺中的义务,进一步缔结执行协定;如果一方拒绝缔结此类协定,另一方就有权根据公报中的前述“协定”单方面地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希腊还认为,如果缔结进一步的执行协定是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前提条件,那么,为缔结此执行协定,公报双方有义务基于善意而为此而进行磋商。
土耳其并不认同希腊的前述立场和解释。土耳其不仅否认公报构成国际法上的协定,同时还坚持认为,在两国政府从未就提交国际法院“事项”所涉范围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两国政府因此“共同和个别地接受国际法院对本事项的管辖权”。土耳其认为,对公报文本的检视表明,土耳其的相关意图是完全不同的,公报“远不等同于一国同另一国所达成的基于另一国单方面适用而将相关争端提交至国际法院管辖的协定”。土耳其指出,在公报磋商过程中,两国仅同意就大陆架的实质问题“优先进行谈判”, 而在这方面,彼此“甚至没有提到谈判缔结一项特别协定”以便将相应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土耳其还强调,在公报发表之后,希腊还曾试图推动彼此间谈判以达成前述这样的特别协定,希腊的此行为也能“确证”土耳其对公报的前述解释是正确的。土耳其还特别明确,如果公报真如希腊所称构成国际法上的协定,这样的协定至少是需要土耳其批准的。
国际法院认为,就形式问题而言,国际法中并无规则否定联合公报可构成一项协定。要判断联合公报是否构成一项协定,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所采用的形式(即公报这样的形式),而需要根据公报所涉行为或业务的性质,根据其所使用的实际措辞以及其起草时的特定情形来判断。在这方面,国际法院充分考虑了希腊和土耳其在公报起草和发表之前双方往来的相关备忘录。
从希腊的备忘录来看,早在发表公报前四个月,希腊给土耳其的相关备忘录中已经提出相关建议,即在不损害两国单方面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权利的情况下,与土耳其联合达成一项将争端交付国际法院解决的特别协定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土耳其回复的备忘录却强调要通过协商来解决彼此间的相关争端。对于希腊有关将争端联合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建议,土耳其仅表示原则上赞成。有关此建议的具体条件,土耳其提议两国政府开始高级别会谈。
对于土耳其的前述回复,希腊显然是满意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备忘录中,希腊同意,为了给自身前述提议以相应效果,彼此间应进行适当准备,以便就起草相应特别协定的具体条款展开磋商。基于希腊的此回应,土耳其总理在随后是这样向土耳其国民大会报告此事的:
希腊对我们有关在将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院之前应先进行会谈的建议给予了积极回应。当然,这样的会谈尚未开始。一旦开始,谈判的目标是缔结一项(有关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特别协定,相关协定将确定提交相关案件的基础。
通过对双方其他备忘录等的审查,国际法院认为,彼此间有关将相关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提议是,应以签署特别协定的方式联合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在此基础上,国际法院认为,自己不能从前述联合公报的任何规定中看出,其表明土耳其当时准备考虑的不是将争端联合提交给国际法院,而是普遍接受国际法院对争端的管辖权。相反,从土耳其的意图可以看出,联合公报中前述规定的语境(“context”)是:土耳其愿意在与希腊进行相关谈判后缔结特别协定,在特别协定中明确需要国际法院裁决的事项,然后再共同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公报中的前述规定似乎并不能证明土耳其在准备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条件方面的立场有任何改变。尽管双方对于联合公报中的前述规定有不同解释,但由于土耳其的立场一直是一贯的,即需要缔结特别协议,双方共同提交争端至国际法院,而本案是由希腊单方面提交的,国际法院据此认为,联合公报的前述规定并不能作为国际法院对希腊请求拥有管辖权的协议依据。
国际法院的前述实践表明,联合公报或联合公报中的某一规定能否构成协定,能否对公报当事国产生约束力,一方面需要考虑公报所使用的具体措辞,另一方面,对这些措辞的真正含义,尤其是当事国意图赋予其的真实含义,则需要根据当事国在公报发表之前的相应外交备忘录、起草过程等来具体确定。一方面,联合公报尽管使用了“决定”“应当”等在表面上似乎具有确定彼此间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措辞,此类措辞本身却并不足以“证明”公报就是一项协定,另一方面,要确定相应规定和这些措辞的具体含义,就需要充分考虑公报发表的“语境”,即双方起草公报过程中的往来备忘录、谈判记录等来证明前述规定和相应措辞能产生法律义务,对彼此有法律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根据公报具体规定和措辞等“得出”公报是协定,这只是一个初步结论,持此结论者有义务具体证明之。在这个意义上,论证某一公报是否构成协定,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寻找充分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明彼此在相关事项上存在共识。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就是,即使公报部分规定构成一项协定,也并不等于公报本身全部构成一项协定。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论证公报构成一项国际法意义上的协定,不如针对公报的某一具体规定讨论其具体法律效果。
在公报性质理解上的最大误区可能是:尽管很多学者在论文或专著中都反复指出,包括国际法庭等也在不同案件中阐述过同样的观点,即就条约而言,形式问题不重要,这却并不意味着,国家间达成的任何形式文本都可以被主张为条约。国家间但凡想要缔结条约,都会考虑和重视形式问题,形式与内容之间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越重要的内容,形式要求就越规范和严谨。很难想象,对于非常重要的事项,国家不会优先考虑通过缔结条约来予以实现和保障。
在前述意义上,对于公报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就需要注意到:国家采用不需要签字的公报这一形式本身就能说明某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公报或公报中的某一规定构成协定属于条约中的例外现象。在此背景下,一方主张其构成协定而被另一方坚决否认,主张方需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证明二者确实在某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从而使公报中的相关规定能产生相应具体的法律效果。
作者最新文章
国际TOP
- 1 197比102!韩国法案判决结果出炉
- 2 中国就是不给台阶,特朗普摊牌了,美国玩不下去了,向中国摇白旗
- 3 特朗普大仇得报!扎克伯格被罚款300亿美元,美国商界瞠目结舌
- 4 王毅外长董军防长首次配合,中方的安排有深意,对邻国极为重视
- 5 美国拒付会费,世卫组织宣布因预算缺口裁员重组
- 6 不到24小时,东盟欧盟集体让步,中国换了打法,对美文化霸权动刀
- 7 华盛顿大门已敞开,只等中方登门,特朗普以总统名义,立下保证书
- 8 激烈交锋,中乌粮食交易清零,基辅提高召见等级,中方回了2句话
- 9 美国人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90艘中国船开往美国,该来的躲不过
- 10 25对59,莎拉集团翻盘,律师称老杜无罪,马科斯家族叛徒出现
国际最新文章
- 1 特朗普长子办超级富豪俱乐部,入会费50万美元还供不应求
- 2 离大谱!马德里赛因断电休赛1天世界第4炮轰:没法洗澡+被困赛场
- 3 美国要求希腊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
- 4 特朗普对华改口,欧洲老朋友提醒中国:切莫相信,美国还没被打疼
- 5 威廉和哈里的前管家,对未来的国王,剥夺他弟弟头衔发表了看法
- 6 53票赞成46票反对!投票结果出炉,特朗普一夜收到3大“噩耗”?
- 7 德国防长呼吁乌克兰拒绝美国的和平方案,称这无异于投降
- 8 把国旗插到铁线礁,菲方目中无人,中国航母一路挺进,直逼菲沿海
- 9 无视特朗普警告,沃尔玛恢复中国市场进口,145%关税由美国人买单
- 10 立陶宛,曾经的"反华急先锋",最终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弃卒
热门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