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阳光从建筑工地的铁皮围挡缝隙里挤进来,灰尘在光束中漂浮。我站在售楼处门口,抬头望着那栋半完工的高楼,不知道该不该进去找项目部。
“小刘,那边来的客户你去接待一下。”
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男人正在指挥几个工人,他背对着我,肩膀宽厚,皮肤黝黑。
我掏出手机,又看了看县里小舅发来的信息:“明辉在黄岭新城当工程师,你去找他准没错。”
这个明辉,就是我堂弟刘明辉。
十年了,整整十年没见过他了。
堂弟比我小三岁,从小在我们家隔壁长大。他爹——我三叔身体不好,常年有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咳个不停。我奶奶去世早,三婶更是在堂弟五岁那年因病去世,所以明辉从小就跟着三叔,在我们院子里长大。
我妈常说:“这孩子命苦,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但明辉从不显得可怜,相反,他比我们都要坚强。
小时候,村里其他孩子下河摸鱼,都是光着脚丫,唯独他总穿着一双破球鞋,我笑他娇气,他也不恼,只是笑笑说:“万一踩到玻璃碴子,三叔医药费又得花不少。”
他比我聪明得多,小学时我背课文要念十遍,他只听两遍就能流利背出。我初中毕业考试全乡第三十八名,他是第一名。
高中时我俩一个学校不同班,他在重点班,我在普通班。那时候我们镇上高中,能考上大学的不超过二十个。我高考落榜,复读一年后考上了县城师范学院。明辉比我小三岁,等他高考那年,我已经上大二了。

他高考那年,三叔病重,住院花了不少钱。明辉原本一直是学校前十名,可高考发挥失常,最后只差五分就能上二本线。
三叔说:“复读吧,爹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
可明辉摇头:“爹,别想那么多了,我去打工。”
那年暑假,明辉收拾了一个旧书包,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就跟着村里老张头的儿子去了省城工地。
临走那天,我正好回家,看见他站在我家门口,脸晒得黑黝黝的,个子比我还高了半头。
“哥,我明天就走了。”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这是我高中的笔记本,你替我收着。”
我接过袋子,沉甸甸的,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十几本练习册,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工整。
“等你考上大学,回来拿。”我说。
他笑了笑:“我可能不考了。”
我当时不信,谁能想到,这一别,真的是十年。
我站在工地围挡外面,突然发现旁边墙上贴了张施工公示牌,上面赫然写着总工程师:刘明辉。

正犹豫着,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
“看什么呢?”
我回头,看到一张黝黑的脸,想了几秒才认出来:“明辉?”
他笑了,露出一口白牙:“猜我会这么黑?来,进来坐。”
项目部就在工地旁边的活动板房里,简陋但干净。他办公桌上摆着图纸,旁边放着一个工地发的泡面碗,里面插着半截2B铅笔和几支圆珠笔。
“坐坐坐,别看乱。”他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桌面,把几本杂志胡乱塞进抽屉,抽屉关不严,露出一角旧报纸。
我意外地看见桌角放着一瓶氧化锌软膏,还是我小时候用过的那种绿油油的药膏。
“还用这个?”我随口问。
“习惯了。”他挠挠头,“工地上皮肤容易干裂。”
倒了两杯水,杯子是工地统一发的那种白色塑料杯,有一只边缘已经裂了,他把好的那只推给我。
“听说你现在是总工程师?”我打量着他,难以把面前这个黝黑结实的男人和十年前那个瘦弱的高中生联系起来。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就是个头衔,干的活和以前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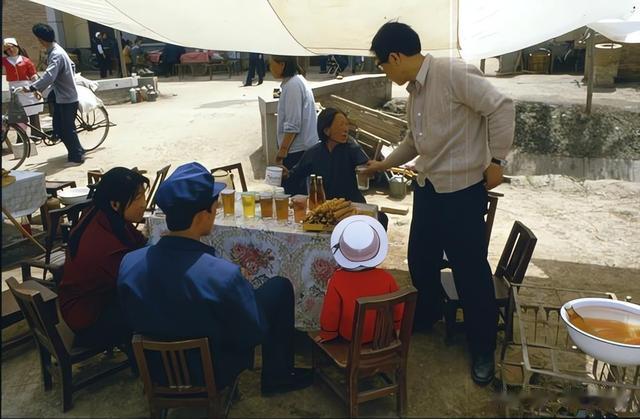
桌上的对讲机突然响了,他接起来,简短地说了几句专业术语,我一句都没听懂。
“楼层预埋件又出问题了,下午我得过去看看。”他放下对讲机,略有些歉意地看着我,“今天不好招待你了。”
“没事,我就是路过,听说你在这里,来看看。”
一阵尴尬的沉默。十年时间太长,曾经的亲密已经被现实磨平了棱角。
“你媳妇孩子呢?”我问。
“还没结婚。”他笑了笑,“哪有时间谈恋爱,工地一个项目就是一年半载的。”
我看了看墙上的施工进度表,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便利贴,有些已经发黄卷边。
“你这么忙啊?”
“还行吧,习惯了。”他拿起桌上的安全帽,“晚上有空的话,我请你吃饭。”
没等我回答,门外就有人喊:“刘工,五楼钢筋绑扎完了,等您验收呢!”
他冲我抱歉地笑笑:“你在这坐会儿,我去去就来。”
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背着书包走向远方的少年。

他办公室里有股淡淡的水泥味和汗味。桌上放着一个旧保温杯,杯盖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便利贴,写着”多喝水”三个字。
我注意到靠墙的小柜子上放着一本《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书脊已经卷边,书页间夹满了荧光色的标签纸。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响动,我走出去,看见几个建筑工人正围着一辆送水的三轮车。
“老李,水送到这儿就行了,你歇会儿吧。”
“不急不急,天还不热。”送水的老人摘下草帽,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走过去,问道:“师傅,刚才那个戴黄帽子的工程师去哪了?”
老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刘工啊,五楼呢,你有事找他?”
“我是他堂哥,来看看他。”
“哦,你是他哥啊。”老人笑了,露出几颗黄牙,“好后生,刘工。”
“他在这工作很久了?”
“有年头了。”老人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梅,递给我一支,我婉拒了,他自己点上,“刚来那会儿,他还是小工呢,天天扛钢筋,手上全是茧子。”

“后来呢?”
“后来啊,他晚上不睡觉,跟着老工程师学画图,学得快。再后来,他自己掏钱去上夜校,考了证。”老人吸了一口烟,“这孩子命硬,从小工到工程师,靠的是真本事。”
我内心一阵酸涩。十年时间,我在县城小学教书,朝九晚五,日子过得安稳但平淡。而明辉在水泥钢筋间摸爬滚打,从最底层爬到了如今的位置。
“那个,他爹还好吗?”老人突然问。
“三叔?”我愣了一下,“前年过世了。”
“唉,可惜了。”老人叹了口气,“刘工常说,等工程完工了,要接他爹来工地看看。”
我心里一紧。三叔去世那年,我去他家帮忙操办丧事,却始终不见明辉的身影。后来听村里人说,明辉赶回来时,三叔已经下葬了。
据说那天,明辉在三叔坟前站了一整夜,天亮才走。
“你看那栋楼,”老人指着半空中的高楼,“刘工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阳光下,那栋高楼巍然屹立。
傍晚,明辉终于忙完了,他换了件干净T恤,但安全帽的印痕还清晰地留在他额头上。

“走,带你去吃饭。”他脸上挂着疲惫的笑容。
我以为他会带我去什么高档餐厅,没想到是工地旁边的小饭馆,墙上挂着几幅发黄的风景画,空气中弥漫着油烟味。
“老板,来两碗牛肉面,加个卤蛋!”他熟练地喊道。
我们坐下后,他把工地发的那种医用口罩从兜里拿出来,折了两下垫在桌角下,让摇晃的桌子稳定下来。
“这家面不错,我经常来。”他解释道,眼睛里透着难得的放松。
牛肉面上来了,热气腾腾,肉块很大,他把自己碗里最大的一块夹给我:“尝尝,这家卤牛肉是一绝。”
“你还是这么实在。”我笑道。
“哪有什么实在不实在的,”他低头吃面,声音含糊不清,“人一辈子,不就那么回事吗?”
我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你那些高中笔记本,还在我家里。”
他抬头,眼里闪过一丝惊讶:“还留着呢?”
“当然,都收着呢。”
他笑了笑,又低头喝汤,但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动。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他提议带我去工地转转。
“这么晚了还要去工地?”
“夏天晚上凉快,正好趁着没人,我可以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工地的大门已经关了,他从便门带我进去,黑漆漆的工地只有几盏应急灯亮着。他拿出手电筒,娴熟地在钢筋水泥间穿行。
“小心点,这边有些建筑材料。”
我们乘坐施工电梯上到五楼,电梯老旧,摇晃得厉害,他却站得稳稳的,仿佛已经习惯了这种颠簸。
从五楼能看到整个城市的灯火,远处的高楼大厦,近处的街道车流,都在脚下闪烁。
“看,那边就是市中心。”他指着远处说,“等这栋楼盖好了,能看到整个城市。”
他脸上洋溢着自豪,就像小时候解出一道难题那样。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问。
“挺好的,”他靠在栏杆上,“起码比一开始扛钢筋的日子好多了。”
“为什么不回家?”我直接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三叔走的时候,你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沉默了一会儿,掏出烟,又想起我在旁边,又放回口袋:“工程紧,请不了假。”
我知道他在撒谎,但没有戳破。
“还记得你高考落榜那年吗?”我转移话题,“整个村子都觉得可惜。”
“记得。”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时候挺不甘心的。”
“所以为什么不复读?”
他沉默了片刻,突然说:“三叔欠村里老周家两万块钱,是我看病住院的时候借的。”
我一愣:“我怎么不知道?”
“没人知道,”他轻声说,“三叔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借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