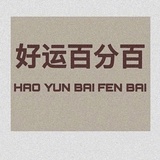中国为何没有委员曾被任命为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在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国际法议题的过程中,特别报告员的作用无疑特别重要,是“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中心”。尽管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16条的规定,只有在涉及到“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时才会任命特别报告员,但在实践中,国际法委员会却并没有遵循此限制,无论是在“逐渐发展”中,还是在“编纂”中,都会涉及到特别报告员的任命,而且,一般都会在议题的尽可能早期阶段就任命。
特别报告员的职责主要有:准备针对特定议题的报告;参加国际法委员会有关该特定议题的全体会议;与负责该特定议题的起草委员会通力合作,推进议题的编纂进程;准备该特定议题草案的评注以供国际法委员会参考。
国际法委员会首次任命特别报告员是在1950年。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从国际法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的数字看,在249位委员中,一共有65位委员曾有被任命为负责某一议题的特别报告员的经历。尽管如此,国际法委员会对特别报告员作用的评估,却是在多年之后。
理论上,在任命特别报告员的时候,国际法委员会应注意到地域分配的适当均衡问题,但在实践中,被任命的委员是否在相应问题上有专长、取得了公认的研究成果,以及是否对相应议题抱有热忱与兴趣等,却更为关键。被任命为负责某一议题的特别报告员,一般都要求其对该议题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或有非常透彻的理解,并且能长期地投入和关注。语言也是任命中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受限于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语言,尤其是起草所使用的语言主要为英文和法文,在无法选择和决定自身母语的背景下,能熟练使用一种或多种工作语言的委员,胜出并出任特别报告员的几率,相较于母语为非工作语言的委员而言,可能要高一些。当然,这也不排除某些其母语为非英语或法语的委员出任特别报告员并表现突出的情形。
特别报告员能通过自身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来推动国际法委员会启动对某一议题的研究,或者把某一议题列入国际法委员会正式工作议题名单。国际法委员会正在工作的议题,或者已经编纂完成的议题,有一部分即是由国际法委员会的某一委员推动提出并列入委员会正式工作议题之中的。而一旦相关议题被国际法委员会列入正式工作议题,只要该委员依然在任,该委员基本就会被任命为负责该议题的特别报告员。例如,“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议题是由国际法委员会长期项目工作小组在2006年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对此议题进行编纂,主导者是后来曾担任此议题特别报告员的罗曼•科洛德金(Roman A. Kolodkin)。推动其考虑的动机,是源于国际法庭和国家法庭审理的系列案件,其中不乏一些经典案例,如皮诺切特案,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刚果诉法国“在法国的某些刑事程序案”,以及沙龙在比利时被诉案等。而提出此议题的基础,则源于他此前对与此相关议题的研究基础和长期跟进。至少从其官方简历来看,其发表的与此相关此成果至少有:
第一篇相关成果是1994年发表的,讨论的是前南刑庭的设立问题;第二篇相关成果是1996年发表的,研究的是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问题;第三篇相关成果是2005年发表的,关注的是国家官员豁免于外国刑事管辖问题;第四篇相关成果是2014年发表的,是有关外交保护问题的;第五篇相关成果是2014年发表的,讨论的是国际法院判决中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官员的豁免问题。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其对此议题的关注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于平时的积累和持续的跟进与研究。此种研究的厚实也体现在其于2006年提交给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将此议题纳入委员会工作议程的报告中。
正因为有前述积累的基础,其2006年递交给国际法委员会有关将此议题纳入委员会工作议程的报告被国际法委员会所接受。2007年,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将此议题纳入其工作日程,从而正式启动了对此议题的编纂。科洛德金即被任命为负责此议题的首任特别报告员,并在任内提交了3份研究报告。
特别报告员会在关键问题上决定条款的编纂方向和编纂的成功。例如,就国家责任议题的编纂而言,从国际联盟“国际法逐渐编纂委员会”开始,即尝试对此议题进行编纂。国际法委员会成立后,此议题也被列入了委员会最初重点关注的14项议题之中。但是,对此议题的编纂却“一波三折”,最终案文直到2001年才最终二读通过。这既与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有关,也与特别报告员的作用有关。负责此议题的先后有6位特别报告员,但真正对议题的编纂起到重要作用的,分别是第2任特别报告员阿戈和最后一任特别报告员克劳福德。克劳福德直接促成了此议题的最终编纂成功。其在国家责任的援引等几个重要条款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正因为某些特别报告员在决定议题顺利向前编纂上作用颇为关键,某些特别报告员在获得其他机构新的任命、并已辞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之后,国际法委员会依然会请其以个人身份继续担任特别报告员,进而推进相关议题的编纂工作。负责国家责任议题的阿戈可谓此方面的典型。
自1963年起,阿戈即被任命为负责国家责任议题的特别报告员。1978年,其在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之后,即辞去了所担任的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职务。尽管如此,时任国际法委员会主席给时任国际法院院长去函,商请同意阿戈以私人身份继续其所担任的特别报告员工作、以顺利完成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的草案编纂事宜。国际法院院长同意阿戈以“专家顾问”(expert consultant)身份继续推进相关议题的编纂。阿戈随后分别参加了国际法委员会于1979年和1980年召开的第31届和32届届会。1979年,他向国际法委员会递交了第8份报告。1980年,其提交了第8份报告的附录。正因为在国家责任议题编纂上贡献巨大,阿戈因此而被某一国际仲裁庭称为负责国家责任法议题的“导师”(mentor)。
当然,从特别报告员制度的具体实践来看,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主要包括:特别报告员在准备其将在下一届届会中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的过程中,事先要不要将相关报告的性质、范围等提前向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甚至获得国际法委员会批准的问题;在届会召开之前,国际法委员会其他委员能否提前获得相关报告的问题;特别报告员与起草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报告员尽管是独立工作,但为保证其工作更有成效期间,是否应给其提供常设顾问团队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国际法委员会在今后实践中逐一解决。
中国迄今已经有9人先后任职国际法委员会。遗憾的是,迄今却无任何一位委员曾被任命为负责某一议题的特别报告员。如果将中国委员的此种表现与咱们的邻居日本和印度相比,数据上的差异可能更需要我们注意:印度先后有5人任职国际法委员会,其中1人曾被任命为特别报告员;日本先后有4人任职国际法委员会,其中2人曾被任命为特别报告员。
作者最新文章
国际TOP
- 1 197比102!韩国法案判决结果出炉
- 2 中国就是不给台阶,特朗普摊牌了,美国玩不下去了,向中国摇白旗
- 3 特朗普大仇得报!扎克伯格被罚款300亿美元,美国商界瞠目结舌
- 4 王毅外长董军防长首次配合,中方的安排有深意,对邻国极为重视
- 5 美国拒付会费,世卫组织宣布因预算缺口裁员重组
- 6 不到24小时,东盟欧盟集体让步,中国换了打法,对美文化霸权动刀
- 7 华盛顿大门已敞开,只等中方登门,特朗普以总统名义,立下保证书
- 8 激烈交锋,中乌粮食交易清零,基辅提高召见等级,中方回了2句话
- 9 美国人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90艘中国船开往美国,该来的躲不过
- 10 25对59,莎拉集团翻盘,律师称老杜无罪,马科斯家族叛徒出现
国际最新文章
- 1 中国不跪!站队中国的国家已出现,美财长下令:对华谈判暂时搁置
- 2 特朗普长子办超级富豪俱乐部,入会费50万美元还供不应求
- 3 韩国转卖中国稀土给美国,中方果断出手,“二级制裁”不是开玩笑
- 4 美国开始撤军!原来特朗普早就把话说透
- 5 离大谱!马德里赛因断电休赛1天世界第4炮轰:没法洗澡+被困赛场
- 6 美国要求希腊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
- 7 特朗普对华改口,欧洲老朋友提醒中国:切莫相信,美国还没被打疼
- 8 威廉和哈里的前管家,对未来的国王,剥夺他弟弟头衔发表了看法
- 9 53票赞成46票反对!投票结果出炉,特朗普一夜收到3大“噩耗”?
- 10 德国防长呼吁乌克兰拒绝美国的和平方案,称这无异于投降
热门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