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聚光灯熄灭,麦克风静音,走下舞台的“艺术家们”,有着怎样的隐秘世界?
刺猬公社联合爱奇艺【桃厂艺术家】栏目,以独家访谈视角,为你揭晓喜剧创作者的幕后故事。
文 | 星晖
编 | 石灿
如果你抢先落座,就能在豁朗的笑声溢满观众席之前,看清舞台上喜剧人的面庞。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有一种奇异的魔力。它的主题是逗人发笑,却常常引起深沉的思考,并在互联网上掀起热议。
观众为精彩的包袱捧腹,却也与抖包袱的人产生共情,试图理解创作者内心的汹涌波涛。
那些故事背后的人文底色,令我们感到好奇。
或许台上是一位腰部演员?他的故事关乎挣扎、沉淀与厚积薄发,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
也可能是一位职业编剧?总是维持叙述者的姿态,真正的话语权却不时缺位。无论在幕前还是幕后,才华本身理应得到尊重。
不然是一位小众艺术家?或许还不够被大众熟知。但是在多元包容的氛围里,观众将有幸目睹前所未见的风景。
来到爱奇艺自制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创作者们,为什么能够碰撞出如此灿烂的火花?平台协力构建的创作氛围,又是如何激发了生机勃勃的喜剧力量?
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创作者们的故事里。
年、昼夜与分秒之间选搭档的紧要关头,蒋龙回想起一段令他印象深刻的喜剧表演。
那是个关于争执的场景:两个演员嘴上骂骂咧咧,但是歌声一响,他们就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颇陶醉的模样。
于是在组队现场的音乐声中,蒋龙效仿着试了一位又一位选手。而那位最能和他跳到一块儿去的哥们,成了他日后的喜剧搭档,名字叫张弛。这个组合则被称做“逐梦亚军”。

“逐梦亚军”成立之初锋芒不显,愿景也很单纯,用张弛的话来说:“能留下一个作品就好。”
第一次看到其他选手表演时,两个人都“傻了”,觉得“好多想法我们根本想不到。”大开眼界之余,他们体会到了十足的压力,蒋龙甚至觉得节目第一轮都不见得能挺过去。
然而令人惊喜的是,“逐梦亚军”的实际表现不但没有“一轮游”,而且一次次惊艳四座,斩获了绝佳的口碑。到中后期,大家越发期待他们的表演,节目中甚至产生了一种叫做“神坛压力”的说法。
这匹黑马的背后,蕴含着两位演员多年来的深厚积累。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蒋龙拍了六年戏,其中不乏《扶摇》《全职高手》这样的大制作,但并非每个观众都能记住“蒋龙”的名字。
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尺度下,蒋龙竭力争取各种各样的机会。频繁而主动的试戏节点成了一种刻度,标记着腰部演员的辛酸奋斗史。
城市中的另一处,年复一年的学习、排练、演出,使张弛的人生与舞台紧密勾连。大约二十年前的一天,母亲带着仅仅九岁的张弛前往北京戏校,使他一头扎在京剧上。六年后张弛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毕业起在北京地区出演舞台剧,成了一名职业演员。
当爱奇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抛出橄榄枝时,两个演员的命运就此交汇。
相较于那些专精喜剧的演员,“逐梦亚军”有着不可否认的稚嫩之处。蒋龙虽然接触过喜剧表演,但不曾经历系统、专业的训练,以往更多是依靠感觉行动。京剧出身的张弛,对于sketch(素描喜剧)这类专业概念也并不太熟悉。
在前期米未组织的的工作坊环节,他们像海绵一样迅速吸收新知,张弛成了工作坊最活跃的参与者之一。蒋龙则梳理了过去的想法,然后下定决心花费好几个月做准备,“觉得还是赌一把。”
蒋龙和张弛开始了喜剧创作,并在节目组的保驾护航下,将孤零零的点子一步步落到实处。
编剧六兽老师为他们解决剧本中的难点,例如确立《这个杀手不大冷》中“杀手”与“人质”的核心关系。导演王建华则帮他们发掘出“人质”用吉他反制“杀手”这个点。而表演指导负责引领“逐梦亚军”进入喜剧的表演模式。

《女友来了》彩排前夜,服装组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缝制出三身精致的灯条服,才有了后来令人眼前一亮的熄灯场面。
这是前所未有的机会。那些听上去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在节目组的配合下照进了现实。“好多很幼稚的、甚至听起来不切实际的东西,这次都好像可以实现。”蒋龙说道。
“平常演舞台剧剧本已经给你摆好在那了,你直接就来演就完事了。”张弛说道,“《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会让我更主动一点,主观能动性更强。”
《女友来了》起初只定了标题,硬是由两个人生活中的点子攒了起来。《最后一课》中“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教诲,来源于蒋龙自己的学生生涯。《台下十年功》里的戏曲元素,灌注着张弛学京剧多年的感悟。
创作过程中,“舞美”是一个被演员们频频提起的关键词。
“咱们舞美是太厉害了,细节做得特别好,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张弛感慨道。铺在地上的报纸、敲出声音的桶、风扇的质感……细微处总能让他们感到惊喜。当张弛和蒋龙置身于这样的场景,又常常会迸发出新的灵感,进而增添更多的巧思设计。
他们总是会想:“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舞台,还是别浪费每次机会。”
于是蒋龙对《最后一课》额外做了诸多场景布置,总觉得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张弛较真地为《台下十年功》准备真正的戏曲道具,因为他相信“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两人日日夜夜反复练习,调整每一个动作细节。
张弛说,《台下十年功》的结尾其实改了好几个版本,因为他们最开始想表达的东西很多。“结尾有说脱口秀版本的,有各种各样的,后来感觉说什么好像潜意识都有点不太对,就选择不说了。”
到《台下十年功》正式演出的时候,临近尾声,伴随着一句“大家好我是张弛”,欢呼与笑语响起又平息。

前面以分钟为单位的时间里,“大我”与“小我”逗乐了观众一遍又一遍。
但接下来的三十多秒,张弛没有说话,他静静地望向四方。灯光照亮张弛的面庞,眼眶微微有些泛红。
直到《叫小番》的音乐再度奏鸣,年岁累积的热忱涌现,他分秒不差地踩进点——
在观众席里,也在报幕牌上当演员在舞台上卖力表现时,《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编剧们正坐在观众席里。
他们笔下的故事在台上复现,光标下的文字成为对白,肩负着引发笑声的使命。
编剧们的名字出现在每个节目的片头字幕,体面而醒目。于奥描述道:“它是跟演员一样很大的。”

于奥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编剧中的一员。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她做过几年话剧导演,也参与编剧工作。2015年前后,于奥尝试转战影视行业,朝着影视编剧的方向发展,并积攒了不少作品,种种题材与发行渠道都有所涉足。
作为产业生态的一环,编剧是尤其重要且特殊的工种。
编剧们所服务的影视作品,具有生产环节多、周期长等特征,编剧工作又是相对前置的。
最多的时候,于奥手上会有四、五个项目同时推进。“打比方说一个电视剧,你比较顺利的话,可能也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所以在这个期间,肯定还需要接其他工作去填补一些时间,包括经济来源。”
漫长的战线,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波动与风险。并行的多个项目中,有的会面临方向上的变化,有的难免中途停滞,乃至完全终止。
据于奥透露,她曾经按照需求完成了某个项目的剧本初稿,但由于最初锚定的演员需要更换,导致原本设计的剧本结构不得不重新调整。
前置的剧作环节在漫长的工业周期中摇摆,给编剧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从普遍的行业现状来看,没有人能够在经济上替编剧承担过程中损失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2016年,于奥曾接触到一个国产情景喜剧项目。她说:“《我爱我家》《老友记》这些都是伴随着我们成长起来的,我们也想说能不能做一个类似的东西?”尽管后来写出了24集剧本,但这个项目在实际推进中遭遇了种种现实问题,包括演员的知名度、情景喜剧的可验证性等等。
事实上,由于制作方、平台各个主体面向复杂的市场状况,剧本创作居于链条上游,编剧的创作话语权也就无可避免地受到掣肘。
在报幕板上给予编剧应有的尊重,或许只是个小细节,但现实中却很少有节目能做到这一点。
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于奥一直是“朝阳男孩”组合的坚实后盾。不过她也观察到了其他同行与演员的组队过程,“节目组真的非常尊重编剧,他们尝试着去理解编剧,理解sketch舞台上编剧和演员之间的关系,然后尽力再去融合合适的编剧和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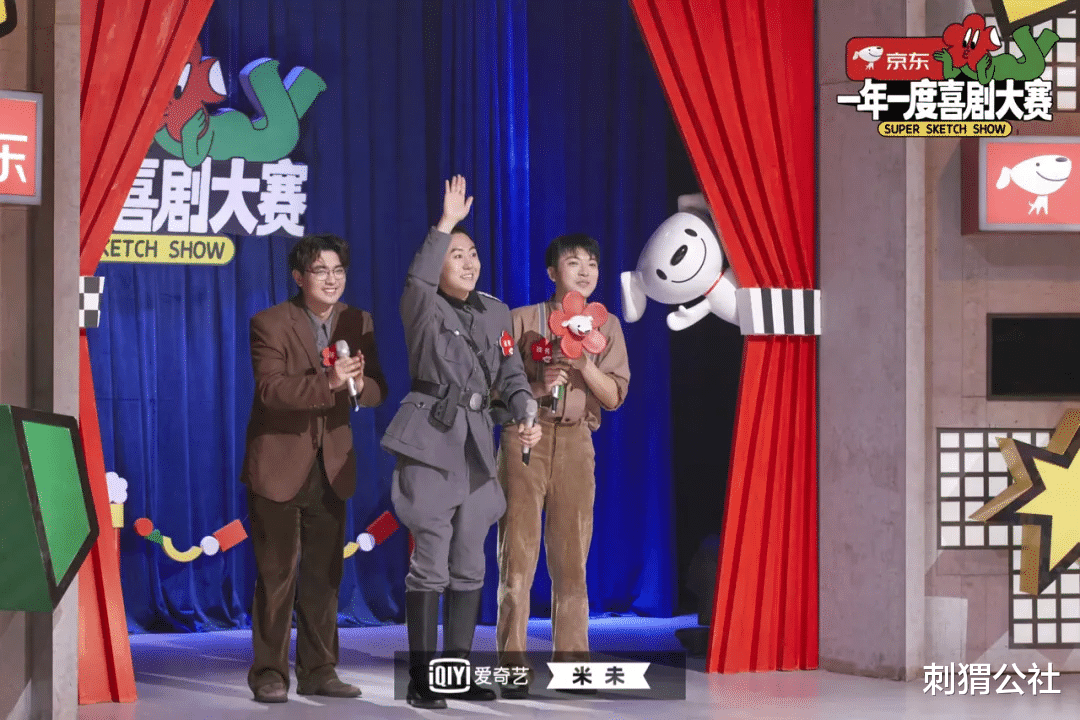
编剧得足够了解演员,才有可能在有限的十分钟内,调动起演员本身的特质或习惯,让剧本的风格和调性顺应演员的长处。
“譬如扬凡,他看起来不太说话,但是他其实在台下是非常细腻感性的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非常饱满。所以有时候一些算是情感表达类的东西,可能会给他多一点点。”于奥举例解释说。
这样的思考贯穿始终,她尽力放大每一个演员的魅力,帮助他们感染观众。
当演员们在舞台上登场,于奥就静静地坐在观众席里。“站到观众的视角去看,你会更清楚哪个地方节奏有问题,语言有问题,表现有问题,调度有问题,及时地进行一个调整。”
每一个赛段,节目组都会组织举办“提点会”,先抛出点子,再渐进到之后写剧本的阶段。在于奥看来,“我觉得这些流程是很专业的,他们也在尝试去找这样更专业的制作方式。”
有时,于奥也会得到来自节目组的建议,但这些建议从来不是强制的。在赛制压力与艺术创作的平衡点上,这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给予创作者的自由与尊重。喜剧人们能够自己选择搭档、自己寻找编剧,自己决定场景、决定剧本。
谈到为什么选择做编剧时,于奥说她愿意自得其乐地坐在键盘前,去创作一个世界,她喜欢看到演员为剧本而兴奋或赞美。
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日子里,“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尝试了很多很多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我们自己特别喜欢的,有我们自己不太满意,但是整个过程我觉得并不遗憾。”
能够真正用作品与观众对话,留下立得住的作品,这是于奥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所有创作者的梦想。她渐渐发现,这里的聚光灯不止打在演员身上,也照亮了那些隐于幕后之人。
幕布落下时,观众会回味《笑吧,皮奥莱维奇》,会记得《钱!啊》。也许这一次,他们也会记住编剧的名字——于奥。
小舟从剧场开启漂流武六七最早接触到默剧,是起源于朋友王梓的一个想法。
他说,咱做一个不说话的剧行不行?
那时武六七也不知道什么是默剧,也没怎么见过,但觉得挺酷的,种子就这样种下。
时至今日,武六七研究默剧已经有十年时间,早期主要靠自学。
“我们那会在特小的一个地方,就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老头老太太在那儿吹萨克斯、学葫芦丝的一个地方。”武六七就在这块闲置的场地上排练,每周在那免费办一次演出。
在他的记忆里,整个屋子也就20多平米,坐个20人就挺挤了。
后来武六七又参与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工作坊,了解到了小丑戏、物件剧等形式,萌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他开始自己研究这些表演形式,有想法就在小剧场里尝试。那时他每个月至少维持着四、五场演出的表演频率,每场大约有五、六十个观众。
这一两年,尽管演出的频率提高了,但小众艺术的盘子依然不大。不仅是市场普及度不高,创作端的活力也并不充足。直到今天,武六七所认识的做默剧的人,“可能全国也就十个左右。”
据武六七透露,前几年,剧社在线下的宣传曝光主要还是依靠口口相传。虽然也不缺少观众,但是主要群体是来自几个剧社演出积累来的微信群。
地域上,小众剧种的观众也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其他城市就不太好做了,比较难卖票。”
为了生计,武六七短暂地做过广告演员、接过话剧,但他从没有真想过转型放弃。
当爱奇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机会降临时,武六七想让更多人看到默剧、小丑戏、物件剧,了解这些喜剧门类的存在。“我们可能节奏不会像语言类节目那么快,需要大家慢慢来看。”

虽然大众不熟悉,但武六七其实并不特别担心,因为他相信观众的接受力。这是十年线下演出经验给他的底气。
节目组不干预创作,而是尽量支持他的创作。物件剧本就需要大量时间制作道具,《花匠》更是一出大群戏,要准备多达60多种道具。
最紧张的时候,能出力的人都会给武六七搭一把手。同队的伙伴、制作人、道具老师、导演……大家前前后后,没日没夜地做了有半个月。“有时候下班收工的时候都赶上早高峰了。”武六七回忆道。
直到上台前最后一刻,大家依然在排练《花匠》,彼此配合。在武六七眼里,这次是一个突破,因为他此前表演的都是独角戏。
“人多了以后真的是力量大,能展现出来的东西更丰富了。希望以后要是有机会,还能再做一些这种更大型的戏。”武六七说道。
观众们常常把武六七视作选手中很“特别”的一员,但在武六七自己眼里,其他选手也都各不相同。“哪种风格都有,大家都有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他尤其偏爱节目中的“三狗”,笑称要向他们拜师学艺。
在专业的创作氛围下,sketch、默剧、漫才等不同风格的喜剧人相聚于此,多种多样的作品都得到了公平的展示机会,接受观众的检阅。
据武六七观察,身边有的朋友在做即兴喜剧表演,这和默剧一样相对冷门。他说:“我觉得要有更多这样的综艺来帮助我们,然后也让更多人能接触到这些小众门类。”
《漂流记》的结尾,武六七手中的小舟唤醒了观众们的童心,留下造梦般的时刻

那驾驭着小舟的艺术家从窄小的剧场启航,终于被更广大的世界看到。
尾声《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不会是终点。
蒋龙和张弛都将在演员的职业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未来计划挑战更多元的角色。
张弛特别关注网友评论,《台下十年功》播出前他无比忐忑,直到看见正面反馈才放下心来。其中有一位网友分享说,本来想解散乐队,但看到节目之后觉得还想再坚持一下。
收到这条评论的那一刻,张弛忽然觉得,表演带来的一切辛劳、痛苦似乎都不重要了。
“我就觉得它太值了。”
于奥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交到了一群特别可爱的朋友。她还记得比赛压力最大的日子里,大家互相支撑着挺过难关,“手拉手一起走过来的”。
而新的故事,又将从她的键盘上“噼里啪啦”地生出枝桠。
回到剧社的武六七说,参加节目之后来看演出的人变多了。比过去更大的场地,如今也有可能坐满。
他并没有因此懈怠,而是想着要赶紧创作更多新节目。
“再出新戏,然后再去更多地方演。我们计划来年做小巡演,在国内做一圈试一试。”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像林中的溪流,它在某一刻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创作者,让他们结伴掀起清亮的波澜。艺术家们在这里找到了舞台,也找到了观众。
往后,溪水将四散为支流各自奔涌,浸润一整片广袤的森林。
在冬季,我们共同跋涉过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