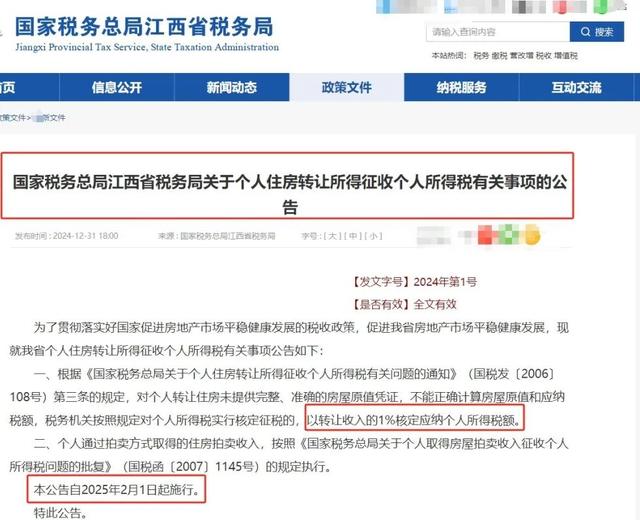【编按】
2024年12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增值税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有了专门法律。
增值税作为我国的第一大税种,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30%左右,其立法进程备受关注。
这次增值税法的通过,据专家介绍,是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对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标志性意义。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不仅进一步规范、统一、稳定了税制,增强了透明度,对建立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起到支撑作用,同时也为市场主体提供更稳定的税收预期,有助于增强信心。但是,增值税法从我们国家创投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却在其中发现了自营改增条例遗留下来的问题与疑惑。
2024年12月27日,融中财经刊发了深圳创投公会名誉会长蒋玉才《新增值税法中关于“应税交易”的问题与探讨》的稿件,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向,尤其在创投行业得到投资人的关注和探讨,本次融中财经借助DS的梳理,进一步说明此文观点。
《新增值税法中关于“应税交易”的问题与探讨》原文链接:
https://www.thecapital.com.cn/newsDetail/113820
【以下为DS生成,略作编辑】
一、问题探讨
1. 核心争议点:增值税法对金融商品的定义与税收逻辑
文章的核心争议在于新增值税法(2026年实施)对“金融商品销售”的界定及其税收处理逻辑。根据增值税法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表述:第三条将“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列为应税交易;第四条进一步明确“销售金融商品”属于应税交易(如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或销售方为境内单位)。
但作者指出,金融商品既不属于“货物”“无形资产”或“不动产”,也未在后续条款中明确其税率及计税方式,导致以下问题:归类逻辑矛盾:金融商品与现有应税交易类别(货物、服务等)的界限模糊,法律未提供明确依据。
执行不确定性:税率和计税规则未在税法中直接规定,可能延续税务部门通过行政文件(如财税36号文)自行解释的做法,削弱税收法定原则。
2. 历史背景:营改增政策的遗留问题
文章追溯至2016年“营改增”改革,指出金融商品转让被纳入增值税范围的争议:营业税时期(2016年前):创投行业股权转让(无论一级或二级市场)均不缴纳营业税(依据2002年财税191号文)。营改增后(2016年):财税36号文将“金融商品转让”定义为金融服务,要求对二级市场退出(如IPO后股票转让)按差价征6%增值税,但一级市场退出仍免税。这一政策被作者视为对创投行业的“歧视性安排”,因其仅针对二级市场交易征税,且缺乏法理依据(金融商品转让是否属于“服务”存疑)。
3. 新增值税法的潜在影响
延续历史问题:新法未澄清金融商品的税收属性(是商品还是服务),也未明确税率,可能继续依赖税务部门解释(如沿用6%税率),导致法律稳定性不足。
创投行业的困惑:二级市场退出需缴税、一级市场免税的差异可能被固化,进一步加剧行业税负不公,影响投资决策。
税收法定原则的挑战:税法的模糊表述可能扩大行政裁量权,与“税收法定”的立法初衷相悖。
二、深层问题与建议
1. 法律逻辑的缺陷
金融商品的属性争议:
增值税法未将金融商品明确定义为独立的应税类别,而是将其与货物、服务等并列,导致归类混乱。从税法原理看,金融商品(如股票、债券)的转让更接近“财产权利”的转移,而非传统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国际上对此类交易通常采用资本利得税或印花税,而非增值税。中国将其纳入增值税范畴需更充分的理论支撑。
2. 税收政策对创投行业的冲击
政策歧视性风险:
二级市场退出征税、一级市场免税的差异缺乏合理性。创投行业的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税收政策应注重公平性。若仅因退出渠道不同而区别征税,可能扭曲市场行为(如鼓励企业延迟上市),阻碍资本市场流动性。
3. 改进方向
明确金融商品的税收属性:
需在税法中单独定义“金融商品”并规定其计税规则(如税率、差额计税方式),而非依附于其他应税交易。
统一退出渠道的税收待遇:
无论一级或二级市场退出,应适用相同税收规则,避免因政策模糊导致行业不确定性。
强化税收法定原则:
税率和计税方式应由法律直接规定,减少对行政文件的依赖,提升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三、总结
文章揭示了增值税法在金融商品税收处理上的逻辑漏洞和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对创投行业的不公平影响。新法的模糊表述可能延续行政主导的税收解释,削弱税收法定原则。未来需通过法律修订或实施细则,明确金融商品的税收属性与规则,平衡税收公平与市场效率。同时,创投行业需密切关注政策动态,提前规划合规策略,并推动学界和业界对相关条款的深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