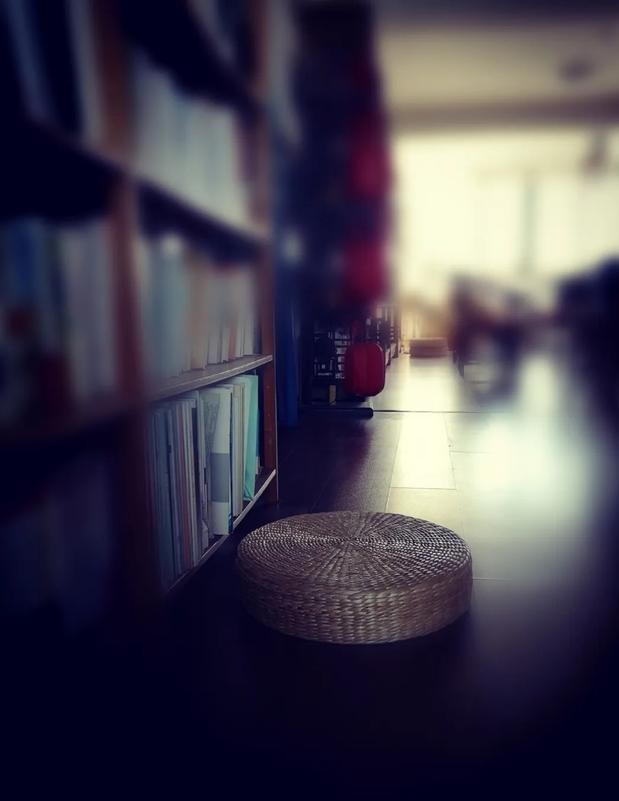
暮春午后,区图书馆东隅的木质书架,悠悠洇出松脂般的暗香,那气息仿若自岁月深处飘来,满是古朴迷人之味。我常不自觉地停留在这片被称作 “东瀛文学” 的区域。阳光恰似温柔画师,穿过《源氏物语》金箔书脊的华贵光芒,在《雪国》素白如霜的封面上,洒下细密光斑。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似浸过京都清晨纯净朝露,每个假名都裹着茶筅在茶碗中轻搅泛起的涟漪,满是细腻温润质感。
在这文字之岛,我如沉醉旅人,尽情漫步探寻。可每当借阅期限临近,理智便化作无形却有力的手,轻轻推我离开这片熟悉之地,穿过斯拉夫语系那厚重如帷幕的文字丛林。在那里,我于契诃夫笔下茫茫雪原徘徊,感受刺骨寒冷与人性温度;又在帕斯捷尔纳克描绘的冬宫前驻足,惊叹历史沧桑与建筑宏伟。
但转译的过程,宛如一杯隔夜冷茶,没了原本的鲜活醇厚。黑塞充满诗意的诗句,历经英伦海峡咸风、香港诗人粤语韵律的重新演绎,最终映入我眼帘时,已然褪去黑森林中松针特有的涩香。这让我想起幼时乡间玩的 “传话” 游戏 —— 祖母轻声耳语,经十个人传递,到最后竟成全然陌生的寓言,失了最初本意。
于是,书架间的这场迁徙,往往以折返结束。当指尖再次触碰到谷崎润一郎作品的绸面装帧,一种隐秘的联系,仿佛在血脉中悄然复苏。这些年,我像执着的农人,刻意拓宽阅读版图,努力开垦生荒地。可在异域文字的广袤土壤里,我总能隐隐嗅到故园 —— 河西走廊腐殖土那熟悉亲切的气息,那是深入灵魂的眷恋。
我抚摸着书架,似能感知它们承载的岁月痕迹。每一本书都像一个小世界,等我开启、探索。而我在书架间的徘徊穿梭,又何尝不是一场心灵的漂泊与回归。那些被我摩挲过的书脊,或光滑,或粗糙,如同岁月指纹,记录着我的阅读历程。在这小小天地,我见证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也不断寻觅着心灵归所。

二
一册书页上,辰巳芳子的名字,像一粒遗落在陶瓮底、未被碾碎的糙米,不经意间硌在我眼底,生出异样的疼。封面上,九十二岁的料理哲人端坐其中,一头银发整齐梳成利休流茶杓的优雅弧度,岁月在她眼纹里沉淀,恰似味噌在漫长发酵中积累的醇厚韵味。
这本不足百页的册子,有着难以言喻的魔力,让我在图书馆落地窗前久久伫立,直至暮色将我笼罩,把我站成一幅暮色中的剪影。
回首往昔,肺结核无情地将她囚禁了十五年之久。那漫长岁月,对她而言,就像一场文火慢炖的艰难修行。在病榻上,她静静聆听铁轨与枕木的震颤,那有节奏的声响仿若生命鼓点。蒸汽机车载着父亲的图纸呼啸而过,远去的轰鸣声似乎带走了她的部分青春。而母亲在厨房与药罐间忙碌穿梭,织就那段光阴的经纬。
当四十年漫长岁月终于熬成一盅救赎的汤,她勇敢推开生物心理学的门扉。可在探索旅程中,她却在料理台前意外找到万物通感的密钥。那一刻,她仿佛领悟宇宙间某种神秘联系,将味觉、情感与生命意义紧紧交织。
我想象着辰巳芳子年轻时的模样,或许也曾有青春活力与梦想。但命运捉弄,让她在病痛中煎熬。可她没被打倒,反而在苦难中寻得生命真谛。她的故事,如同她做的料理,经时间沉淀,愈发醇厚、深刻。那本小册子,不只是一本料理之书,更是她一生感悟与智慧的结晶。
“要让蔬菜在锅里感到舒适。” 这句话如醍醐灌顶般在我耳边响起时,我这个在灶台前常陷入混沌的人,仿佛被灵光瞬间击中,猛地惊醒。从前,我总把炝炒当作单纯物理反应,只关注油温高低、食材生熟。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油温升降间,竟藏着如此玄妙的共情。
当白萝卜被切成滚刀块,“噗通” 一声坠入砂锅的刹那,我仿佛听见河西走廊冬日寒风呼啸,裹挟着沙砾的声响,那是苍茫而独特的声音。而萝卜在汤水中缓缓舒展腰肢,那姿态分明是黑河河畔家有女清晨唱起的悠扬晨歌,在空气中轻轻荡漾。
童年记忆也随锅中升腾的蒸汽渐渐复苏。外婆的盐粒在陶碗里结晶成琥珀般颗粒,那粗粝质感折射出过去艰难岁月的苦涩。菜籽油滑过青瓷碗沿的弧线,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金色光芒,那是匮乏年代里最奢侈、最温暖的记忆。
如今,超市冷柜里摆满琳琅满目的有机食材,它们看似光鲜亮丽,却似乎没了与土地对话的灵性。那些经层层包装的蔬菜,没了泥土芬芳,没了阳光雨露的亲吻,只是工业化生产出的商品,失了生命温度。
我站在厨房里,手握锅铲,仿佛握住一把开启回忆之门的钥匙。每一次翻炒,都像是在与食材对话,倾听它们的故事。那滋滋作响的声音,不再是简单的烹饪噪音,而是生命在锅中跳跃的旋律。我开始明白,烹饪不只是为填饱肚子,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是将自然馈赠转化为人间美味的神圣仪式。

三
家人总对我痴迷那些看似粗劣的美食纪录片感到不解,甚至常讥笑我。可他们不懂,在那些摇晃镜头呈现的婚丧嫁娶里,才是未经驯化的生活原浆,满是真实质朴的力量。
甘州大地的寿宴佳肴,案板上新鲜的食材,带着泥土的气息,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牛肉小饭,菱形的面丁宛如珍珠般散落汤中,与鲜嫩的牛肉片、翠绿的香菜葱花交相辉映,恰似一场味蕾的狂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食的执着。热气腾腾的菜肴,那盘黄亮酥脆的羊肉垫卷子,面片吸饱了羊肉的鲜香,每一口都嚼劲十足,与书中描写的日式料理那精致的“残月”摆盘相比,虽少了几分精致典雅,却在粗粝豪爽间,与自然万物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彰显着这片土地独有的雄浑与质朴。
当摄像机扫过帮厨农妇那皴裂的指尖,我总会想起辰巳芳子说的 “料理是手的记忆”。那些未经修饰的方言,在电磁炉嗡嗡鸣叫声中漂浮,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竟比 NHK 高清镜头下的和食美学更接近味觉本质。因为它们承载着生活酸甜苦辣,记录着人间烟火百态。
我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着画面,仿佛自己也置身热闹场景。我能闻到食物香气,感受到人们的情感。那些美食,不只是一道道菜肴,更是文化传承、情感寄托。它们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联系在一起,共同书写人类饮食文化篇章。而那些民间厨师,用粗糙却灵巧的双手,创造出无数令人垂涎的美食,也传承着一代又一代的智慧与记忆。
我曾试着按书中所写,精心培育辣子。满怀期待地种下种子,每日悉心照料,浇水、施肥,满心盼着它们茁壮成长。可第七日,我却发现幼芽已然霉变,像一个个夭折的生命,让我满心失落。我这才明白,城市阳台终究长不出河西走廊农田那充满希望的晨曦,塑料花盆也盛不下千年农耕文明的厚重。
这让我想起在小时候在老家见过的播种仪式。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全村的人都聚在田间,神情庄重。爷爷将第一粒种子小心翼翼撒入土地时,那一刻,整个村落的呼吸都随之起伏,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祭祀。那是对土地的敬畏,对农耕文明的传承。
不过,糙米汤的实验给了我意外惊喜。浸泡整夜的米粒在铁锅里焙炒时,竟爆出类似童年柴火灶的噼啪声,那熟悉声音瞬间将我拉回过去时光。当琥珀色的汤水缓缓滚过喉头,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 “生命之味”,不过是让每个细胞都深深记住阳光雨露的来路,记住生命的起源与成长。
我站在阳台上,望着那几盆奄奄一息的菜苗,心中满是感慨。在这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离土地、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吃着加工食物,却忘了它们最初的模样。那些传统农耕文明,正渐渐被我们遗忘。但在那一瞬间,我从糙米汤的味道里,感受到生命力量,也感受到农耕文明的魅力。它不只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四
春节期间的最后一次家宴,我怀着莫名执着,执意撤去餐桌上的转盘。清蒸鳜鱼静静地卧在龙泉青瓷盘中,宛如沉睡的仙子,不再承受筷箸的轮转之苦。众人起初都有些拘谨,眼神中透着疑惑。但渐渐地,他们也学会用舌尖而非声带交流。
窗外,玉兰花的落瓣如雪花般轻盈飘进汤碗,那一刻,竟无人舍得将其捞起。大家只是静静看着,仿佛在见证一场生命的轮回。就让它完成从枝头到餐桌的最后一次旅程吧,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然的敬畏。
辰巳芳子说 “进食是与万物缔结契约”。当我们停止用喧嚣佐餐,静下心来,终于听见萝卜在砂锅里软化时的轻声呢喃,听见米饭在蒸汽中舒展筋骨的细微颤栗。这种寂静的狂欢,或许才是对生命最深沉、最真挚的敬意。
暮色如潮水般缓缓漫进书房。我常对着那些料理书脊出神,那些铅字仿佛有了生命,正在悄然生长。它们生成了牛肉小饭的爽滑、搓鱼面的劲道、炒炮仗的热辣。终于,我深深明白,读书与烹鲜,从来都是同一种修行 —— 用一颗敬畏之心,将每个字、每粒米,都读作生命的偈语,从中领悟生命真谛,感受生活美好。
在这漫长人生旅程中,阅读与烹饪,如同两条交织的线,贯穿我的生活。它们让我在文字世界遨游,在美食天地品味,让我对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每一本书,每一道菜,都像一个独特故事,等我倾听、讲述。而我,也在这阅读与烹饪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蜕变,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