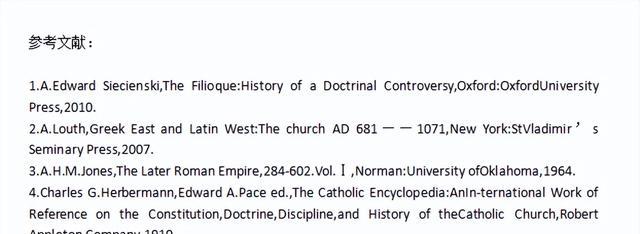从查士丁一世即位到查士丁尼时代结束,在这将近一个世纪(518-610年)的时期里,拜占庭帝国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拉丁文化逐渐过渡到希腊文化。
实际上,在罗马帝国分裂前,东西两部分的文化就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西部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东部官方语言先是拉丁语,后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用,再后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

这样,到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帝国(395年)时,东部居民中大约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讲拉丁语,到620年时,拜占庭帝国中讲拉丁语的已不到十分之一。
准确地说,从希拉克略王朝开始,拜占庭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希腊化国家。拉丁语既被民间遗忘,也被官方舍弃。
客观地说,语言对于教会教义的发展、传播以及教会之间的交流又是至关重要的。罗马教会同君士坦丁堡之间本就不和,语言障碍更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有关教义的争论。

除了语言,拜占庭帝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同样受到希腊的影响。东方教会的护教士往往把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相联系,通过利用哲学中有意义和价值来解释教义,从而将教义上升为最高哲学思想,这种倾向也决定了日后东方教会逐渐向理性化方向发展。
不同于东方希腊教父提倡的理性思考,西部教会则把宗教和哲学完全对立起来,拉丁教父们坚信基督教的基础是神的启示,这种启示不可能被任何理性思考所代替。
在西部教士的观念里,基督教是超越了所有的哲学,它的真理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来自神的启示,人的理性的适当位置是在启示之后。

因此神的启示才是高于一切的,故而希腊护教士认为理性是多余的。而且此时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横行造成的“交通的困难,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与拉丁基督教大相径庭的宗教心态和教会组织,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越来越多地割断了东罗马帝国同西欧基督教团体的联系。
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语言障碍、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空间上的分离,使得它们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逐渐形成了“希腊东方”和“拉丁西方”两种极具地域色彩的基督教文明。
这就决定了东西教会在某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在东西教会因教会利益矛盾不断激化之时,双方为维护自身利益,往往将彼此间的差异无限放大,并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

无论是5到7世纪的基督性论之争,还是后来“和子”问题的出现,亦或是8世纪开始的圣像破坏运动,这些教义上分歧的存在,都成为导致东西方教会从疏远到对立、再到对抗,直到最终走向9世纪分裂的重要因素。
5世纪,在基督教会内部曾出现过有关基督性论问题——聂斯托利的基督二性连接说(Dyophysitism)与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的激烈争论。
君士坦丁堡教会基督一性论的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反对到支持再到反对再到支持的过程。

而君士坦丁堡方面态度的变化却极大地影响到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
第一阶段,君士坦丁堡教会对基督一性论持反对的态度。
这一理论由主教的聂斯托利提出,他认为:圣子的神人二性是分离的,人性来源于其生身母亲玛利亚,神性则来自于上帝,因此他的神人两性是相互对立。
这一观点彻底否定了教会所秉持的圣子只有一个位格的传统观念。不仅如此,他还否认了玛利亚作为“上帝之母”的身份,认为她只是生育了耶稣肉体,却没有赋予其神性,故而反对将她神化。

他主张用“基督之母”的称呼取代“上帝之母”,这遭到了其他教会,尤其是罗马教会和亚历山大教会的强烈反对。
在431年召开的以所弗大公会议上,聂斯托利的基督二性连接说被判为异端,他本人也遭到了罢免。
并且此时,在亚历山大教会出现了与聂斯托利完全对立的基督一性论的雏形。

这一思想最早是由亚历山大教会主教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提出,后经神学家尤提克斯(Eutyches)加以阐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基督教义:基督在最初有神人两性,但在道成肉身之后,人性为神性所融合,最终只有神性这一唯一属性。
后来,基督一性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它在基督的神人两性中,更加强调基督的神性,并排除基督人性的特质。
但如果按照基督一性论的观点,基督不具有人性,那么他被钉上十字架就无法体现为人赎罪的意义,也就影响了基督教的救恩理论。

无论是在君士坦丁堡教会还是罗马教会中,人们信仰的都是“基督二性”,即认为基督同时具有神和人二性。
因此,基督一性论与基督二性连接说,均遭到罗马教会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点上,君士坦丁堡教会也与罗马教会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第二阶段,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态度在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II,402-450)的干涉下发生了巨变,转而在431年召开第二次以弗所公会议上被定为正统教义。
并且在会后,基督一性论教义在东方各教会中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教义之一。

皇帝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这一做法,对于罗马教皇而言是不能容忍的,直接影响到了双方的关系。
并且基督性论之争还引起了拜占庭帝国内部各教会之间的激烈争论,因而,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
第三阶段,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将基督一性论判定为异端。狄奥多西二世的继任者马西安(Marcian,450-457)451年,召开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并通过著名的《卡尔西顿信经》(Chalcedonian Creed),对“基督的神人二性”进行了重新界定。

它规定:“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同等完整的;按其神格而言,他与父同体,按其人格而言,他与世人同体,但无原罪;按神格而言,他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格而言,他在末世之中,为救世人,由‘上帝之母’童贞女玛丽亚所生;这同一个基督、圣子、主是独生的,处在两个性质之中,两性互补混淆,互补变换,互不割裂,互不分开;两性不因联合而失去区别,每一性的特点反因此的以保全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本体之中。”
罗马教会将这次大公会议的决议视为基督教信仰的明确表达。在教皇看来,耶稣基督既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两性互不混淆,同存于一个位格之中。
这一信经的通过,虽然缓和了罗马与拜占庭教会之间的关系。但却没有从改善东西教会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一看法并不被东部,准确地说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教会基督徒接受。

作为东方教会最重要的教会组织之一的亚历山大教会,位于帝国的经济重心的埃及。
埃及作为拜占庭帝国国库的主要经济来源,每年缴纳的税金多达150万索里达,即便是北非的其他几个行省(包括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西提芬西斯(Mauretania Sitifensis)、特里波利塔尼亚、毛里塔尼亚·恺撒连西斯(MauretaniaCaesariensis)、普罗康苏拉里斯(Proconsularis)、比查塞纳加在一起,只有40万索里达左右,还不及埃及所贡献的三分之一。
因此,埃及对于帝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基督一性论的坚定支持者大多来自于埃及地区的亚历山大教会,皇帝无法对一性论派的感情采取不闻不问或者淡漠的态度,至少他根本无法承受失去埃及,这个帝国粮仓的巨大风险。
同时,由于卡尔西顿信条强烈反对基督一性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亚历山大教会以及埃及一性论信徒与拜占廷当局之间的矛盾。
一些狂热的信徒甚至通过暴力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情绪,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治安,引起了拜占庭帝国政府的担忧。

为了能够安抚帝国内部支持基督一性论的教众,君士坦丁堡总主教阿卡西乌采用了亲一性论派的神学观点,并得到了皇帝弗拉维·芝诺的支持。
482年,芝诺颁布了《联合诏令》(Henotikon)以缓解拜占庭教会和亚历山大教会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一诏令却回避了基督性质这一争论焦点,取消了卡尔西顿会议规定的教义,实际上都是对一性论派的退让。

虽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两大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却带来了教会内部的另一大问题——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仇视。
罗马教皇菲利克斯(FelexⅢ,483-492)认为,君士坦丁堡教会这一离经叛道的做法是对于基督正统信仰的背叛,并将阿卡西乌视为异端,予以绝罚。
双方也因此断绝了圣礼共融。东西教会史上的第一次分裂——阿卡西乌教会分裂由此开始,这次分裂分裂前后延续了35年,直至519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与罗马教皇签署《何尔米斯达信式》(The Formula of Hormisdas),东西教会之间的分裂才告一段落。

虽然罗马教皇对基督一性论一直持反对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它在帝国东部的传播。到了7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斯(Sergius,610-638)写信给时任罗马教皇的洪诺留(Honorius,625-638),在信中他重新对卡尔西顿公会议的决议进行阐述,将会议通过的“基督的神人二性不可分”解释为“基督只有一性”,在信件中,他还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他对这一教义支持的愿望。
此后,帝国皇帝希拉克略及其后任君士坦三世(ConstantineⅢ,641-668)又分别于638、648年,相继发布诏令,在全国范围推行“一性论”教义,不从者予以治罪。

这一做法不仅引起了帝国西部广大教徒的不满,还遭到了不受拜占庭帝国直接控制的西部教会主教们的强烈反对。
基督性论之争又重新成为东西教会博弈的焦点,其激烈程度较5世纪时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