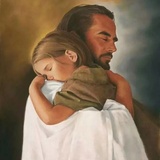口述丨李玉泉 采写丨徐晓

我是1982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法律系,198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读民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我的专业课成绩考得很好,外语课成绩考了78分(当年除北京大学要求外语考试成绩不得低于60分外,其他高校要求不得低于50分)。
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本来我想回浙江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但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保险系的系主任魏华林老师找到我,希望我能去他们那里教保险法。
武大是第一批恢复保险专业教育的四个院校之一,金融保险系从1985年开始招生。魏老师催我赶快去报到,因为15号之前报到能领全月的工资,于是,1989年7月1日,我就去金融保险系报到上班。新学期开始,我教保险法、保险条款与案例分析两门课。
我读研时并没有系统地专门学过保险法,保险法是民法里面的重要内容和一个分支,合同法里面包括保险合同和海上保险合同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教保险法这门课,就得自己下功夫“补课”,像保险学原理、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再保险、保险经营管理、风险管理等等,都要自己从头学一遍。

那时候大陆还没有保险法教材,我把学校图书馆里能找到的资料都找来看了,包括民国时期陈顾远老先生的线装本《保险法概论》,还有台湾郑玉波大法官的《保险法论》等等。
英文的保险法著作也相当少,由于属于英美法系,基本上都是判例,理论论述不是很多,也不系统,看起来很费劲。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主任施文森先生写了很多保险法的书,但是图书馆里只有目录没有书。
当时也是愣头青,我直接给施文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一番,说现在要教课,资料很少,看到先生写了很多保险法的书,非常冒昧地写信求教,保险法该怎么讲,哪里能买到您的书。万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就收到了施文森先生寄来的一大包书。
他那个信是用毛笔竖写的,像书法一样,非常漂亮,抬头是“玉泉吾兄”,落款为“弟施文森叩拜”,真是受宠若惊!他一下子给我寄来了15本书,包括他的保险法著作、论文集、美国纽约州保险法原版等等。我真激动啊,如获至宝,太珍贵了!他的书里面还提到一些外文资料的索引,我按图索骥,去图书馆找原文来研读,这样资料就多了。
保险法一周四节课,保险条款与案例分析一周两节课,经济学院的课时费为9元钱,比法学院高一点(法学院课时费5元钱),加上82元的月工资,我的收入还算不错。
我跟学生们说,从法律的角度讲,保险就是一种契约或者因契约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你学保险不懂法律肯定不行,不但要学保险法,还得学合同法和民法等。于是,很多金融保险系的学生就跑去法学院听课,有的还辅修了法学第二学位。
我在金融保险系教了两年保险法,自己在备课过程中也做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保险法方面的文章。

后来碰到法学院的韩德培老先生,他说你还是回来读博士吧。韩老先生是国际私法的宗师,泰山北斗,当时只有武汉大学设了国际私法的博士点。
韩老先生说,你以后博士毕业就留在法学院,法学院更需要。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如果你要脱产读博士,就要赔给学校1500元的“编制费”,理由是我们占了学校两年的教师编制。那时候每个月工资才82块钱,1500元等于把两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这样,1991年我就到法学院全日制攻读国际私法专业博士学位,师从李双元教授。
我问导师,我能不能继续研究保险法?他说好啊,你原来一直教保险法的,还写了一些文章,你可以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国外的民商事法律,继续研究保险法。韩德培老先生也非常支持我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保险法。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家重视知识、重视学历、重视人才,电大、夜大、函授很时兴,机关企事业单位里面很多没有学历的人,下班了以后都去这些学校上课,我们就去讲课,我讲经济法、民法、合同法这些课程,挣了不少讲课费。
此外,还跟着导师参与一些疑难案子的咨询,也有一些报酬。另外,保险系的魏华林老师又来找我,说你去读博士,保险法课没人上了,你还是来给我们上课吧,学生反映你教得很好。
我想上一节课也有9块钱呢,就上吧,反正讲义、讲稿、课件都有。所以我一直在金融保险系又上了两年课,到第三年,我跟魏老师说不能上了,我要写博士论文了。
读博期间,对保险学和国外的保险法律都有了研究,慢慢的形成了体系框架。我的博士论文是《保险法基础理论研究》,18万字,这是国内第一个从比较法角度研究保险法的。
博士论文答辩,按学校规定自己的导师李双元教授要回避。博士论文校外评审专家是时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系主任的曹建明教授,曹建明老师的意见是手写的,给了很高评价。
韩德培老先生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经济审判庭副庭长费宗祎老师当答辩委员会主席。
费老曾参与《民法通则》《合同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仲裁法》等很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后来还推动设立了中国首家知识产权法庭,是理论与实务很好结合的权威专家。
答辩时,我先把论文的框架、基本内容、主要观点作了汇报。作为主持人的费老说:刚才玉泉已经把保险法的情况都说得很透彻了,咱们也都不懂保险法,是不是就算了,我们说点别的吧?
答辩委员会的刘振江教授、张仲伯教授等都同意费老的意见,所以很顺利地就通过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费老说,小李,你毕业了以后就到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工作吧,你外语也不错,我们涉外经济审判需要这样的人,说好了。我们学法律的如果能去最高人民法院,肯定很激动,我就说行,谢谢费老。

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曾经到北京查过资料,到过位于西交民巷的人保总公司保险研究所,也到过阜成门的人保总公司“新大楼”。在阜成门办公大楼碰到人事部的人,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是武大的博士生,学保险法的,来国际保险部找资料。他说你毕业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吧,我说好。
后来差不多已经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我们法学院管研究生的副院长是我读硕士时的小师弟,他说,师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人到院里面来考察你了,要你到人保总公司去工作,说你是人保第一个博士,还要给你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我犹豫了,就跟家里说。我父亲是个老农民,目不识丁,平时的“文化”活动也就是跟着我母亲看看电视,特别喜欢看《杨乃武与小白菜》《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方庆见姑》《碧玉簪》等越剧电影电视剧,其实他是边看画面边听我母亲讲。
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不能去最高法院,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如果把案子判错了的话,那是罪过的!你没看杨乃武和小白菜那个戏啊,那是冤枉官司,作孽啊!以前我们的上一辈把法官、律师这些都叫作冤孽行业”。
我又跑到我们法学院院长家里面听他的意见,他建议我别去司法机关,说:我的同学在公检法机关很多,虽然当了什么官,但都是清水衙门;你研究保险法,去保险公司,是第一个博士,人保又给你一套房子,挺好。
听说人保在“挖”我,最高人民法院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也可以给套两居室。
我因一直想把保险法理论研究与实务结合起来,最后还是选择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人保系统第一个博士。但是人保并没有兑现“给一套两居室”的承诺,只在国防大学集体宿室给了一间14平米的单身宿舍。

1994年7月12号,我到人保总公司报到。本来以为15号之前报到能领全月工资,结果还是按半个月给。
原准备让我到办公室调研处写材料,我就跟人事部机关干部处侯彦勤处长说,我一直做保险法研究,没有保险实务工作经验,我非常希望做具体的保险业务,否则我就不想来了。她说会向领导反映你的这个要求,后来就叫我到国际保险部去报到。
当时国际保险部有时国庆、王真、王海明三位副总经理,时国庆主持工作,三位领导在11层的一个办公室一起办公。
我报到的时候时国庆出差了,王真和王海明在,王真说:“哟,来了个博士,欢迎欢迎,我们正需要人才呢,你看看你想到哪个处?”
我也搞不清楚,就说到综合处吧,我以为综合处什么业务都做,实际上是打杂的。王真说那不行,你博士怎么能去综合处,我说听领导安排,她说你先等一等,就把我带到船舶险处,因吉小满休假,就叫我临时先在她位置上办公。
时国庆回来以后,把我正式分配到远洋货物运输保险处,我就在那儿做了近两年远洋货物运输保险的展业、承保、理赔、追偿,把水险这一套实务基本上弄清楚了,当然也参与了水险、非水险的条款修订等工作,学到不少东西。
翻看历史上的业务档案,发现有些案卷材料上有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感觉到人保的地位很高,也感觉到“涉外无小事”。

1996年7月,经中央、国务院批准,人保机构体制改革,成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简称中保集团),下设中保财险、中保寿险、中保再保险三家子公司,由集团副总经理孙希岳、何界生、戴凤举分别兼任这三家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我被留在集团办公室条法处,被任命为副处长,王建是处长,下面有李政明、罗庆、吴军这几个人。后来,王建去集团资金运用部主持工作,我接任条法处处长。
刘学生从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处里,我刚好出差回来上班,在走廊里碰到政研处的施红,她告诉我:你们处里来了个刘学生。
我说:留学生?哪个国家的?施红说:不是留学生,是名字叫刘学生。
在中保集团期间,我经常跟着政研处一起给领导写工作报告,我们条法处写的三个调研报告,得到了集团领导的高度肯定。
中保集团成立后,产寿险业务分设为两家公司,互相抢业务。那时候保险法还没修改,还没有“第三领域”这个概念,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还属于寿险业务,财险公司是不能做的。
但是中保财险以责任险的形式来做意外险,而中保寿险也改头换面,把责任险业务也搞成意外险来做,两家打得一塌糊涂,互相告状。
我们去调研以后,以条法处的名义写了一个关于责任险和意外险业务交叉的研究报告,把责任险是怎么回事、意外险是怎么回事、现在集团财险和寿险的业务是怎么个情况、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梳理。
中保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马永伟在调研报告上批示:条法处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请希岳和界生同志阅。
还有一个研究报告,当时的机动车辆保险,工商部门说是垄断,物价部门说是乱定价,天天查我们。我和刘学生、罗庆去调研,回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工商、物价部门参与强制定价是不合理的,没有法律依据。文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影响很大,马永伟总经理看到以后说,小李把这个问题又说清楚了。
还有一个也是机动车辆保险的事儿。车险是财产保险公司最大的业务,各公司之间竞争很激烈,打价格战,后来各地纷纷成立新车共保中心,统一承保之后按约定的市场份额来分。
工商局又来查处,说你这是搞价格联盟、垄断。我又和刘学生等去调研,也写了文章发表在保险报、金融时报上。那时候工商局很较劲,还写了内参向上面反映,中保集团很被动。
我们的研究报告出来了以后,马永伟总经理挺高兴,说再到国务院开会,如果领导问起来,就能够讲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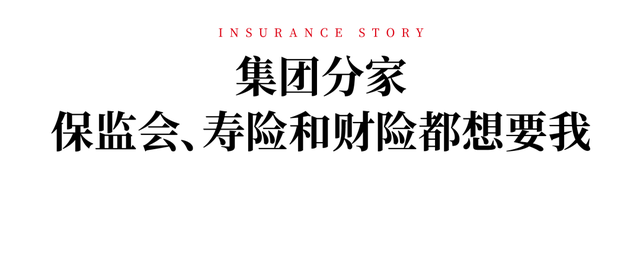
1998年下半年,马永伟总经理受命牵头组建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撤销,旗下四个子公司成为独立的一级法人,分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香港中国保险(集团)公司。
在1996年人保那次机构体制改革时,吴小平副总经理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集团公司办公室条法处当副处长,当时我不太愿意。
我觉得我在国际保险部做水险业务,信用证、租船合同、贸易合同、保险合同、提单、租约这些东西,经常跟海商法、国际私法、民法、合同法、保险法打交道,专业很对口,水险的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想一辈子搞这个,成为一个水险专家。
吴小平副总经理说,一辈子很长的,你不可能就搞水险一个东西;他说他自己原来也是搞国际保险业务的,后来转了这么多岗位,换来换去;他劝我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到办公室来,接触的东西就多了,眼界是不一样的。
1998年在中保集团的基础上组建保监会,还是吴小平找我谈。他说:马总委托我找你谈,希望你留在保监会。我说好,听领导的。
回去一想不行,我还是想搞业务,不愿意留在机关,我就又去找吴小平。吴总很不高兴,说你都答应了,怎么又变卦了?我跟马总怎么交代?你回去再考虑考虑。
我考虑之后又找了他一次,他说,你要真的不愿意留在保监会,我建议你不要去财险,去寿险吧,未来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寿险的作用比财险大。
那时候的现实情况,寿险比财险差远了,如果要我去寿险,我宁可辞职。现在回头看,还是领导站得高看得远。
后来他们真的把我分到中国人寿去了,是中国人保孙希岳总经理看到名单后把我要过去的。孙希岳总经理还专门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小李,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财险来。

2000年8月,孙希岳总经理退休,唐运祥从保监会副主席转任人保公司总经理。
当时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入世”谈判,金融行业也要改革,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体制。金融行业里面,工、农、中、建这样的银行太大了,轻易不敢动;人保在保险行业是第一,但在金融行业里面属于体量小的。
所以,中央、国务院批的那个方案是要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并选择适当时机在海内外上市。
2000年10月,人保成立法律部,我当总经理。2002年2月,公司成立股改领导小组,正式启动股份制改造,我是股改领导小组成员,全程参与了这次改制工作。
这事儿谁也没有干过,不知道该怎么干,感觉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既然上面定了,硬着头皮也要搞。我们就对照海内外上市的要求,一项一项地梳理,开展选聘中介机构、会计审计、土地评估、资产评估剥离和重组等工作。
那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是不太认可的,觉得你实际上是跟政府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公司。最明显的有两个:
一个是企业有这么多离退休人员。在发达国家,退休人员是社会化的,不是单位的人了。我们这儿“生是人保的人,死是人保的鬼”,离退休老干部很多,还经常要搞活动、发福利。
二是有那么多资产权属不明,还有很多不良资产。我们的很多资产,比如办公楼、宾馆什么的,很多都是政府无偿划拨一块地让你去盖楼,也不用办土地使用证。现在要上市了,必须要权属明确,厘清法律关系,否则不能进入上市公司。这里面有的是国有土地,有的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如果交土地出让金的话,那是天文数字。
我们法律部负责这块工作,配合资产评估师对公司4000多家分支机构清产核资,完成资产评估报告;配合土地评估师完成了2000多个市县的土地评估及备案工作,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完善了产权;收集、整理了1999年以来各类法律文件上万卷,建立了完整集中的法律资料库,协助律师审阅了公司各类法律文件、重大合同和重大诉讼案件。
资产剥离、审计评估、精算、法律等股改工作于2002年5月份启动,历时整整一年。
2003年7月1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组改制为中国人民保险控股公司,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
这是一个“靓女先嫁”的策略。中国人保变更为人保控股,其职能包括代表国家投资并持有上市公司和其他金融保险机构的股份、经营管理存续资产、经营国家授权或委托的政策性保险业务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业务。
把离退休老干部也作为宝贵财富转入人保控股公司。人保财险是中国内地最大的非寿险公司,继承原来的人保公司的所有商业性保险业务,优质资产都在股份公司里面。
人保资产是国内首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和运用人保财险委托的保险资金。后来又成立了人保投资控股公司,把不良资产都装进去。随着中国房地产的上涨,这些资产处理都变成了好资产。
2003年11月6日,人保财险(对外名称为:中国财险)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2328,据说是“又升又发”意思。它是内地保险第一股,同时也是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第一股。
一个多月以后,中国人寿于12月17日、18日在纽约和香港同步上市,所以他们说是“海外两地上市第一股”。其实一开始人保也想在纽约和香港两地上市,但我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认为不符合美国的监管规定,硬上的话风险太大,就决定先在香港上市。
人保财险上市还是很成功的。中央和国务院的评价很高:
中国人保的成功实践,为中国金融企业改革和上市、走向海外探索出了一条路子。当年,唐运祥总经理被评选为CCTV十大经济人物。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美国国际集团(AIG)入股的事儿。
从筹备上市工作时,就考虑了要引入优秀的国际战略投资者,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形象。先后与十几家国际保险公司、金融集团进行了秘密接触和谈判,最终谈成的是AIG。AIG在全球500强排名第50名,在保险排名第一。
它是在中国发家的,对中国很有感情,AIG主席格林伯格也很看重中国市场。唐运祥总经理带着我们跟他们谈,夜以继日连续谈了十几天,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战略投资协议和业务合作协议。
人保上市,AIG作为基石投资者,以首次公开发行价购买了人保财险发行后9.9%的股份,持股锁定期为5年;但是人保要把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业务的40%分保给AIG,签订长期合同。
AIG获得人保财险的一个董事会席位,同时AIG将派出营销、精算、产品开发、理赔等专家到我公司长期工作,为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我于2003年7月人保财险成立时被提拔为副总裁、党委委员。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两险”项目,AIG派来的专家团队由美国人John Carry牵头,包括来自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成员;我们这边由营销、精算、产品开发、理赔的一帮人跟他们对接,我是分管领导。
他们按照AIG的经验来设计开发一些产品,但双方理念冲突还是挺大的,相互之间告状,都说对方不懂。我就召集两边对口的人员喝了一场大酒,要求双方都要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形成合力,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汇报,不要经常吵吵闹闹、拍桌子。
真没想到,AIG专家团队不仅技术含量高,酒精含量也是相当高,那一次酒喝了以后,大家就好多了。John Carry很高兴,每次见到我就说:老朋友,老朋友!

我从1994年进入“老人保”公司,干过水险业务,当过条法处长;“分家”之后在人保公司当过市场开发部副总经理,法律部总经理,人保财险党委委员、副总裁;后来又当过人保健康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人保集团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总裁。
但是,法律是我的“老本行”,可以说从来没有离开过法律。
1995年我应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之邀请,负责撰写国家“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之《保险法》。以前国家法学统编教材都是全国范围内挑选最一流的几位专家教授共同编写,有主编、副主编、撰稿人。
我刚30岁,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邀请我单独撰写《保险法》,真是欣奋不已,受宠若惊!幸好此前有18万字的博士论文《保险法基础理论研究》打底,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修改完善,经常是半夜以后才睡觉。
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稿(24万字),1997年出版,成为各大学本科、研究生学习《保险法》的国家统编教材,首次建立了保险法教材的完整体系,反映很好。
此举也奠定了我在保险法领域的江湖地位。后来在工作中广泛接触保险实务,并且参与国家保险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活动越来越多,大开眼界,在工作之余还一直坚持理论研究。
2003年出版了《保险法》第二版(44万字),2019年出版第三版(47万字),成为普通高等院校保险法学精品教材,现在我正在准备修订出版《保险法》第四版。
保险法是1995年6月30日颁布,10月1日起实施的。后面的几次修订,都征求保险业界的意见,我都参加了。现在正在进行第五次修订。
1995年保险法公布后,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更好地适用保险法,组织力量起草了保险法司法解释,草案共82条。
199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分管副院长唐德华带领起草小组到人保公司征求意见,人保方面孙希岳总经理亲自出面,我主要发言。当时年轻气盛,我说草案82条,除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没有问题,其他80条都有问题,逐条发表意见,整整讲了一天。
最后唐院长说,看来我们最高院对保险法理解不深、不准,就跟孙总商量,委托人保帮助起草。我受命后天天加班加点,起草了一稿,共50条。后来听说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时分歧较大,认为出司法解释暂不成熟,待保险法司法审判实践再丰富时再行起草。
直到2009年、2013年、2015年、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一)、(二)、(三)、(四)才陆续岀来,可见对保险和保险法的认识分歧是多么大。我有幸一直参与其中,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2002年是第一次保险法修改,修改过程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按照国际惯例,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属于“第三业务领域”,寿险公司、财险公司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国家1995年的保险法规定,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只能是寿险公司做,财险公司不能做。
我记得是在新大都饭店开会,有全国人大法工委、保监会、人保公司、中国人寿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我们人保公司是王毅副总经理参加,我是法律部总经理;保监会是魏迎宁副主席,全国人大法工委好像是王胜明副主任。
我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介绍了十五个国家的保险立法情况,反反复复讲,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通行的做法,第三业务领域寿险公司和财险公司都可以做,从立法、理论、利弊各方面都讲了,讲的时间比较长。
中国人寿当然不希望财险公司进入这个领域,但他们的发言没那么系统,只是讲了如果财险可以做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那么寿险公司也可以做责任险等等。第一次保险法修改后,财险公司经过监管机关批准也可以经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

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的时候,涉及到我们保险的就四条,草案里面规定了机动车辆必须要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出了事故以后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我一看说不行,我就找到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的王胜明副主任说:王主任,如果这样的话保险公司要关门了。
为什么呢?国家规定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强制保险是有保险责任范围的,它有除外责任,还有保险金额。
保险公司赔偿,但不是说造成第三者损失都得赔,第一是要在保险金额范围内,第二要属于保险责任,第三如果是逃逸案件,法律上可以规定由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之后可以向逃逸者进行追偿。如果笼统地写发生事故以后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那保险公司不是要关门了吗?
我给王胜明副主任打电话,说这里面四条写得都有问题。他说,那你写个书面的材料,明天到我们法工委来,我把相关的室主任、处长都叫上,你再详细跟他们说一说。
第二天我就带去四条具体的修改建议,在法工委当面跟他们一条一条汇报。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完善了,但是执行的时候又出现偏差。为了息事宁人,出了交通事故以后公安和法院多是让保险公司赔偿,拉一个垫背的。我又给王胜明副主任打电话,建议由法工委牵头,召集公安部、最高法院、保监会一起开会强调一下:
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含义是什么、立法的本意是什么、目前在实际操作中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来执行。
后来王主任还真的组织开了这个会,会是在人保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交管局、保监会财产险监管部都派人参加了。
事先我跟保监会财产险监管部丁小燕主任也作了汇报和沟通,她说李总,我们争不过他们,你们人保要多发挥作用。
公安部交管局是叫苦连天,说压力太大,保险公司要多承担社会责任,尽量多赔。
后来实践中还是有明显的好转。但在某个省份,只要机动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都判保险公司赔,根本不管你保险金额、除外责任什么的,保险公司亏得一塌糊涂。
我专门去找过那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我说您这样判不是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本意,他说我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样你还跟谁说理去?
我们搞保险和法律的,应该尽可能把法律、保险理论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推动保险业依法高质量发展!